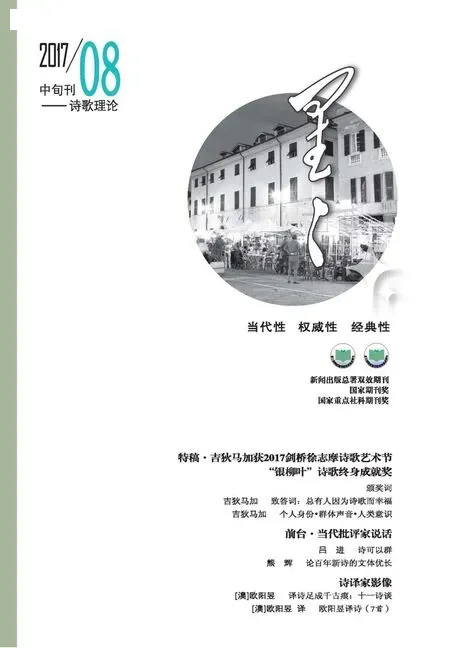有“度”的咏叹调
2017-12-29卢贝贝
卢贝贝
代 薇
有“度”的咏叹调
卢贝贝
罗兰·巴特高呼“作者之死”,让我们对话前人作品时更理直气壮,而当我们加入现代诗歌的宴席,巴特的这碗“壮胆酒”似乎降了度数。对于开放动态的诗歌文本,一定程度上的“误读”提供了阐释的可能,阐释属于大众,而诗歌的形成却更私人化。诗人通过自我观照,“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歌咏之。”诗歌是诗人的咏叹,他们或烛照内心,或直视身体,或洞察世界,本期的《停顿》《身体里渐渐有木质的东西》和《动摇》这三首诗,正体现了诗人们自我观照的不同维度。
一轮圆满可以在回忆里待续,半生遗憾何尝不是在记忆里添油加醋?《停顿》一诗“我记得夜晚的唱片”,它的旋律还飘渺着那晚的蜃景。“我记得无能的力量”,挥拳无力的空虚,忍痛与世界妥协,却偏不握手言和。“我记得你的眼睛”,它们有泪有痛有伤……代薇的咏叹戛然而止,记忆却弥散开来。结构主义诗学大家尤里·洛特曼认为,诗篇中看似完全重复的单位,其信息含量随着位置的改变而改变。三个“我记得”在语法层是对等的,其结构在聚合轴上形成平行对照关系,遗憾的是语音层过于自由,未能锦上添花,在语义层上情感则层层深入。“唱片”“金属”“火车”和“眼睛”蒙太奇式的跳跃,无意完整地讲述什么,反而营造了回忆的模糊惆怅。整首诗的基调,看似是“失温”的冷,“无力”的痛,而三次娓娓道来的“我记得”,却升腾起脉脉含情的暖,正因为对记忆有情有义有温度,才这般念念不忘。或许,这列移动的火车是命运乐谱上一个轰隆隆的休止符,停歇了一场本应继续的故事。亦或是随君直到夜郎西的明月心与火车同速同步,移动的火车反而像是自欺的静止。我有富足的回忆,你的眼睛是否也记得我?
诗人窗户也“只剩回忆了”,在《身体里渐渐有木质的东西》一诗中,年少时荡漾的波心从圈圈涟漪变成同心圆的年轮,木质化的身体,有着阴阳割昏晓的纹路。诗人烹煮煎熬的粒粒文字——“木质”“水面”“爱情”,都淘洗于日常生活的米袋,为何诗歌并未因此而变得清淡寡味?现代语义诗学学者C.T.佐梁给出答案:词被选入诗歌之前,本身就是多义的,潜在的意义相互指涉,诗歌就变得饱满。“木质”指涉的是坚硬、成长、大地。生命经历风沙的砥砺,逐渐纤维化,有的人干涸腐朽了,有的人获得雨露的滋润,茂盛于天地之间。木质化的我们如何获得这份生命之水?诗人并未告知。他只是翻开记忆的口袋,荡漾着青春的花叶与少女的裙摆,它们或许曾带来一场暴雨,摧枯拉朽,又使人愈发坚韧成长。待盛夏明媚,木质的心,也会不期然地吐翠。
当人与木同构,心意便渐渐共振,目之所及皆生机勃勃。针对《动摇》一诗,在诗人眼中,路的拐弯也是野性的,诗人继而把视野交给大雁,用双翼丈量大地,俯视生动的草原,把握生命的脉搏。在这里,生命的诞生与捕猎的死亡同为一瞬,神圣与残忍共为一体。诗人没有沿着大雁的视线继续展开,而是含蓄地吐露心事,他将“由于”独立于诗歌一行,行末的停顿使完整句法一分为二,产生逻辑重音,于无声处的停顿却是另一种方式的呼唤,是诗人情感波动的表征。诗人也曾是“我们”中的一员,他似乎发现了什么而内心动摇,委婉地责怪风没有吹来生之旋律,却对“我们”不置一词,这般谦虚有礼,实然已与“我们”保持了距离,这便是诗人敬畏生命的态度。
“停顿”的代薇烛照内心宇宙,呢喃过往,有温度地自我慰藉;审视“身体正木质化”的窗户,云淡风轻,有湿度地进行“光合作用”;正发生某种“动摇”的余真,俯瞰大地,有态度地指出人类过失。温度、湿度、态度是三代诗人发声抒情的不同音色,构成人生乐章的复调咏叹。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
本期推荐诗歌
停顿
代 薇
我记得夜晚的唱片,金属弯曲
渐失的体温
我记得无能的力量
世界不可改变的方向
——痛心,执迷
移动的火车像漫长的停顿
我记得你的眼睛
像一个伤口挨着另一个伤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