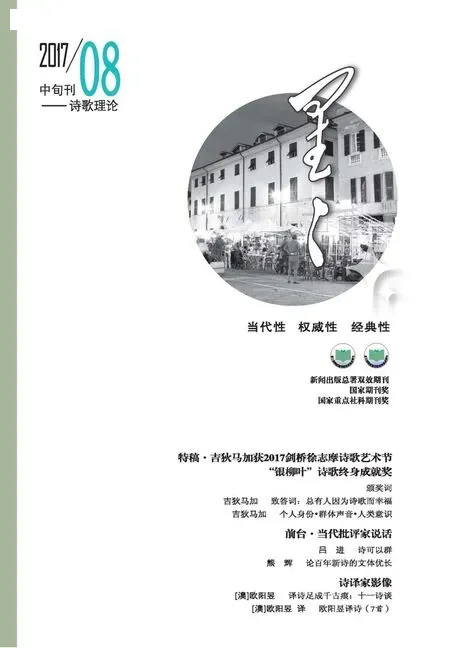出神入化通灵魂
——评王崇党的散文诗
2017-11-16崔国发
崔国发
散文诗现场

主持人语
在当代散文诗理论界,崔国发可谓最为刻苦和勤勉的学者,而他同时也是一位重要的散文诗作者。他不但有散文诗理论,还积极进行散文诗创作,通过实践反观自己的理论,通过理论审视自己的实践,这是非常难得的。这里推荐这篇他的解读王崇党的散文诗集《出神》的导读性文章,紧紧围绕着散文诗写作的“出神入化”之境问题而展开。他认为“散文诗的‘出神入化’,归根结底,需要在美的观照中回到自己的内心,凭依灵魂的内部视觉。”而王崇党的作品,正是这种审美追求的具体体现。通过文本分析,他最终的结论是“王崇党的散文诗,出神出情,入智入美,思想深邃广阔,艺术感觉敏锐,每每触及到灵魂的纵深、文化的截面和诗性的前沿,明心见性,意味悠远。他的书写打破常道,勇于变局;拒绝重复,寻求差异,在解构与建构中参差与磨砺,显示出了作者少有的锐气与才气,也有力地见证了当下散文诗的丰富可能性。”这是一篇值得大家细细品读的文章。张晓润也是一位散文诗作者,她的文字充分发挥了女性特有的细腻与婉约,总在自己的散文诗中静静地打开心灵深处的一面“镜子”映照自身,同时也向读者敞开这面镜子的“更深处”。而这里推介的却是一篇她的审美文章,是她阅读近期出版的周庆荣新著《有温度的人》而产生的审美共鸣,从中不难发现作者对于社会的冷静审视与深度忧患,在这里《有温度的人》成为她的另一面“镜子”,她在“镜子”中把自身与这个社会同时映照,同时揭示与提醒。
——灵焚
出神入化通灵魂
——评王崇党的散文诗
崔国发
在灵焚、周庆荣主编的“我们·散文诗丛”第三辑中,我特别注意到王崇党的《出神》。正好,这个书名蓦然唤起了我对散文诗之所能臻境阈的热切期待。散文诗写到最后,果真能出神入化,炉火纯青,技艺达到神妙高超的境界,那该有多好啊!于是,我迫不及待地翻到了崇党兄的那章《出神》:“周围的人神采奕奕时,人间便是天堂;/周围的人黯然无神时,人间便是地狱。//我时常入寂静深山,喝山泉,吃松针,听鸟鸣,走萨满的禹步,与天地万物沟通,随遇而安。/我无驾而行,清点大好河山的细软。/冰河递上来的奏折我看一页烧一页,暂且允许土里的种子围着壁炉做梦,顺便把拟好的春天交给清风。//我深信,出过神的人,才是活过的人。”可见诗人的匠心独运,泉水、松针、鸟鸣,以及大好河山的细软、冰河在风中吹来的奏折,还有那土里的种子,春天的清风,温暖的壁炉等,悉数在这篇短章中裒集与团聚,成为触发与生成诗歌静穆、慈祥与灵性的意象。诗人感物,连类不穷,这些经由作者在“寂静深山”中感触、发现和捕捉到的生动的形象,折射着诗人主体审美的情操、性情与心境,于相对应的体验与情绪中深深地影响着诗者的心灵,“目既往还,心亦吐纳”(刘勰语),当诗人将感情移入观照对象时,那一种美的存在,便不再是来自“先验的形式”(康德语)、“理念的显现”(黑格尔语)或“感性的静观”(费尔巴哈语),而是来自观照对象之生活与实践的客观存在。让美的形象开口说话,美中生情,美中生智,美中生理,透过这些有形、有神、有声、有色的意象,充分表达诗人“与天地万物沟通”的那种随遇而安、淡泊明志的一腔情怀,以及祈盼“周围的人”神采奕奕而非黯然无神,人间都是天堂的美好愿望。而结尾句“我深信,出过神的人,才是活过的人”,可谓画龙点睛之笔,不仅点明了散文诗的题旨,而且统摄着全篇的脉络,使人灵敏的“生理器官”一下子便发展为形上而非形下的“文化器官”、形内而非形外的“灵魂器官”,它们于美感的氤氲中,真的能“出神”而入一种化境了。
散文诗的“出神入化”,归根结柢,需要在美的观照中回到自己的内心,凭依灵魂的内部视觉。对此,新柏拉图主义的创始人和重要代表者普罗提诺曾经说过,真正的存在只有通过所谓“出神”才能被认识,出神就是灵魂从肉体回到自身,是一种“灵魂的单纯化”,也只有通过这种单纯化,灵魂才进入幸福的安宁境界。为此,普罗提诺这样写道:“我常常离开自己的肉体而醒悟回到自身,处在别的东西(外物)之外,进入内心深处,得到一种奇妙的直观和一种神圣的生活。”(参阅麦凯南的《九章集》英译本,第4集,第8篇,第1节,1930年伦敦版)。美的观照本质上就是一种出神状态(转引自汝信、夏森著《西方美学史论丛》第7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而王崇党的“出神”,我以为,他在散文诗中的美学观照,不啻借助于感官,很大程度上还来自诗人“灵魂的视觉”,诗人也只有改善自己的灵魂,才能在“更高的世界”里进入出神状态,达到与灵魂合一的思想境界。王崇党先生坦言,既然选择了散文诗作为自己心影的投射,就要努力让心灵的底版纯净一些。他在散文诗集《出神》的后记中这样写道:“不管如何修炼,我觉得首先要让自己的眼睛清澈,才能看得更多更彻底。要想具有清澈的眼睛,就得去除蒙蔽,沉积混浊,让自己具有柔软、慈悲、灵性、静穆、博大、智性、天真等质地。只有这样,我们的诗歌写作才能走得更远。”(《散文诗两问》,《出神》第92页,北京燕山出版社,2016年版)——诗人所说的“让自己的眼睛清澈”、“具有清澈的眼睛”,这不是“灵魂的视觉”又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有了“灵魂的视觉”,散文诗便有如神助,任何一个见到美的东西的诗人,都不得不承认美的真实存在,或者说存在的真实性,美便是与灵魂同类并使灵魂感到喜悦的幽灵。“无法逃离。我看事物的双眼,一半是白,一半是黑”、“能够被抹黑的,都是虚无;能够被照亮的,都是金刚。/虚空一直铺展着它的天涯,一切光荣和梦想都在快马加鞭中一闪而过。/肉身和炭一样,可以是灰烬也可以是金刚。精神才是它永恒的纹理。/白天像一道打开的伤口,一切都在盛大地溃烂着;黑夜则是一片最大的菩提叶,用它别样的光芒照亮苍白与荒凉。/昼上面是神灵,夜下面是苍生。任一光亮,都是观望我们的眼睛。”(《玄白之思》),诗人“看事物的双眼”,于虚实、隐显、黑白之间,所看到的,是“光荣和梦想”,是“精神”的永恒,是“别样的光芒”,是“光亮”与被照亮的“金刚”,当然也有“虚空”、黑暗与灰烬、一道溃烂的“打开的伤口”等等。在这里,诗人灵魂内部的观照,又何尝不希望摆脱“和炭一样”的肉身的束缚,把“白”带入“黑”的世界,把光线带入阴暗的地方,努力使一切都发出美的光辉,因为灵魂的美就在于保持它的纯洁;灵魂的美就像“金刚”,如果混杂着其他杂质的话,它就会贬值。灵魂还像诗人的眼睛一样,不能被“抹黑”,也不能掺杂着沙子,即便是“黑夜”也是“一片最大的菩提叶”,能够熠熠照亮“苍白与荒凉”。诗人多么祈盼,灵魂的内部视觉,有如白昼的“神灵”,那至上的光辉,能烛照“夜下面”的“苍生”啊!“架在栴檀木柴火上的亡人,终于放开索取的双手,火之钥匙层层打开肉体的禁锢,还灵魂以自由。/一炷栴檀香的袅袅烟雾中,爱在升腾,罪在消解。”(《栴檀树下的观想》),读到崇党的这章散文诗,我忆想起曾经读过的奥古斯丁,这位著名的哲学家当年曾受到柏拉图派即普罗提诺的启发,从肉体上升到灵魂,深入灵魂的秘室,在出神状态中窥见“永恒的真理”(《忏悔录》VII,10、17)。而崇党的这段散文诗,似乎可以为奥古斯丁作一最好的艺术注脚,诗人以“火之钥匙层层打开肉体的禁锢”,让不断加持的自由的灵魂,在栴檀香的蒙熏中,深入到人自己的内心,并且随着一脉袅袅的烟雾升腾而起,让罪愆消解,让人类的欲望消肿止热,让爱开始散发出生命本有的香气。诗人彻底挣脱了肉体的羁绊,他所培植的这一棵栴檀树,“喜欢用阳光洗脸,浑身张扬着绿色的芳香。/人类用雾霾为繁华揭幕。但不可否认的是,人类在自己的致幻术中,正越来越多地把自己弄丢。/树的奇香是生命的布施,为尘世放下一架架接引的梯子。”于心灵的致幻术与生命的布施中,诗人美的追求从栴檀树上,我们看到了他使自己美化而非矮化、接引而非践踏的一种努力,美使灵魂把它认作同类,并在岁月的年轮中唤醒灵魂通过它而看到自己的精神本性。
王崇党的散文诗就是这样,他在芸芸众生中找到了自己灵魂的方向。面对黑白,他便是一根点燃的香烛,带着温暖、感恩与敬意;面对洞穴,他能打开新生的出口,让太阳和月亮重新泄漏潜藏于内心的光与影;面对古井,他努力把它做成一只帽子,让天空将它戴在头上; 面对桂树,他想到要秘制一些桂花茶,让路上的人在内心的香气用尽时正好续上;面对月亮,他看见了一座静穆的明亮的空中教堂,让自己寂静的影子,在它下面羞愧地暗着;面对一道旧门槛,他把目光和疑问弯成一束光,让“爱和恨都在外面。斑斓的生,寂静的死”;面对眼罩,因为它的大而不能将它从酸痛的眼前摘下,于是眼罩作为一种多义性的象征符码,又让我们引发出了更多的联想……他说一不二:一扇门、一粒盐、一株高梁、一块石头、一池碧水、一座山谷、一片秋色,都能使诗人在灵魂深处发掘出艺术的生命与美的秘密,或者从有限的偶然的具体物象中昭示出生活本质的无限与必然的内容,“一象之明昧不如悟对之通神”,诗化的物、情化的理、神化的形,都在主与客、意与境、情与理、动与静、形与神的辩证统一中,贯穿着生活的神髓与灵魂的韵味。他喜欢寂静:“我想知道古镇想要告诉我什么,侧耳细听,却又阒寂无声。此刻,我已进入得太深,成为其中轻轻颤动的簧片。/我终究不属于古镇,无法解开巷子深处的死结。”(《阒寂》)、“终南山的茅蓬,是寂静在山腰上长蘑菇”“一个没有寂静可以偎依的人,是一个穷人!”(《穷人》)、“一小块的寂静动起来,就是风。”(《寂静的颜色》)——与“心跳加速”一样,“内心平静”依然可以使诗人找到灵魂的皈依,对此,诗人在《出神》后记中有言:“一小片树林里感受到的和大森林里感受到的,那种让我心跳加速,或让我内心变得平静,总之让我心绪产生变化的那种只可感受的东西,我觉得那就是诗。”以静制动,寓静于动,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寓无声于有声,不仅创造出静谧的意境,而且使之充满了情趣和生机。无论是古镇里的“阒寂”,还是终南山中的“安谧”,抑或是山涧背阴处风的“寂静”,无不源自诗人灵魂之中心智的“流溢”,这“寂静”或许与诗人和谐、平静、冲淡的理想世界互联互通,“一个没有寂静可以偎依的人,是一个穷人!”是啊,心中有了寂静,或能拥有精神的“富足”,寂静就是诗人心中的“神”啊!他崇尚自然:山水杂咀,“山为笔架,水为墨。而我,是那书写的笔。”自然山水在王崇党的诗中亦是那么的“出神入化”——“我的山谷,是一张微开的嘴唇,正轻轻说着我的闲淡与富足。”(《山谷》);“山一开口说话,就口若悬河。/我听不懂,是因为我们之间有着百丈的落差。”(《百丈漈》);“我与自然同在,想见我时,你可以在任一地方召唤我。/不管你是谁,对抗自然,就是与我为敌。”(《我终会分散得让你找不见》),在诗人的笔下,风景远不止是一个自然形态的事物,英国美学家纽拜曾经说过:“风景具有围绕着人的环境性质以及符合、创造或影响人类心情的能力。”(《对于风景的一种理解》,《美学译文2》第18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如果一个风景根据个人的感受对于他是富有意味的,它对他就具有了意义。”(同上,第188页),从“山谷”联想到“嘴唇”,进而听见它说出的“闲淡与富足”;从百丈漈瀑布联想到“口若悬河”与“百丈的落差”,使人联想到“夸夸其谈”以及人与人的隔膜,象喻写作之于自然山水,不仅形象生动,寄慨遥深,山水对于诗人来说,也具有了深刻的意义,难怪乎诗人引山水和大自然为知音,一句“不管你是谁,对抗自然,就是与我为敌。”直率地道出了诗人拜自然为益友、视对抗自然者为敌的一种心声。
“白汲水,灵魂的显影水。/天空是多么好的大宣纸啊,它一页页地覆盖下来,无始无终。/云朵,旧时空里飘过来的柔软扑子,饱蘸时间的墨汁轻轻扑打在生命的底片上。/没有什么能够真正消失。身边的任何物件,都有可能成为某个灵魂复活的介质。/轻轻抚摸着石碑上的字痕,潮水一样随之而来的呼吸与心跳突然就将我紧紧攫住。”(《散落在大地上的拓片·1》),诗人面对“石碑上的字痕”,不禁心潮澎湃,忽发思古之幽情,拓片成为其灵魂复活的特殊介质,白汲水、天空、云朵、宣纸、墨汁,这些身边的“物件”与仰视的“意象”,皆轻轻扑打在诗人“生命的底片”上,旋作灵魂的显影。这章散文诗共有12节,像“无论贫贱富贵,都会被一张黄土纸遮蔽住去路”、“向上生长,也是向下堕落。希望和仇恨一样,都能使深渊受孕”、“刀口缝合时,思想就有了真实的疼痛,医生已为我做出了取舍,剩下的只能靠自己”、“与风相对的是一茎莲荷高洁的心,它突破淤泥高高举起来,一直举过头顶,不摇摆,只用绽放的光芒跳动”、“谷水清幽,生命静静觉照,一颗心,正铺开辽阔的净土”等掷地有声的句子,比比皆是,无不关乎生命、心灵、思想、价值等层面,诗人一方面从客观现实世界中获致美的真正根源,出现在字里行间的是黄土纸、深渊、刀口、莲荷、淤泥、谷水、净土等看得见、摸得着、感觉得到的事物,另一方面,又把自己对美的认识归结为灵魂的神秘的体验,彰显的是贫贱富贵、希望和仇恨、真实的思想、高洁的精神与辽阔的襟怀这些形而上的东西。并非溢美之辞,美的观照是生活的最高境界,王崇党在这些“散落的拓片”上觉照到的,不仅有大地的脉息,更有天空上的亮色,美从何来,当不言而喻。
总的来说,王崇党的散文诗,出神出情,入智入美,思想深邃广阔,艺术感觉敏锐,每每触及到灵魂的纵深、文化的截面和诗性的前沿,明心见性,意味悠远。他的书写打破常道,勇于变局;拒绝重复,寻求差异,在解构与建构中参差与磨砺,显示出了作者少有的锐气与才气,也有力地见证了当下散文诗的丰富可能性。艺术探索永远在路上,珍重啊!最后,请让我用崇党《玄白之思》中的一节诗文,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一想起你,我就有了引力,苹果一样落向你的星球。
每天夜里,我们都试着进入夜的子宫,忘掉世俗的一切,在夜的羊水里净化提纯。
每天早晨,我们都双手合十,感念再一次重生。
生命需要夜的洗礼,也需要太阳这枚印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