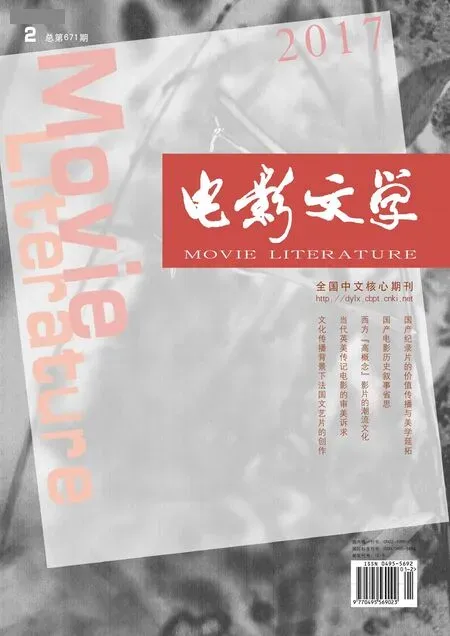中国风意蕴下的《大鱼海棠》
2017-11-16黄慕洲
黄慕洲 曾 光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福建 漳州 510067)
一、中国动画发展历史及现状回顾
纵观中国动画创作历史,第一部动画电影为1926年上海长城画片公司拍摄,万氏兄弟精心制作的《大闹画室》。[1]中国动画元年从此开创,之后上海制片厂首部黑白动画长片《铁扇公主》(1941)问世,在国内外受到好评。[2]1949年新中国成立,上海电影制片厂美术组设立,《骄傲的将军》《山水情》《三个和尚》《天书奇谭》《哪吒闹海》《大闹天宫》《小鲤鱼跳龙门》《神笔》《小蝌蚪找妈妈》等一批佳作在此后30年内被创作,获得海内外的赞誉,开创了中国动画民族化道路。之后,受市场经济冲击,国外动画侵入,中国本土动画创作转入低谷。直到1999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制作生产的《宝莲灯》出现,成为中国动画市场化的开端。2009年根据动画电视改编的动画电影《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牛气冲天》获得近亿元票房,开创了用动画电视系列片培养动画电影观众的新模式。之后连续几年,中国动画电影都保持着较高的票房纪录,逐渐形成了动画贺岁片寒假档期、暑假档期和国庆节档期等。
2014年1月,国产动画电影《熊出没之夺宝熊兵》上映十日获得票房1.7亿,又一次刷新国产动画电影票房纪录,中国动画电影成为电影票房的新生力量。2016年7月,导演梁玄和张春经过十余年艰辛创作的《大鱼海棠》终于上映,此片融合了中国上古神话传说和古典元素,被主创称为一部“极具东方意境、韵味与神秘感的电影,我们希望它能成为中国动画电影走向世界的起点的电影”。
目前,关于《大鱼海棠》的研究,鲜有深度剖析的学术文章发表,少数的几篇集中在其场景构造的评述、众筹的作用。本文在梳理中国动画发展史及其局限性的基础上,从母题、美术、制作以及其他中国元素等几个方面,探索《大鱼海棠》的中国风意蕴及其在中国动画中的重要性。
二、中国风意蕴下的《大鱼海棠》
(一)母题:人性、爱、牺牲和救赎
人性:作为反映社会人生的艺术形式,电影在发挥娱乐功能的同时,具有教育和影响的功能。动画电影,虽并非完全以儿童为中心人物,观众也不完全指向儿童,但相对其他类型电影,其拥有较多的儿童(及其父母)受众。遥远的时代或梦幻般虚无缥缈的仙境为此类电影提供了宽广的想象空间和叙事场景。《大鱼海棠》也不例外,大海本身的虚无缥缈,海底神秘的环境,人物和观众身份、生活氛围的同一,创造电影叙事的现实感、逼真感,来增加影片的艺术感染力。
影片首先在片头就区分了两个世界:一个是人类世界,另外是处于海底既不是人也不是神却掌握着人类灵魂的“他者世界”。对于人类世界的展现十分短暂,整部影片的大量笔墨放在了刻画海底的他者世界上;这个世界中的生物要经历“16岁的成人礼”,彼此有人类间的亲情,例如椿的祖父母间的相濡以沫的感情,椿的母亲对她的保护与管制,湫对于椿如兄长又如恋人的关爱,通过交易而延长“生命”长度的鼠婆和汤婆。这些海底的“他者”的关系模式很大程度上是人类之间的模式,到最后湫成全椿的方式是牺牲自己整个长度的生命,换来椿进入真正意义上的“人类世界”从而和恢复成人形的鲲一起生活在人间,影片通片包含着对人类世界的向往和对人性的歌颂。
爱:跨种族的爱恋。基于上文两个世界和两个种族的划分,此动画电影的爱情主线进入了经典的跨种族恋爱模式。类似的电影在国内外都可见,例如《美女与野兽》 《金刚》、《暮光之城》系列电影以及俄罗斯电影《他是龙》。此类爱恋关系一般可以在神话故事中找到原型,例如,美人鱼电影可以追溯到安徒生童话《海的女儿》。延续这一爱情模式,海底“其他世界”中的椿与人类男孩的爱恋,也经历了跨种族到统一种族的过程。开始时经历16岁成人礼通过“通天隧道”进入人类世界的椿是一条鱼,被人类男孩解救后爱上这个人类男孩;男孩为救他而死,进入椿的“他者世界”并且灵魂化为一条鱼,名为鲲。紧接着椿为了让鲲能恢复人形,历经艰辛,面对亲情的矛盾,最终化为鲲的同类——人。这样的情感通过电影的视觉化展示,成为童话电影的有机组成部分。如阿恩海姆指出的,“艺术家与普通人相比,其真正的优越性在于:他不仅能够得到丰富的经验,而且有能力通过某种特定的媒介去捕捉和体现这些经验的本质和意义,从而把它们变成一种可触知的东西”[3]。
“爱”的母题贯穿情节发展的整个过程。除了贯穿全电影的椿与鲲的爱情主线,还有一些附属感情线,例如,椿的祖父母之间相濡以沫的感情,椿的父母对椿的亲情,以及湫对椿超越亲情却无法达到爱情的眷恋和保护。影片超越一般叙事作品之处在于,它既分别表现了人类世界与“他者”世界的“爱”如何成为以“类”相区别的特定世界人物关系的基础,又使“爱”成为沟通两个世界的纽带和桥梁。“爱”所指称的就不是局限于某个地域乃至某个世界的人物之间的亲情与关爱,而超越一般意义,在情节发展过程中得到了更高层次的升华。
牺牲和救赎:椿为了鲲不惜牺牲自己一半的生命,不惜经受家族的责骂;湫为了椿的幸福,愿以生命和自我为代价赋予其人的生命和与鲲一起在人间生活的权利;在“爱”的大主题观照下,牺牲和付出显得自然而然,又让人为之动容。
(二)美术设计
1.人物设计
影片人物的衣着汇集了很多中国元素。例如,椿的服装中可以看出民国时期的学生服的影子。几个法力高强的长者都身披飘带,身穿宽松的长袖古代服饰,体现人物的年龄和地位,这是从我国古代绘画中得到的灵感。鼠婆子脸上的妆源自京剧中丑角的脸谱;灵婆掌管灵魂,权力巨大,所以头戴鳞片帽,腰间革带,多少能看出点官服的影子。其他辅助道具如斗笠、油纸伞、灯笼、蚕丝织布、粽子等具有独特中国风的物品都是其文化特色的体现。
2.场景设计
片中“其他人”生活的场景借鉴了福建永定土楼。福建当地人为了维护家族的共同利益,让众多的宗亲几十人或几百人聚族而居,以使家族兴旺,抵御外敌,便建造了殿堂式的土围楼以及方形、圆形等丰富多姿的土楼。土楼融合了“天、地、人”的元素,将地和人围在一个圆形的通天空间里。影片中的主楼以承启楼为原型,承启楼是福建土楼中规模最大的圆楼。于是影片开篇在土楼举行的成人礼,颇有一种中国传统文化里宗族仪式的味道。
3.色彩
在《看电影的艺术》一书中,作者约瑟夫·M·博格斯(Joseph M.Boggs)从色彩的表现主义用法、作为象征符号的色彩、色彩的超现实主义用法、色彩的主题反复、色彩有助于增强情绪等12个方面总结了色彩在电影中的作用。总结而言,在电影中,色彩的确能起到体现时空转换、创造情绪意境、刻画人物形象、烘托影片气氛、表现思想主题等作用。颜色是影片的艺术风格的构成部分。在色彩使用与传统的颜色表达方式不一致时,色彩主观性被体现,色彩的情感作用得到表达。
大的色彩基调是红配蓝,全片有600多个色彩指定。即使在同一场戏里面同一个氛围下,根据景别的区分色彩也是有细微差别的。影片开头和结尾为冷调的蓝,指代具有深邃包容特性的蓝色海底世界;中间椿的服饰、鲲的色调均为红色,湫在赋予椿人类生命时服装为红色,康定斯基说:“世界上有冷的色彩,也有暖的色彩,但是任何色彩都不具备红色强烈的热力。”[4]可见导演在涉及“生命”“新生”等话题时有意用红色作为象征。和椿与鲲以及影片中的其他“年轻形象”形成对比的是湫,几乎和椿同龄的他的发色是白色,在色彩的加色体系里,白是各种色彩加在一起后的统一体,是色彩最丰富多彩、最圆满的终结状态。在另一面,白色缺乏色彩,在白色上无法看到任何色彩的倾向性,是活力和纯洁的体现。[4]导演通过这样的颜色区分塑造出了一个极具活力、心灵纯洁,为了椿勇于自我牺牲的湫的形象。
另外,灵婆与鼠婆子人物塑造上色彩较为丰富,黄色衣服,白色脸,黑色眼睛。马匹为黑马、白马两色,无生命的中国麻将也注意到了传统色彩搭配,使得影片在主基调一致的情况下也具有适时的色彩变换,不至于让观众在90分钟左右的观影过程中产生视觉疲劳。
另外,这是因为导演张春希望整个片子不管是色调,还是其中任何细节,都稳定、不轻飘。
(三)制作
全片以人物为主,运动规律都比较接近现实生活,情节以感情为主,动作比一般的动画片要细腻,导演的要求是表演不能过度,不能卡通化,一定要微表情,小动作,写实挪移。例如,椿听说换回鲲生命的代价是她的眼睛,这一刻时,她的眼神有细微变化。又如,在影片中段,鼠婆子预言鲲将来是条大鱼时的表情,以及后面将手伸进光柱,由于魔咒的作用指甲被光融化了,之后有一个复杂的表情,表现出鼠婆子向往回到光明人间但又有咒语在身的无奈心态。这些细微的动作和表情在动画上增加了难度,因为动画是线,每根线条都是艺术家提炼概括后的结果,颜色一般只有亮面和阴影两种颜色,失去了现实中的体积感,所以越是心理活动的微动作越难表现,很容易崩型。
(四)后期特效、手绘特效
全片的火焰和水全部使用手绘特效,每一颗水珠的大小,包括海浪上翻起的浪峰、阴影部分、高光大小,在比例上都要有所控制。张春导演对火焰的运动规律也要求要有仙气,有流畅的感觉,是S形上升,包括火焰外细小的碎裂,也会形成流线型的飘散趋势,说到底就是要延续一个中国传统绘画流线型飘动方式的逻辑。雨和雪也有大小,层次感、明暗都需要做出真实的精神和层次。其中巨海棠一场戏中,雨效做了620层。
(五)其他中国古典元素
影片中墙体的对联与每个角色的性格相对应,没有重复。如灵婆所在的如升楼门口悬挂的对联,切合了如升楼主人的身份。门前的对联是这样写的:“是色是空,莲海慈航游六度;不生不灭,香台慧镜启三明。”对联取自清代乾隆皇帝御书北京雍和宫法轮殿联。法轮殿是僧人诵经说法之所在,旨在宣扬佛教生死轮回、万象皆空之理。联语上“是色是空”,即是佛教之语。“色”与“空”分别指称物质的形相及其虚幻的本性。佛教常说的“色即是空”指一切事物皆由因缘所生,虚幻不实。佛教常说的“色即是空”指一切事物皆由因缘所生,虚幻不实。“莲海慈航”“香台慧境”同属于佛教用语。对联放在这里,和如升楼掌管人类灵魂的功能非常契合。
人物名称上,鲲来自于《庄子·逍遥游》:“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椿、湫两个人物的名称同样在此书中可见出处:“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另外,白泽为中国古代汉族神话传说中昆仑山上著名的神兽,后土、句(gōu)芒、嫘祖、赤松子、祝融、瞿如等人物均可以在《山海经》等古典名著中找到原始出处。甚至场景道具中的束综提花织机、箜篌,如生楼、梯田等,均渲染着浓郁的中国风。
三、结 语
在爱和救赎的主题观照下,《大鱼海棠》以极具中国风的笔墨,勾勒出了一个既非人也非神的他者世界,其中极具张力的人物关系矛盾和故事冲突,最终指向人性。影片充满着对人类世界的向往,闪烁着人性的光辉和对人类的歌颂,集教育和娱乐功能于一体,是中国动画史上不可多得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