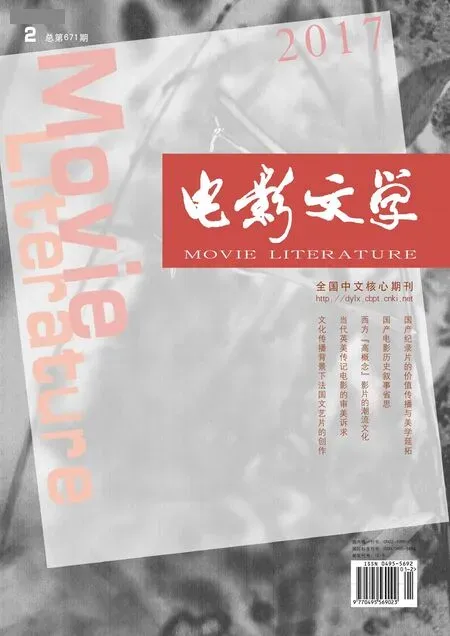国产电影历史叙事省思
2017-11-16刘明
刘 明
(白城职业技术学院,吉林 白城 137000)
“历史”是电影艺术创作的重要素材提取对象和灵感来源,以历史为创作素材与叙事基础的电影具备多种类型化方式,如史诗电影、传记电影、战争电影、爱情电影等,历史在不同的类型化创作的诠释下,呈现出不同的面相。现如今,商业文化和消费文化大行其道,电影市场经历多年的发展低谷后,重新迎来了大跨越的发展。可以说,电影艺术在21世纪再次迎来了黄金时代。但是,对于电影艺术来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糟糕的时代”——电影艺术的繁荣与发展造成了电影创作的良莠不齐,商业利益的放大也使得电影艺术的商业气质越发突出,众多电影人纷纷告别了艺术电影创作,转身投奔商业电影。然而,电影艺术的商业化,导致消费历史现象的出现,即对历史的扭曲、消解、娱乐化和后现代处理,竭尽所能地发掘其中的商业价值和娱乐元素以及其功能性,历史逐渐成为一种叙事的工具。近年来的国产电影在历史题材方面的创作,泛娱乐化成为主流,历史已经不仅仅是创作的内容和素材,而是作为一种叙事和表达的工具广泛存在。
一、被消费的历史
后工业时代的到来促使商业文化日益兴盛,商业电影市场呈现井喷式繁荣,观众在物质生活日益富足的情况下,急需精神消费品缓解工作与生活的压力,满足日渐匮乏的精神需求。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走进电影院去消费电影,如此消费文化的兴起带来的是电影的愈加商业化和娱乐化,艺术电影日渐式微,娱乐电影(大众电影)成为主流。商业文化和消费文化促使电影创作者将越来越多的娱乐元素融入电影当中,竭尽所能地创造商业电影的娱乐属性。
但是,不仅局限在中国,对于世界范围内正处于黄金时代的电影艺术来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糟糕的时代”,这一说法再合适不过。“最好的时代”是指后工业时代带来的精神消费的兴起,电影院线再次迎来了大批的观众,电影票房收益呈现直线上升的趋势,观众对精神消费品的巨大需求促进电影艺术的快速发展。毫无疑问,电影艺术创作的大环境是优越的,电影艺术的黄金时代已经到来。“最糟糕的时代”是指后工业时代带来的消费文化和商业文化,迫使精英文化下台,大众文化成为主流文化,艺术家为了追求眼前的财富和利益,纷纷投奔商业文化和消费文化的怀抱,泛娱乐化的艺术创作顺势而生,越来越多粗制滥造的作品涌现在市场上。因此,电影艺术无疑正处于一个复杂而特殊的时代,大环境使其处于充满矛盾的发展状态之中。
在泛娱乐化的时代,人们对于历史不再抱持一个严谨和严肃的态度,而是尝试以各种方式“消费历史”。因此,我们看到历史被肆意地扭曲,以娱乐化的方式呈现本应严肃对待的史实,以美其名曰“后现代主义”的方式对历史进行拆解、重构、甚至消解,不知不觉间,历史也成为电影艺术创作中的娱乐元素,成为被大众消费的对象。于是,电影市场中涌现出一批取材于历史的商业电影和娱乐电影,为观众讲述着不一样的历史,甚至会在观众不了解这段历史的情况下,歪曲观众对历史的认知。同时,碍于电影院线的票房压力,一些电影会攫取历史的视觉元素,将一段历史以奇观化的方式呈现,以适应观众对于视觉奇观电影的心理诉求。最终,历史只能化作银幕上奇观化的视觉片段,完成商业电影的惊奇叙事,造成历史在观众心里的扭曲和变形。
二、历史的文艺空间化
在消费文化的语境当中,历史已经不仅仅是电影创作的素材来源,更多的时候,特定时期的历史已经被艺术提炼并符号化,被赋予了更深层次的艺术内涵和美学意蕴。由此,历史的文艺空间化成众多商业文艺片的创作方式,将特定时期的历史进行刻意的截取,构成一个具有时代气息和复古美学韵味的文艺空间,给予观众独特而深刻的审美体验。
对于历史的文艺空间化,张婉婷导演的电影《三城记》是众多以历史为题材内容的电影中较为典型的例子。历史,成为电影《三城记》主要的叙事工具,特定的历史时期、时代背景赋予了这段关于父辈的爱情故事特定的底色,战争历史不仅是这段爱情故事的特殊标记,更是给这段爱情故事以审美内涵的重要因素,因为这段历史,这段故事才能令人印象深刻、感人至深。历史赋予了三座城市不同的时代特征,虽然同样是在战火纷飞的时代,三座城市却各自有着不同的风貌和底蕴,安徽—上海—香港,相遇—分离—相聚,三座城市对应着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中国不同地域的不同风貌,虽然同样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之下,却各自呈现不同的景象,而这三座城市也对应着房道龙与陈月荣爱情故事的起承转合,历史给这段故事以底色,历史的发展成为牵连故事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更重要的是,导演张婉婷将历史文艺空间化,将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中国社会进行审美提炼,挖掘出历史和时代赋予人们的精神面貌和神韵气质,透过历史舒展故事情节和人物命运、情感纠葛。因此,即便是在表现战争的惨烈镜头时,导演张婉婷仍然利用滤镜将镜头画面的颜色改变,利用忧郁的蓝色表现战争的无情和情绪的崩溃,镜头中看不到猩红的流血画面,在特殊处理的画面中,呈现了一个独特的艺术空间,片中人物和片外观众的情绪都笼罩在这样的空间当中。经过特殊艺术处理的历史空间,极端的情绪化和浪漫化,并非一味地强调历史的惨痛经验,而是强调身处其中的人们有着怎样的情感体验。同时,这种处理也是符合商业艺术电影的创作精神的,能够创造不一样的审美体验。
同样将历史文艺空间化的成功作品还有吴宇森的《太平轮》,同样反映的是20世纪40年代的战争历史,却呈现出与张婉婷的《三城记》截然不同的审美倾向。吴宇森同样将这段历史看作一个文艺空间,甚至这个空间与张婉婷的《三城记》相比较,显得更加封闭。张婉婷更深入地挖掘了那个年代的人们的艺术气质,无论是他们看待爱情的方式,还是表达并追求爱情的方式,都有着截然不同的审美趣味。而吴宇森借电影《太平轮》更加深入地发掘了这段动荡的历史对人性的深层次影响,吴宇森构建的关于20世纪40年代的文艺空间除了有着浪漫主义的审美趣味,更有着一层现实主义的惨烈和真实,封闭在这个空间中的人们既有不切实际的浪漫幻想,同时又无比脚踏实地地勇敢生活,吴宇森将那段历史给予人们的不安定感和伤痛定义为“浪漫的活着”。导演吴宇森同样是从历史中萃取出文艺美学的元素,拍摄了《太平轮》这样同样有着商业电影特征的艺术电影,商业性与艺术性二者兼具的艺术特征,也让该片的历史叙事表达存在多样性特征,在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游弋。
如今,历史的文艺空间化已经成为历史题材叙事表达的一种方式,历史被符号化和工具化,从中被提取出美学特征和审美价值,以恰当的方式与商业电影创作相结合,最终实现历史叙事的创新表达。
三、娱乐化与狂欢化的历史叙事
商业文化与消费文化将电影艺术彻底推向了大众化和娱乐化的范畴,历史题材电影的娱乐化和狂欢化也成为当前此类电影的主要创作方式,如何从历史中挖掘出娱乐元素和奇观化影像故事是当代导演着力研究的方向。夸张已经不足以成为商业电影导演处理历史的方式,传奇化和奇观化才是当前商业电影导演对于历史的处理方向。
在现阶段的商业电影当中,娱乐化与狂欢化的历史叙事仍然主要集中在抗日题材电影上,过分地夸大中国军人的作战能力,肆意贬低、诋毁日本军人的人物形象成为主流的创作趋势,如此一来,中国军人和日本军人都在抗日题材电影中实行了脸谱化塑造。但是,现阶段狂欢化的抗日题材电影,又不同于早年姜文执导的电影《鬼子来了》。这部改编自小说《生存》的狂欢化、荒诞化电影,将小说中描写的悲凉与无奈化作荒诞的黑白影像呈现出来,《鬼子来了》的狂欢、荒诞与戏谑是一种反讽与无奈,是正视历史、直面人性的一种艺术考量和处理。但是,在现阶段的“神奇抗日”影视剧中的狂欢化、奇观化,就彻头彻尾地代表了这些影视作品的娱乐倾向,本应严谨、严肃、正确、正面对待的抗战历史,却沦为消耗民族情绪、片面地表达爱国情感、刺激观众的娱乐神经的娱乐化内容素材。
导演陶明喜执导的电影《嗨起,打他个鬼子》就以诙谐幽默的方式呈现了1938年贵州少数民族英雄抗日的故事。该片全片利用怪诞的处理方式夸大了日本兵的丑陋嘴脸,过分夸张、夸大了中国人民的作战智慧和能力,人物形象的脸谱化和扁平化,在几乎没有中间过渡地带的正义与邪恶之间得以表现。虽然在极端的“好人必胜,坏人必死”的故事模型中,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民族情绪和革命意志被淋漓尽致地表达,但是抗日战争的艰难、无奈,正确的历史并没有在影片中呈现,虽然抗日战争最终赢得了胜利,除去结果的整个过程历史仍然需要被正视。
在管虎导演的电影《厨子戏子痞子》中,这种对历史的娱乐化和狂欢化得到了更加极致的处理和表达。片中将一段抗日谍战历史进行了后现代的夸张处理,戏中戏的结构将这个荒诞、夸张的故事巧妙地表现出来。虽然电影当中并未出现“抗日神剧”中经常出现的“手撕鬼子”“以一敌百”的奇观化剧情,但是四个爱国青年与日本士兵斗智斗勇的充满黑色幽默的荒诞故事仍然极端娱乐化与奇观化。导演管虎企图利用这样一个充满黑色幽默的抗日故事,表现抗日战争过程中中国军人的过人智慧、战斗能力和忘我的爱国情操,夸张与荒诞地演绎凸显抗日的艰难。但是,剥离表面的这种以爱国情怀为最高准则的创作方式,管虎深层次的创作动因仍然是通过这样一个看似荒诞离奇却构思缜密的故事,通过消解历史、重组历史来构建一部奇观化的电影,中国军人的“高大全”、日本兵的“矮丑愚”依旧是《厨子戏子痞子》中的创作核心。
四、结 语
当今的国产电影对历史的处理方式多种多样,历史被发掘出更多的功能性特征,历史叙事功能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叙事功能,而是在美学提炼、艺术加工、娱乐化、奇观化处理之后,生发出更加多元化的功能和意义。商业文化和消费文化促使娱乐电影日渐强大,正史的消解与野史的放大成为这些娱乐电影看待历史的主要视角,如何能够从历史中挖掘出更丰富的娱乐元素,进一步刺激观众日趋疲惫的娱乐神经并迎合观众日新月异的审美趣味,也将会是这些以历史为创作素材的商业电影的主要创作方向。面对当下国产电影历史叙事的诸多特征,我们亟需做出深刻的艺术省思。电影艺术取材于生活且高于生活,一味地扭曲历史、消解历史是否违背了电影艺术创作的艺术真实的根本,是否会影响到观众了解历史、理解历史、铭记历史,以及日后历史的书写和传播,都是值得中国电影人积极思考的现实问题。虽然新世纪的中国电影已经走进商业电影的大时代,票房收入成为众多电影人电影艺术创作的最高目标,但是作为艺术家的艺术自觉,电影艺术本身的大众文化传播的艺术责任,都应当被重新审视,并吸纳进影视艺术的创作当中,在严肃历史和娱乐历史之间寻找到一个表达的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