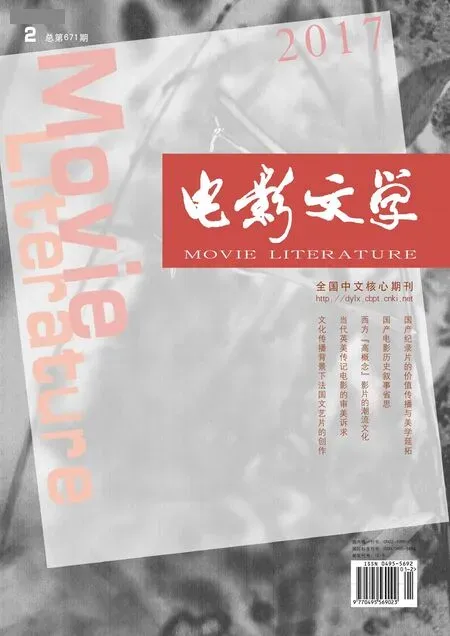《风之谷》中的文学叙事研究
2017-11-16蒋乡慧丁景辉
蒋乡慧 丁景辉
(1.应天职业技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2.南京森林警察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动画大师宫崎骏的文化传奇今天已经人所共知,他被誉为“第一个把动画上升到人文高度的思想者”。而动画电影《风之谷》作为第一部来源于宫崎骏自己创作的同名漫画而且全程亲自制作的电影,无疑是最能体现宫崎骏人文思想中环保主义、和平主义和女性主义这几个最重要的思想标签的。显然,国内大部分对宫崎骏这部电影的解读都是从这几个角度展开的,也有极少数研究另辟蹊径,从阴阳五行和突破虚无主义等角度创造性地理解这部内涵丰富的影片。从岛国思想、民族性或自身文化传统的一般性解读略显庸常,相比之下,对《风之谷》中大量借鉴的异国元素的分析有助于把握《风之谷》的丰富性和多层次性。
根据现有的研究和宫崎骏自述,《风之谷》的主角“娜乌西卡”的名字借用自荷马史诗《奥德赛》中一位公主的名字。在伊维斯林的《希腊神话小事典》中,记载着她具有不可思议的亲近大自然和自由驾驭飞行的能力。“娜乌西卡”这一形象也与传统名著《提中纳言物语》和《爱虫姬君》中都讲述的一个名叫“爱虫公主”的贵族少女的故事一致,这个少女因对蝶虫的喜爱与感动被世人视作怪人。在叙事背景上,沙漠场景可能参考了美国的科幻文学,战争场景参考一些二战历史电影,魔法、奇幻元素似乎参考了好莱坞科幻大片《星球大战》。这些素材元素的挖掘体现了电影《风之谷》不同的立体侧面,但多是细节性和局部性的,在对全局性的情节设计和角色设计方向的挖掘略显乏力。
本文将揭示一个《风之谷》研究中被忽略的全局性借鉴,即电影《风之谷》中全局性的救赎叙事模式是借鉴基督教圣经弥撒亚式的叙事模式,换言之,也就是《风之谷》救赎叙事与基督式的救赎叙事高度同构。这种叙事模式作为一条隐线躲藏在环境或和平这些电影的显性主题背后,其研究至今不被国内研究提及。从创作的角度来讲,这一救赎叙事的同构性无法在创作动机上完全还原出来,因为宫崎骏本人从未如此提及。虽有研究提到电影《风之谷》宗教色彩的地方,也仅仅限于电影结尾复活部分。事实上,电影版《风之谷》仅仅是史诗般的漫画《风之谷》的三分之一,电影版的大量情节和细节为了适应电影题材而做了不同于动漫的大量改动,结尾几乎是临时加上去的。考虑到宫崎骏自己的左翼色彩,很少有人考虑到他的创作会全局性地借鉴宗教元素,尤其是基督教的叙事。但是将《风之谷》作为独立的电影来看,它的确自觉不自觉地在救赎模式上与基督教的弥撒亚式的叙事同构,这在下面对电影本身的解读中将一一呈现。
一、从角色身份设计看电影《风之谷》的弥赛亚叙事
弥赛亚救赎叙事的核心是救赎者。电影《风之谷》的主角娜乌西卡无疑就是这样一个用自己的生命救赎风之谷乃至整个世界的救赎者,她的使命与圣经中的弥赛亚基督相似。
所谓“弥赛亚”就是希伯来词Mashiah(受膏者),上帝拣选出来委以特殊重任者,会委派先知用香油膏抹他的头,成为上帝选立的救世主,翻译成希腊语就是基督。新约圣经就是在证明,基督就是那个自愿走向十字架用自己的生命救赎世人的耶稣。圣经赋予基督三重身份:先知、君王和祭司。先知就是把上帝的话,把世界的真理揭示出来的角色;君王身份指的是耶稣既是上帝之子(神子)又是大卫王的子孙(人子),是未来天国之王,会治理看顾他自己的新以色列百姓;祭司身份指的是他是人与上帝之间的中介和桥梁。世人皆犯罪,得罪了神,唯独弥赛亚是无罪的圣洁的圣者,他来以无罪的代替有罪的,以自己的受难和死亡来平息上帝对罪人的愤怒和惩罚,用自己神性的生命来赎回犯罪的世人,实现神与人重新和好,完成对人的救赎。
对比电影《风之谷》中的核心人物娜乌西卡就会发现,她几乎就是基督原型的翻版。娜乌西卡形象就是完美无瑕的,她勇敢机智、认真细致又积极进取,她仁爱怜悯、善良无私、热爱和平、宽厚包容和勇于牺牲。在她身上,几乎找不到任何缺点。她与身边贪婪、凶残而又自负的多鲁美奇亚帝国的库夏娜,阴暗猥琐、自私而冲动的培吉特人,以及甘于保守自保的风之谷人等形成鲜明对比。她完美得不像常人,几乎就是一个女神,与无罪圣洁的基督形象完全吻合。作者也全局性地为娜乌西卡准备了基督原型的三重角色:第一个角色是真正的先知,发现腐海秘密的先知。为突出这个角色,电影专门配置了一个世人公认的先知犹巴作为对比陪衬。电影中的独行侠大师犹巴,就是腐海秘密的探索者,真理之道的追求者。他一次次惊叹于娜乌西卡与自然大地相处的能力,就是为了反衬出基督式的真先知揭示真理的能力。娜乌西卡在自己的地下实验室轻易解决了犹巴一生探寻的腐海难题。第二个角色是祭司。如果说大自然腐海就是上帝,娜乌西卡恰恰是和谐沟通环境与人的唯一中介。耶稣的祭司角色是追求人与上帝的和解,平息上帝的愤怒,而娜乌西卡则是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解,平息自然大地的愤怒。为突出娜乌西卡这个真正的祭司角色,也专门配置了一个风之谷的祭祀祖奶奶角色作为对比陪衬。祖奶奶仅仅能体察自然的气息和愤怒,却无法使人与自然和解,而娜乌西卡可以。第三个角色是君王,指向娜乌西卡作为国王基尔的公主身份。在国王死后,她事实上就是风之谷的王,是其百姓热切拥戴和热爱的王者。为突出这个角色,也专门配置两个“君王”,即自负而暴力的多鲁美奇亚公主库夏娜和冲动的培吉特王子阿斯贝鲁,来对比烘托王者娜乌西卡的善良、宽厚、智慧和能力。以这三重身份和无罪的状态来研究娜乌西卡就会发现,她的这三重身份几乎关联和统一整个叙事的各个层面和各个重要配角,各个层面的支线都被统一安排到这个基督原型的塑造上来。
二、从背景和情节设计看电影《风之谷》的弥赛亚叙事
末世论秩序,预言与应验模式,超理性悖反模式以及圣经救赎叙事情节中经典的四重节奏,是圣经救赎叙事独特的全局性特征。而它们几乎全部为电影《风之谷》的叙事所采用。
圣经中的末世论叙事几乎举世皆知,整个圣经的基督叙事都在天国临近和审判末日临近的危机气氛之中,而这种危机时刻临近的气氛又处在亚当堕落后人类普遍困于有罪并受诅咒的痛苦阶段中。堕落—痛苦与危机—拯救之路—最后审判,构成一个线性时间秩序,这一时间秩序都置于整个末世论秩序背景中。电影《风之谷》也在一开始就建构了一个类似的末世论秩序背景。故事发生的千年之前,人类因为破坏自然和滥用暴力,在“七日之火”战争结束后,繁华的文明崩塌。此后千年,仅存的少数人类即将被栖息着虫类的广大森林腐海所征服,空气中弥漫的毒气腐蚀了人类的健康。各国都在设计道路寻求拯救之路,但危机步步紧逼,一个又一个国家被腐海吞没,《风之谷》的故事建立在类似的末世论秩序中。
预言与应验模式是整本圣经的基础叙事模式。在新约中,旧约大量的预言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应验,例如,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时说出的诗篇22篇的诗句,这些诗句暗示十字架上受难受死的大量细节,新约对此处的记载就应验了旧约诗篇22篇的大量预言。这种预言与应验模式带来一种独特绮丽的效果,指向了神秘背后的崇高和神性,是救赎叙事最为经典的模式之一。电影《风之谷》中,风之谷的祭司祖奶奶提到在“黄金草原上的蓝衣圣者”来拯救人民的预言,这预言很明确地为祖奶奶和大师犹巴所相信,并在最后出人意料地在他们熟知的娜乌西卡身上应验。这种应验使得救赎叙事中出现“草蛇灰线,伏脉于千里之外”的意外效果,使得整个叙事的有机整体性、层次感和立体感大为加强,也为人们带来意外的震撼效果。
超理性悖反模式是圣经独特的救赎叙事模式之一,被置于救赎教义的核心地位。它意味着真理的出现一定是以超出理性和常理的形式出现,呈现出悖反性。超理性的悖反性是人类能力限度的体现,是真理和人性冲突的最高潮之处,也是真理出现的最一般形式。在圣经中,耶稣明明是最强大和荣耀的神,却以最卑微、最屈辱的方式出现并在十字架上受难受死,这就是最大奥秘和悖反,是人类理性本身所无法预料和相信的。因此,接受上帝唯独依靠信心而非人的理性。在圣经叙事中,耶稣的家乡人因着对他的熟悉而拒绝相信他是基督;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虽然明明看见他施展神迹,但强大荣耀与卑微屈辱至死的反差和悖反,使他们根本无法相信他就是弥赛亚,他们到死都相信弥赛亚应该像历史上的大卫王那样是有着军事政治上的外在辉煌的君王。这种内在紧张的叙事手法同样不断出现在电影《风之谷》中。当所有人都以为预言中拯救的圣者是男性且来自远方时,没有人想到圣者就在身边,而且是柔弱的少女。所有人都看好大师犹巴的智慧和祭司祖奶奶的能力时,没人想到年纪轻轻的娜乌西卡的关于腐海的智慧远超犹巴,她与自然和虫类的体察沟通能力远胜祖奶奶。最后的拯救不是靠多鲁美奇亚的暴力或有着原子弹威力的巨神兵,不是靠培吉特的残忍和阴谋诡计,而是靠少女娜乌西卡那柔弱的爱、怜悯与牺牲。这牺牲在庞大的王虫冲击群面前看上去极其渺小,但与自然和解的威力却远远胜过巨神兵原子弹一样的火力。超理性悖反模式让救赎叙事的戏剧性极其强烈,更强化了电影《风之谷》的救赎叙事。
在圣经的救赎叙事中,明确地分为卑微的道成肉身、受洗、受难死亡、复活做王的叙事四重节奏。令人惊讶的是,电影《风之谷》中也有很明显的类似四重节奏。娜乌西卡虽然没有道成肉身的情节,但她对童年的几段回忆构成第一重节奏;她和阿斯贝鲁在腐海的底部洞彻腐海的全部奥秘并第一次被王虫金色触须包裹,如同圣经中耶稣第一次受洗被上帝从天上降下的圣灵充满的情节相似,构成第二重节奏;娜乌西卡救小王虫的受难,主动降落在王虫冲击群前面的牺牲类同耶稣主动走向十字架的受难受死,构成第三重节奏;娜乌西卡被王虫群的金色触须包裹并复活与耶稣被上帝复活高度相似,构成第四重节奏。从此可以看出,二者关键点的叙事节奏几乎完全一致。
至此,电影《风之谷》和救赎叙事与圣经的弥赛亚叙事同构已经清晰呈现。毫无疑问,这种同构与个别场景,名字或魔法之类的元素相似相比无疑是全局性和结构性的,这有助于我们理解宫崎骏电影《风之谷》的立体性。
三、弥赛亚救赎叙事背后的启示与溯源
这种同构的叙事情况可能是宫崎骏创作中不自觉的作为,或者受圣经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或者是环境主义自然观内在逻辑的流溢。一方面,好的叙事固然是为了讲好这个救赎故事,那些经典的救赎叙事模式用到极致必然相似;另外一方面,弥赛亚救赎叙事的设计背后,宫崎骏将自然神性化和神圣化的思想在对比中呼之欲出。在这种与基督教圣经高度同构的叙事中,叙事背后的价值指向暴露出来。自然取代上帝成为环境主义者背后新的神,它能够与人类互动,它要求人顺服,渴求新的人神和好。如果熟悉思想史,不难发现对自然赋予神性的思想,在近代19世纪泛神论那里已经成形,滥觞于自启蒙中走出的浪漫主义者,如华兹华斯、柯勒律治等。在浪漫主义者不再相信基督教的上帝后,他们不难在寂静而涌动的自然中发现新的上帝。在宫崎骏温暖人心的《风之谷》背后,那闪现的浪漫主义身影也渐渐浮现出来,虽然《风之谷》的救赎叙事与圣经一样,但救赎背后的上帝已经不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