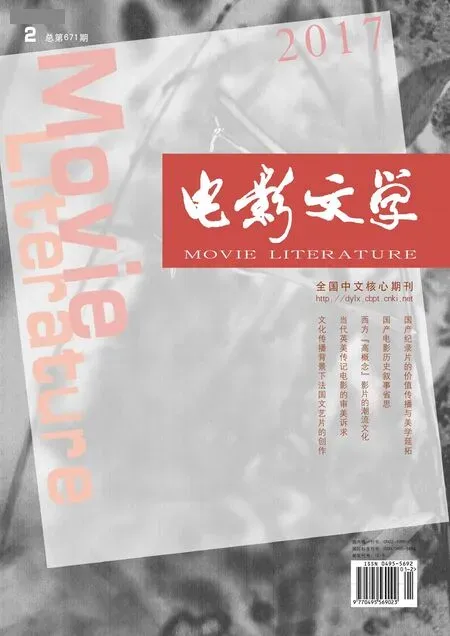霍建起电影的视觉语言分析
2017-11-16唐旭军
唐旭军
(桂林旅游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在当代电影导演中,霍建起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存在。他沉默,低调,韬光养晦,为当代中国影坛贡献了诸如《那山那人那狗》《暖》等具有多重阐释空间又别具一格的艺术文本。霍建起电影中常常散发出一股只属于东方的幽远和飘逸感,镜头渲染出的光影细致、考究、含蓄,犹在画中,显出浓郁而真切的中国风味,给本土电影带进新鲜的风气和独特的景象。可以说,其作品中对于视觉语言的把握和掌控,借助视觉语言对“乡土中国”的讲述,具有经典的垂范意义。
霍建起实可称得上是一位典型的“作者导演”。视觉语言的编制与呈现是其最大的印记。他所有的秘密几乎都隐藏在视觉语言、光影的编造之中。本文试从技艺、效果、容受三个角度,对其特质做简单论述。
一、视觉语言的技艺:摄影美学与蒙太奇技术
霍建起的镜头语言和画面呈现,有着别具一格的风范。在他的电影里,摄影机不再只是一个工具,而是和他的视觉世界合为一体不可须臾分离之物。画面的每一次转换,镜头的每一次运动,影像之中的那些层次复杂的山水、小桥、树木、矮屋、麦子、河流,乃至人物的一衫一履,都在不断地改变着景深,给予画面复杂的空间分隔和纵深,巧妙地规避一般影视因为日常、农村题材限制而带来的平面感。这是独属于霍建起的摄影美学和蒙太奇技艺。
首先,霍建起造就了东方电影摄影美学的新典范。他的电影,摄影机的运动无处不在又无声无息无影无形,真正的浑然天成、举重若轻。霍建起的电影画面,摄影机几乎完全支撑起了整个画面的空间构图,尤其是一些大场面的布景,他乐于也善于运用升降镜头拉提至纵深幽长的大远景,赋予画面雄厚辽阔的感觉,仿佛是高空航拍的纪录片布景,又有着其难以企及的情感视觉存注其中,景、物合一,情、韵兼具,展示的是饶具特色的“中国风”,是妩媚万千的人文、山水、乡村情怀,是一望可知的“霍式摄影机美学”。《那山那人那狗》的画面里,随着摄影机的移动和镜头的处理,如诗如画、苍茫温情的影像缓缓出现:苍穹之下,弥漫雾气的晨曦、陡峭的山路、蔓延没有边际的群山、清澈缓缓流淌的溪水、层层缔结的梯田、处处安详坐落的湘西民居、茶树边上若隐若现的少女……摄影机在制造美景的同时,也在制造情感,酝酿着诗意和温暖的人间情怀。这是霍建起电影里最常采用的视觉语言方式,即随着摄影机的移动,掩映之间,设置出明丽而畅顺的动感,接着,将镜头放置在一个精致的画面上,仿佛某种超越性的目光在深情凝视,背景、人、物体、虚幻而真切的气氛,都被安放在各得其宜的位置上,展现出霍建起在电影艺术上所独具的那种沉稳深情的气韵和暖意。霍建起依靠其摄影机创造出了其独有的美学风范和一个温暖、清新、洗练、厚重的视觉世界,让观者沉迷在那个“前现代的中国”气氛中无法自拔。
其次,霍建起运用出神入化的蒙太奇剪辑技艺,营造出特殊的视觉情绪。他的电影可以明显地看出主要仰仗视觉的语言支撑整个电影情绪,几乎完全由摄影机运动、构图、剪辑来交代推动剧作的发展,而不是像一般导演那样基本依赖叙述来交代情节。在这样的视觉语言布置下,霍建起的电影表现出了沉默,在这样的视觉沉默之中,蕴藏着深沉的情绪。好像《秋之白华》,杨之华在秋意潇潇中去探望瞿秋白的住所,画面清净白亮,杨之华惊讶地发现该地残垣断壁,四处荒草蔓延,中间赫然一座四方小楼。缓步而进,白杨树上的一只喜鹊欢叫,杨之华凝视少许,突然一声呼唤,杨差点在台阶上跌倒。这样的一组镜头,气氛营造上写意而舒缓,视觉上明暗相宜、动静得体,节奏感控制得恰到好处,是典型的蒙太奇组合,将镜头沉淀为安静状态的长镜头和硬切的剪辑法,极大地发挥了分镜的功能,展示出一股温情、写意、浪漫、有格调的视觉语言。这是霍建起本身画家出身、深谙视觉美学的不经意抖露。
二、视觉语言的效果:叙事与隐喻结合的美学境界
作为一种叙事的艺术,电影依靠镜头来讲述所讲是它最基础的职能,然而,但凡出色的电影,绝不会把其作为唯一的职能来完成。几乎所有的优秀电影导演都会在叙事的进行之中顽强地追求影像视觉之上的隐喻功用,致力于表现电影的隐喻性和叙事性的交互统一。在霍建起的电影里,视觉语言的完美安排最终也是为了隐喻的完成。摄像操作之中,电影的表意从来不是独立地取决于一个个孤立没有灵魂的影像片段,而是取决于影像、视觉之间的关系组成,表达最广泛、最深切的含蕴。比如,在《暖》里,主角和乡亲们围坐吃饭饮酒的片段,酒杯被反复地端起,并给予几个特写的镜头。原本,作为视觉语言而言,一个酒杯仅仅只是表现这个物件的原态,但在霍建起的视觉安排里,酒杯借助蕴含的关系,既可暗示时光的酝酿,也可表示完全不同的意思指示:无聊、不安与焦虑。在此,霍建起为影像建立起了一套互相指涉的隐喻关系,也传达出超越记录之外的美学意义。这在所有霍氏电影作品里,几乎是标签一样的视觉表达存在。
首先,视觉语言向影像语言转换,实现隐喻功能。任何一部电影的创作,都必然是一个将视觉语言转换成影像语言的转换艺术,是建构一整套和视觉语言相互适应的视觉代码,完成从孤立的视觉表意走向影像表意的视觉和隐喻变异。视觉语言是静态的、孤立的、能指的、感官的,影像语言是动态的、组合的、所指的、隐喻的。霍建起作为一个学美术出身的导演,尤其注意电影画面中视觉元素的表意功用。在他的掌控之下,电影的视觉始终在介入剧情之中,在强化视觉语言的前提下完成叙事和向影像语言的转换,从而实现隐喻功能。《那山那人那狗》就是成功转换的典范:一路的风景,桥、溪、稻、山,一幕幕的视觉探寻,也在找寻内心风景,透露出别样的情绪和田园牧歌式的叹咏;父亲过河时小心翼翼地保护邮件不被打湿,一阵风吹来他死命地奔跑追赶,到了村庄有如抚摸宝贝一样细心整理,诸多视觉画面传达出老邮递员更丰富的形象,而每一次送件员的到来在影像语言的隐喻功能上承载的其实也是闭塞乡村人的一份希望;儿子走过河流,背起老迈的父亲,视觉上突然呈现黄亮的色调,影像语言仿佛在传达儿子肩负起自己责任的信息;风吹的信件、跟随父亲的追逐,夜里铺排隔天的信件、村姑探头出现、放牛娃高歌呐喊等等,都在一晃一动的视觉上昭示着希冀……凡此,皆是影像语言转换后实现隐喻功能的表征。
其次,视觉语言表意形式的巧妙择取。在霍建起的电影里,他总是如此地善于择取和电影之中所涉及的事件、人物、题材、主题、视觉画面相适应的影像表意形式,从而使得电影语言和视觉语言一起与它的故事形态、叙事过程、叙事对象组成高度视觉化、纯粹化的“电影故事”。《那山那人那狗》是一部以真实的视觉美学和隐喻系统为主旨的影片,出于这样的意图设计,电影里几乎没有出现特写的镜头安排,叙事的整个过程都是以平行的视点为基准,布置适应的中、近景镜头和画面,与之相适应的是清一色的无技巧化剪辑。直到末尾,当儿子背负着那些信件悠然走向山路之中,他的脸上才出现未曾有过的安详与甜蜜的神情,眼中迸发出此前未有的志得意满。同时,银幕之上伴随着不曾投射过的特写镜头。这些镜头景别的突变是视觉语言的突然转向,是表意形式的隐喻功能放大。正是霍建起电影在视觉语言表现力度、强度、范围上的突出特点。
三、视觉语言的容受:信息的传达与接收
就“读者反映”批评理论而言,观者在银幕前观看时,是语言、心理、视觉相互交流的过程。电影的观看,和其他任何的叙事性作品一样,制作者和接收者是互为前提的。作为电影的制作者,其所要表达的全部主旨和意图需要寄托于和观看者共同享有的编码、解码机制来沟通、完成、塑造。从这个意义而言,一位优秀的导演,不仅仅是善于借助视觉语言来“讲”故事,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位善于掌握某种秘诀或媒介来与观者“共同使用代码”(艾柯语)的人。霍氏影片的话语形态上不是那种使得观者始终处于消极阅读、品味、观看的“封闭体系”,而是在电影构成的序列上归属于“连锁并置类型”。其作品《那山那人那狗》《秋之白华》《暖》《情人结》,都是这种叙事结构的产物。叙事上的铺排式、并置式、连带式的电影语法,使得其影片的观者始终处在对于故事不断探寻、联想、期待之中。可以说,霍建起的影片制作,正是择取了这样一种视觉语言的编码方式来建构自身影片和观者的交流、沟通机制。其意图依靠此传达,观者所有的感悟也有赖于此而认知。
一方面,霍建起在视觉语言的情境设置上,使得观者成为置身于黑暗中探寻世界的访者。探寻的渴望和触动成为电影观赏机制的构成要素。如在影片《暖》《情人结》《秋之白华》中,都有着不同形态的探寻情境,即都展现了在现实中被疏离、遮蔽、隔断起来的情境。特别是《暖》中的林井河,其视觉语言和叙事语序的部署,本身就是探寻者的角色。他实际上成为观者的化身。从城中回乡,在路口偶遇过去的初恋情人,已经完全不同往昔的暖,他屡屡透过各种可能的方式,探寻自身、暖、乡村、社会的变迁。视觉画面中泥泞的、荒草丛生的小路,古雅安静的徽式建筑,风中摇曳的黄色芦苇,几场丝丝雨景,还有那个如今邋遢、粗鲁的瘸子村妇与当初能歌善舞的姑娘的对照,在微雨飘飘的深巷井河和暖的对望,都成为视觉语言制造过程中探寻的路径和窗口。这是霍建起运用视觉语言的编码构成对观者的有效控制。
另一方面,霍氏电影善于借助视觉语言,编制较强故事性的叙述主线来完成沟通。说到底,电影是一类企图祛除现实语境和叙事语境的艺术,它唯有不断地借助视觉语言的编码来衔接现实和叙事语境之间的横沟。霍建起的几部作品,无论其潜藏的文化意蕴、价值隐喻归属于何处,就叙事的表层结构而言,都是择取了故事性强的叙事主题来构建主线。《那山那人那狗》是一个邮递员在闭塞的山村成长感悟的故事;《秋之白华》是革命年代家国情怀掩盖下的情感纠葛;《暖》直接讲述了男女之间的情爱主题、挣扎冲突,与人性、人情处处压抑又生机不断的展现。在霍建起的视觉编码中,这些矛盾冲突更加凸显,同时也构成了叙事层层推进的动力。《暖》的开首,林井河骑着自行车载着老师穿过芦苇,来到浮桥上,偶遇暖的视觉安排中,霍建起给予了画面非常显著的特写:飘扬的芦苇、缓缓的潺流、暖的衣饰、蹒珊的步履……视觉语言的编码上也特意凸显了叙事的强度和对观者带来的震撼力。正是这样的视觉布置,更加亲切地、具化地、鲜明地走进观者的内心,暖、林井河、父亲、杨之华这些银幕上的人物,也永恒地“生活”在一个由视觉语言编码制造的叙事体系之中。
综上,就霍建起电影来说,视觉语言的编码是其最具特色之处。但是,作为一个有浩然雄心、自视甚高的导演,他始终自觉地将视觉语言放置在一个辅助的位置上,而立足于思想内容的表达和深化,巧妙地运用相关视觉技巧,讲述一个又一个“过去中国”的故事,试图重建“文化中国”“乡土中国”的往昔记忆。品评霍氏电影理应立足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