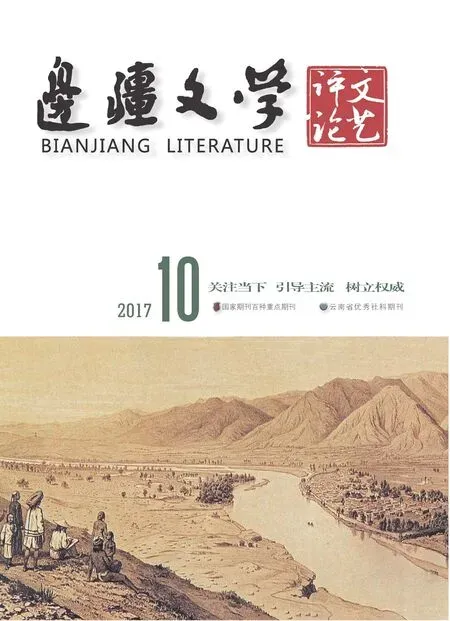张二棍诗歌的悲悯及救赎意识
2017-11-15朱江
朱 江
张二棍诗歌的悲悯及救赎意识
朱 江
张二棍,本名张常春,1982年生于山西忻州,山西大同217地质队职工,出版有《旷野》。张二棍是当代诗坛较活跃的诗人之一。他的诗歌满怀悲悯,有强烈的救赎意识。基于此,本文以悲悯为起点讨论其诗歌。
一、张二棍诗歌的悲悯
张二棍是一个地质工作者,长年跋山涉水。读其诗歌会发现,他的作品大多抒写野外及生活的底层。细读其诗歌会发现其诗歌的一个共同点:悲悯。
讨论张二棍诗歌的悲悯性,可以从其职业开始。张二棍所做的工作是这个行业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后续工作的就无从谈起。职业的卑微与重要不言而喻。《露水是秋蛉共同的敌人》中诗人直接冠以副标题“给野外的所有人,写给你们的热爱”,诗中有“在每个黄绿更迭的山路口/你们在我永远不能抵达的地方/像一只背井离乡的秋蛉”,诗人从“虚”的角度呈现野外劳作,永远不能抵达,让人下意识的想到没有尽头,表面上是写其他人劳作,实际上是作者自我劳作的体验,它是将自我情感通过位移的方式写出,作者内心无法言说的悲伤得以呈现。作者还以“秋蛉”做比,秋蛉本身是非常微小的物类,再加上背井离乡的修饰,悲伤程度进一步加深。短短的几句诗,劳作的艰辛、无奈、孤独跃然纸上,这个职业的悲悯也随之出现。《写给钻探的兄弟们》中有:“再坚韧的钢铁也会慢慢的劳损”,作者通过浪漫的笔调来写这个职业,诗句表层写钻杆,实际写人,表层(钻杆)物性与深层(人)物性合二为一,物性高度概括。职业的漫长,无期,无奈随即显现。“我散落在山间的兄弟啊/拥有这野花的姓氏/并以来自地心的石头/命名”写出了职业的空旷,无边和孤独感。
张二棍很多诗歌都写到野外,这应当与他长期的野外作业有关。《在山巅》、《在灵丘》、《野外,我来了》等都是对野外劳作的抒写。同时,他的诗中大量写到植物、寺庙、山村等。这里以植物为例来讨论其诗歌的悲悯性。《草民》中有:“说说韭菜吧。这无骨之物/一丛丛抱着,但不结党/这真正的草民/用一生的时间,顺从着刀子/来不及流血,来不及愈合/就急着生长,用雷同的表情/一茬茬,等待”,短短几行诗就写出了韭菜。这里草民是借韭菜来完成的,它其实是一个象征,写韭菜如同写人,诗人抓住韭菜的特性,形象地写出,这就是一个诗人的能力。韭菜是一种驯养了的植物,是带有人类性的植物。韭菜是草,又不是野草。这样的植物呈现在诗中,也不可能是有野草的气质,不可能像野草一样“哪怕孤独/也要保持我的青/从骨头里蔓延,由内而外的/青。这是一株草的底线/哪怕被秋风洗白,也请你/记住:我曾经青过,/白的,是我留在这尘世的/骨骼”,(《让我长成一棵草吧》),这些野草“成为”韭菜之前,才是真正的草,而现在,野草进化成了韭菜,变成了卑微的物种,失去了野草性。韭菜最终就是“用一生的时间,顺从着刀子/来不及流血,来不及愈合/就急着生长,用雷同的表情/一茬茬,等待”,作者说出的是一种悲悯。如此的卑微,如此无奈,又如此尽力,诗人写出一种生命“恶”性循环的存在和无法破除的悖论。
张二棍诗歌的悲悯更多体现在对底层生活的关注,如《穿墙术》中孩子的病痛,《流浪汉》中城市流浪者,《咬牙》及《我应该怎样死》中的人们,等等。《娘说的,命》中这样写:“娘说的命,是肝癌晚期的大爷/在夜里,翻来覆去的疼/最后,把颤抖的指头/塞进黑乎乎的插座里/娘说的命,是李福贵的大小子/在城里打工,给野车撞坏了腰/每天架起双拐,在村口公路上/看见拉煤的车,就喊:/停下,停下”。这里诗人借“娘”的口说出底层生活的艰辛。大爷及大小子,两个生活在底层的人,他们的痛苦是无以复加的。大爷的病痛是自身的,是一种要抵达生命终结的痛苦,人终有一死,这是人类无法抗拒的,肝癌晚期是用来终结生命的方式。大小子的痛苦,是行动不自由的痛苦,对生命终极来说,他的痛苦比大爷更痛苦,他无法预知自我痛苦的终极。他们的痛苦是自然或人本能的痛苦。这种痛苦是人生命无法抗拒的,这就是悲剧,诗人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让人生无法摆脱的东西呈现出来,比如生老病死,比如行动无法自由。
而更多的痛苦源自社会,张二棍这样的诗歌很多,比如《一脸幸福》、《我收藏着一张图片》、《雀》等。《素手无策》中有:“是的,没有办法/女儿逃学,练习抽烟/他没有一点办法/母亲病了多久,也躺了多久/他却没有一点办法/他卖水果,刚收了假钱,/又得交罚款/他只有呆呆地,蹲在那里/没有一点办法/他攥着那张钞票,揉着,撕着/真的,没有一点办法/一点点办法”。诗人抓住“没有一点办法”,一步步将读者拉向痛苦的深渊。“女儿逃学,练习抽烟”,女儿是什么,是自身将自己留给世界的一种延续,但“逃学”,还“抽烟”,这里可能是个隐喻,逃学的是什么,是学生,抽的是什么,是烟。学生是什么,是希望,烟是什么,是毒品。这就是生命的未来,“卖水果”,“收了假钱”,假钱就是社会对他的回报,最终“他攥着那张钞票,揉着,撕着”,所有的东西,最终都化为乌有,唯有悲伤留下来。这就是悲剧,悲剧是由社会引发的。又如《醒》中有:“他说起年轻时的上甘岭/又说起这些年的下窝子沟/但他问起天色的时候/我撒了谎。我说黑着哩”,“上甘岭”是一个空间物象,诗人就这样简单地让诗歌的背景得以设定。在此背景之下,“二舅”的价值得以显现,他是“一个年迈的瞎子”,他为什么会是一个瞎子,在上甘岭的背景之下,二舅的隐喻不言而喻。通过这个小人物,作者写出了一场战争带来的创伤。为什么会撒谎,撒谎有什么用,高度节约的文字背后,暗含了一个诗人内心的悲悯。
同样,强大的自然灾害也可以酿成悲剧,《那年蝗灾》中,诗人现场感地呈现了一场灾难:“父亲疯子般吼叫,向天空/甩着破褂子。我学着他的样子/挥舞着一小片褂子,我学着他的/慌乱,愤怒,和破嗓子/蝗军过境后,土地如末日/一片杯盘狼藉的荒凉/父亲坐在田埂上,一言不发/他混身沾满了禾木的碎屑/和蝗虫的残肢”。蝗灾的价值与意义不在当下,因为,蝗灾的危害可以向前追溯多少年,这首诗的价值可以理解为诗人时间性地表现底层人们的无助。在大自然面前,人是渺小的,同时也是值得悲悯的,诗中,诗人以“我”的口气,实际上借一个更弱小者的眼光来呈现这场灾难,从人称的角度,诗人将诗歌的时间性隐没,“我”到底有多大,我只是“挥舞着一小片褂子”,正是没有具体的时间,“我也学着他的样子,拍打着他的肩膀”就显得意味深长,诗人利用一种童心式的幽默还原灾难后的场景,与灾难自身的悲剧场面形成鲜明对比,诗歌的诗意由此显现,以父子的情感画面“写实”般地深化了这场灾难的悲剧性。
二、张二棍诗歌救赎意识
应该说,悲悯与救赎是相关的,因为有悲悯存在,救赎才成为可能。这也是一个作家的价值取向,张二棍诗歌体现的即是救赎。
张二棍有一首诗叫《有间小屋》,最后这样写:“要有间小屋/站在冬天的辽阔里/顶着厚厚的茅草/天青,地白/要扫尽门前的雪,撒下半碗米/要把烟囱修得高一点/要一群好客的麻雀/领会一个腊月赶路的穷人/要他暖一暖,再上路”,诗歌通过叙事抒情,呈现一种理想。“要”呈现的是一种想法,从时态上讲是一种将来时态,同时又是对过去时态的一种追问,这意味着诗人特定的价值取向,它到底要指向什么,指向的是善。而文学有文学的标志,这里写出的是一种追忆,是对过去的追忆,这是身处现代社会的人对过去农耕文明的一种追忆。因为,“烟囱”是一个标志,是一个指路碑。诗中,它提供给世界的是麻雀的避难所,是穷人的指路碑。于是,我们可以看出隐含于文字的主题:救赎。小屋为何存在,等穷人。是不是小屋最终就是穷人的归属?不是,它只是让穷人“暖一暖”,还要再上路。小屋最终只是为迎接一个归者而存在,当然迎接意味着送走。穷人最终依然是一个穷人,这就是隐含在文字背后的阴影。这首诗为什么叫“有间小屋”,因为小屋是不存在的,所以才叫“要”,什么才叫“要有”,这就是一个隐喻。
张二棍的诗歌蕴含着深刻的救赎意识,尤其是自我救赎意识。《在乡下,神是朴素的》中诗歌这样写:“在我的乡下,神仙们坐在穷人的/堂屋里,接受了粗茶淡饭。有年冬天/他们围在清冷的香案上,分食着几瓣烤红薯/而我小脚的祖母,不管他们是否乐意/就端来一盆清水,擦洗每一张瓷质的脸/然后,又为我揩净乌黑的唇角/——呃,他们是一群比我更小/更木讷的孩子,不懂得喊甜/也不懂喊冷。在乡下,/神如此朴素”。诗中,“神”是普通的,诗歌笔调直观冷静,将神以人的方式呈现,神“坐”在穷人的堂屋里,“接受”粗茶淡饭,“分食”烤红薯,仅仅是“比我更小更木讷的孩子”。张二棍其他一些诗也写到“神”。《寺庙》中诗人写到“木雕的佛像里/驻扎庸庸白蚁。半抹残笑/为蛛网牵绊,唇角/沾满蚊虫的尸骸/多让人唏嘘”。《春,寺》中诗人这样写:“诸神越发胆小/躲在泥巴和油彩里,发呆”。在诗人看来,神也丧失了神性。这就像特雷·伊格尔顿所言“宗教的衰落”,正是神的衰落,人才回到人的信仰价值观中,人需求新的救赎方法,这就是文学的意义。张二棍正是通过文字的呈现,找到自身的价值,人只有自我救赎才能拯救自我。
以救赎为基点,我们就不难理解《黄石匠》中诸如“无非”之类的词语,“他祖传的手艺/无非是,把一尊佛/从石头中/就出来/给他磕头/也无非是,把一个人/囚进石头里/也给他磕头”,这里连续用了两个“无非”,我们是不是简单的就将其理解为加强语气,无非是什么,无非就是不外乎,就是把事情往小里说、往轻里说。诗人为什么要在这里连续使用无非,本质上就有轻视的意思。可见诗人在这里要表达的是拒绝神灵。正因为拒绝,作者表达的其实就是以文字为起点的自我救赎。以此,我们就不难理解《旷野》中震撼人心的场景:“我害怕,风随意触动某个音符/都会惊起一只灰兔的耳朵/我甚至害怕,当它无助地回过头来/却发现,我也有一双/红红的,值得怜悯的眼睛/是啊。假如它脱口喊出我的小名/我愿意,是它在荒凉中出没的/相拥而泣的亲人”。这是一个非常感人的细节,它是诗人对生活的一种关照,而这种关照又是一种大胆的想象,这也是一个作者的本质及任务。诗人在这里要做什么,这里饱含着一种悲悯。“我”为什么会有一双红红的眼睛,而且是值得怜悯的眼睛,生活的角度来讲,红红的眼睛,明明是兔子的,这就是作者通过拟物的手法,在人的身上拟上动物的眼睛。而“它”脱口喊出我的小名,它是什么,它是真正的兔子,兔子怎么会喊出的名字,这就是拟人,作者在一个特殊环境中(旷野)赋予了兔以人的色彩。于是,人与兔得以通融,“我愿意,是它在荒凉中出没的/相拥而泣的亲人”,这是何等的孤独与荒凉,人傲然于荒野中,内心的渴望是如此的强烈。透过如此大胆近乎疯狂的想象,我们看到一个内心悲悯的孤独者,他是多么需要救赎。
理解了张二棍诗歌的自我救赎意识,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张二棍诗歌中的抒情主体。他的诗歌常常通过第一人称来呈现。《六言》这样写道:“因为拥有翅膀/鸟群高于大地/因为只有翅膀/白云高于群鸟/因为物我两忘/天空高于一切/因为苍天在上/我愿埋首人间”,诗歌读起来朗朗上口,读到最后,悲从中来。他喊出的是一种命运的伤悲。人是卑微的,人始终无法超越天空与大地。而需要追究的是诗人是怎样说出卑微的,这里诗歌叙述的主体是“我”,这也是张二棍诗歌叙述上的一大特色:有我性。追究有我性,这似乎与诗人的生活和生存背景有关,长时间的野外作业,常年面对的都是空旷的大地,以及自语式的存在。于是,我们同样也不难理解其诗歌无我叙述中的有我性,比如《娘说的,命》中的“娘”,这里诗人说的“娘”与母爱无关,作者是要借“娘”的口气来说出这个事情,诗人所要借助的依然是一种口气,本质上依然是作者的叙述口气,只不过,借助这样一个物象,让叙述有依托,让表达得以顺利进行。所有这些都因诗歌的自我救赎而起。

吕 印 国画 文村印象
注:文中所选诗歌来自文[2]。
【注释】
[1] 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武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2007年版,20页。
[2] 张二棍:《旷野》,漓江出版社2015版。
(作者单位:云南省镇雄县第一中学高中部)
责任编辑:臧子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