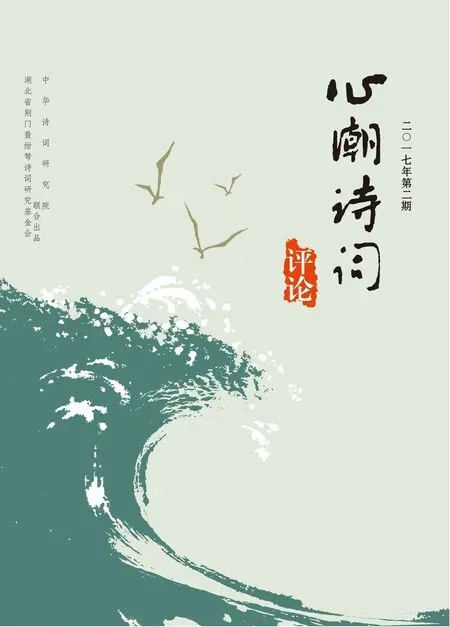恬淡与刚健的融和魅力
——江岚诗质地漫议
2017-11-14段维
段维
恬淡与刚健的融和魅力——江岚诗质地漫议
段维
江岚的诗包含着深邃、厚重的意蕴,却又如陶诗一样用字平淡自然。正是这种恬淡的美,深深感动了读者,润物无声地让读者产生情感共鸣。但他的诗,也有金刚怒目、慷概悲歌的刚健之笔。他的峻峭诗骼更多地是源于一种心理自觉,一种与天地同悲、与百姓同仇的可贵品质。他的诗或柔或刚,或刚柔并济,这两种看似对立的元素却在他的整体创作中由恬淡的基调所统领,终至融和。正是这种对立统一的双重诗性,造就了魅力江岚。
《心潮诗词评论》编辑部约我写一篇江岚诗作的评论文章,我不假思索就应承下来。及至收到江岚兄寄来的40首诗作,品味再三,心有戚戚焉,却不知如何下笔。读江岚的诗,总有一种潺潺的情愫律动心弦,着力处还会让内心最柔软的部分隐隐作痛。但那到底是什么,却一时说不清。按照当下评诗的套路,大可摘出作者的一些佳句进行品评,然后再将其升华一把。但说来奇怪,江岚的诗不能说没有佳句,但十分抢眼的并没有很多;然而读后却又那样真真切切地触动着我。因此,评论欲走现成的老路,恐怕行不通。
于是,我把他的诗作打印出来,带在手边,有空就拿出来品味一番。渐渐地似有所悟。然对与不对,只好套用一句当下流行语了:我的文章我做主。
一、恬淡:江岚诗风与诗人情怀
仲冬的一个周末,艳阳高照,气温回升,我驱车至郊外闲游,看到三五农民正在翻耕田土。那怡然自得的神态,让我情不自禁地念叨起陶潜的诗句: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陶诗字面上往往用平淡、自然、优美、浅净的文字,写意出一幅幅宁静、淡远的山水田园画,表现了大自然清明澄澈的美,以及诗人物我同一、超尘拔俗的恬淡人格。而实质上,这些平静浅淡的文字里却包含着深邃、厚重的意蕴。正是这种恬淡的美,深深感动了读者,润物无声地让读者产生情感共鸣。
这不也正是江岚诗中最明显的风格么?我们不妨先来看看他自选集中排在最前面的三首绝句:
乙未春雨过敬亭山生态园瞻太白像步其《独坐敬亭山》原韵
胜地耽高咏,临风负手闲。
也应听不厌,暮雨洒空山。
壬午春末游十渡杂咏选一
孤馆倚空山,清光如许寒。
骆驼峰下望,恍惚已千年。
春日过东固访富田事变发生地王家祠堂
故地青樟老,空庭丹桂花。
休教花解语,一任日西斜。
五绝最是难写,江岚兄能写得如此醇厚,与他肯将自然性情流露以及使用朴实无华的笔法分不开。这几首五绝,乍一看很有些王维的影子。仅从诗的意境来看,王维与陶渊明确有相似之处。但如果更进一步考量二者的内心世界,区别还是很大的。陶渊明是真心实意的归隐,王维则是遇挫后的暂时逃避。反映到诗作中,陶渊明就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那般自然天成;而王维则多少有些像“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那样刻意了。
我与江岚兄谈不上过从甚密,有限的几次接触和交谈,感到他葆有谦谦君子之风。这种为人处世的风格与其诗词创作有没有内在的必然联系呢?我想到了意识批评。
乔治·布莱的《批评意识》一书被认为是日内瓦学派的“全景式的宣言”杰作,他在书中提出一种建立在阅读现象学基础上的意识批评理论和方法,主张批评主体与创作主体的认同。他认为,在阅读过程中,批评主体虽然让位于创作主体的意识,但他并非完全地丧失自我,而仍然在继续着自身的意识活动。这样在读者和作者之间就通过阅读行为产生一种“相毗连的意识”,并由此在读者身上产生一种“惊奇”,这个感到惊奇的意识就是批评意识,它实际上即为读者意识。读者在把他人的思想当做自己的意识对象时,与创作主体形成了一种包容或同一的关系。
而这种认同又是通过把握作者的“我思”而获得,是两个主体间的意识交流和沟通行为。所谓“我思”即作家在作品中流露出来的意识,因此,发现作家们的“我思”,就等于在同样的条件下,几乎使用同样的词语再造每一位作家经验过的“我思”。这样就出现了批评的认同。
丙申春暮谒安海镇龙山寺
一片慈云卧翠微,春残法雨尚霏霏。
苍蟠石柱龙听海,绿锁莲池叶护龟。
愧向娑婆耽好句,空教文字老通眉。
上人经过多遗泽,瞻拜不禁双泪垂。
丙申春暮过晋江草庵寺
万绿沉沉处,红墙一草庵。
深山无客到,绝壁有龙盘。
古寺耽凭吊,幽禽自往还。
昔人不可见,空此雨廉纤。
机构中构件的长度都为常数,构件1的角度θ1为固定值,构件2由液压装置控制作为原动件,所以θ2为独立变量。然后只剩下构件3和构件4的角度θ3和θ4待求,它们的代数表达式的形式是构件长度、构件1的角度θ1和一个变量角θ2的函数
这两首诗,依旧是淡泊的风格,除了第一首七律的颔联句式有些新人耳目外(我清楚地记得,这还是我们一帮好为人师者建议他这么组句的,他也许不好意思拒绝诗友的盛情才使用的吧),其余都不以句法、章法取胜。第二首五律读至“古寺耽凭吊,幽禽自往还”时,我不禁想起陶潜《饮酒二十首》之四中的“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的句子,甚至恍惚觉得江岚诗里的“幽禽”就是陶潜诗里的“失群鸟”,而这只鸟正穿越千年,充当着两位诗人心灵沟通的信使。
在这次采风活动中,我发现江岚兄是很享受创作过程的,他在这个过程中不是为了完成任务,更不是为了炫耀才学,而是用心去与历史对话,然后把这种对话的心得忠实地表达出来。这与当下诗坛心浮气躁的表演和逞强斗技的风气有着云泥之别。就我自己来说,写诗丝毫没有求实惠的功利之心,但却不乏求虚名的炫技举动。当下诗词界,评价一首诗的好坏,十分注重句子是否精妙、章法是否独到、立意是否崇高等元素,因为浮躁的编辑和敷衍的评委哪有心思去“细读”海量的作品呢!这样一来,像江岚兄这样的本色写作,是很难被选为报刊头条或摘得各种大奖桂冠的。这就十分考验一个人的写作动机了。
二、刚健:江岚诗骼与内在品质
既然把江岚与陶渊明对照着来看,那么两者的恬淡风格与情怀是一以贯之的,还是同样都有着共性中的个性呢?
在很多人眼里,陶渊明是山水田园诗的代表,其诗营造的田园牧歌式的意境令许多人迷恋。钟嵘《诗品》这样评价陶诗:“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至如‘欢颜酌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邪!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严羽《沧浪诗话》云:“汉、魏古诗,气象混沌,难以句摘,晋以还方有佳句,如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谢灵运‘池塘生春草’之类。谢所以不及陶者,康乐之诗精工,渊明之诗质而自然耳。”赵文哲《媕雅堂诗话》则说:“陶公之诗,元气淋漓,天机潇洒,纯任自然。然细玩其体物抒情,傅色结响,并非率易出之者,世人以白话为陶诗,真堪一哂。”
然而,陶诗并非只有一种面目,他的内心也并非一直古井无波。他一生最大的痛苦是忠心报国的愿望无法实现,未酬的壮志一直深埋在心底,至晚年更加强烈。诗人内心的慷慨与悲愤借助怪诞神话形式释放出来,尤以《读〈山海经〉》组诗之九、之十所写的内容十分突出:
夸父诞宏志,乃与日竞走。
俱至虞渊下,似若无胜负。
神力晚殊妙,倾河焉足有!
余迹寄邓林,功竟在身后。
——《读〈山海经〉其九》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
刑天舞干成,猛志固常在。
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
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
——《读〈山海经〉》其十
陶渊明通过对夸父远大志向和非凡毅力,对精卫、刑天顽强品格与一往无前的斗争精神的歌颂,对他们最终徒存猛志而发出的叹惋,从字里行间抒发了诗人“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十二首》其五)的豪情和“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杂诗十二首》其二)的悲慨。
而他的《咏荆轲》则最为慷慨且锋芒毕露。像“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漤”、“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的气概真可谓横绝千载!陶渊明之所以热情歌颂荆轲剌秦王的英雄事迹和正义勇敢行为,其目的是为了抒发自己对强暴者的反抗精神并对他们进行鞭挞。荆轲勇烈无畏、重义任侠的英雄行为在现实生活中是无法达到的,但是在诗人心灵深处,荆轲就是他自己,是他的理想,因此,诗人通过热情歌颂荆轲刺秦王的勇敢行为,使他的理想插上翅膀,自由翱翔。
同样,江岚的诗也有金刚怒目、慷概悲歌的时候。兹略举二例:
过山海关怀戚继光
大纛飘扬十六年,更无烽火照燕山。
使公横槊向明末,哪个胡儿敢叩关!
过长白山天池
雪从太古尚皑皑,虎踞关东千嶂开。
绝顶霜风骇神鬼,大池何物吐氛埃?
棉衣愧比苔衣暖,心火休随地火埋。
淬罢群崖坚似铁,好同猛士镇高台。
第一首的“使公横槊向明末,哪个胡儿敢叩关”,大有润之先生《咏蛙》之“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的豪情。第二首整体上浩气干云,尾联则卒显其志——“淬罢群崖坚似铁,好同猛士镇高台”。这种气势当不在渊明《咏荆轲》之下。
与近体诗相比,江岚的古体诗写得更加厚重,亦更多刚健之笔。像《谒成吉思汗陵有感》、《过伊犁咏马》就是如此。尤其是《咏长白山岳桦林》更是惊神泣鬼:“独怜岳桦近高寒,倔强势欲傲风霜。木棉也称英雄树,对此壮气恐难当。苍松宁折不能弯,安知岳桦虽弯不能折?恍若复生与任公,去留肝胆两豪杰。”收束处,直是惊雷炸响:“斧锯何辞根还在,雷电交加色不挠。截去犹堪作长剑,好为吾侪破寂寥”。
为什么江岚与陶潜的诗骼会有如此的相似之处呢?是经历、个性使然,还是观念、才情使然?我们很难妄加猜测。那我就只好又一次发挥我的“主观能动性”,以小我之心度他人之腹了。
好在有一种理论叫印象主义批评。那我就再次拿来给自己撑腰了。所谓印象主义批评其实是一种依据审美直觉,专注文学作品的审美特性,来表现批评家自我的主观印象和瞬间感受的批评方法。印象主义批评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西方一度盛行,它与我国传统的印象式批评在某些方面有契合之处。一方面,印象主义批评认为,批评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批评家就是艺术家,在进行批评活动时,不单要有情感的投入和体验,还要自由地舒展自己的个性,将自己的独特感受、内心体验、个性气质融入批评过程中去,这种充满个性化的批评才是真正的文学批评,用艺术家的标准要求批评家的做法是印象主义批评的一个特点。另一方面,印象主义批评既不重判断,也不重分析,而注重批评家审美印象的描述,这种印象的描述,只能以文学的方式进行,批评家将自己的理解溶解于感觉之中,不显露出理性的筋脉,带有鲜明的诗人气质和直觉方式,他们的批评过程就是感受美、颂扬美、创造美的过程。
这真是一个特别适合我的批评武器,可以一任我思维的野马,放纵奔驰。
我一直认为,人的性格有一个统领性的主调或基调,但也有适度性的变调。平时呈现的是主调,遇到合适的环境也会呈现出变调。陶渊明如此,江岚也不应该例外。陶渊明终其一生都难以彻底泯灭报效国家的愿望;我想,江岚兄心底燃烧的同样是一腔报国赤诚。这在“淬罢群崖坚似铁,好同猛士镇高台”和“截去犹堪作长剑,好为吾侪破寂寥”中清清楚楚地表明了心志。只是陶渊明隐于乡野,江岚兄隐于都市,因此二者在呈现变调时音色不可能完全一样而已。
性格决定命运。不善逢迎、不善言辞、不善屈膝者,常常空怀一腔热血,理想永远都是梦想。但陶渊明晚年的愤懑与其生活日渐困顿有关,而江岚兄的生活不至于窘迫吧,因此,他的峻峭诗骼更多地是源于一种心理自觉,一种与天地同悲、与百姓同仇的可贵品质。
三、融和:双重诗性造就的魅力江岚
说实话,我最喜欢读江岚那些恬淡风格的作品,这除了我个人的性格偏向内敛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读诗时很容易将其诗与其人融合为一个整体,更何况他的诗意还那样醇厚耐品。我们来看他的一首七绝吧:
丁亥夏日过赛里木湖
湖上风高带雪吹,湖边芳草绿成围。
几时浪静摇船去,泊向湖心看落晖。
开头两句推出两幅绮丽的画面,尽管看起来是二元对立的;第三句则笔触一转,“几时浪静摇船去”,从而逗出第四句“泊向湖心看落晖”。外界好也罢、歹也罢,我且随心任意地欣赏夕阳的美丽去。这是何等的修为!
江岚兄的七律则很有些老杜的气质,那就是显性的家国情怀。他的《读中国近现代史咏怀》三首情怀浩荡。如第一首中的“宁与外邦共休戚,那堪禹甸满腥膻”,第二首中的“纵遣小民自为战,百年何至泣铜驼”,第三首中的“长技强兵徒逞霸,移民立国不禁风”等诗句,苍凉老辣,直逼人心。
不止如此,江岚兄的一些作品,在同一首中还融和了恬淡与刚健之风,读来别具神韵。我们还是用作品来见证:
咏长白山美人松
风雨神州哀陆沉,白山黑水共悲呻。
几多巾帼揭竿起?赢得苍松属美人。
过潘家口水库
一湖山影绿,万壑水光青。
日沐九天阔,云飞数朵轻。
长城望犹在,痛史抚难平。
爱此喜峰口,登临豪气生!
前一首借美人松起兴,抒发的是对巾帼英雄的仰慕。这本是一个严肃而重大的主题,但结句的字面却无比秾丽华美。第二首算是典型的山水诗,前二联意境恬淡优雅,后二联则转为刚健峭拔。这种舒徐斗健之间的转换如此合拍,毫无斧凿痕迹,是极见功底的。
击键至此,文章该煞尾了,心情也顿时松弛不少。端起已经转凉了的咖啡,牛饮一口,顿觉微苦中带着些许清爽和甘甜。这与我品读江岚兄诗作时的感受颇为相似。更深入一层,这种特殊的回味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微凉,二是牛饮。江岚的作品似乎也是需要放一放再品的,不适合趁热吞咽;江岚的诗还需要通过饱和式阅读才能渐入佳境,读三五首很难从局部上与之共鸣。这也是他的作品未能引起评论界重视的缘由吧。就我所知,评论家不管内心是否真的喜欢,都愿意去评论“实验派”作品。尽管这些“实验”很少有成功的,但却给评论家提供了舀之不绝的“话题”活水。江岚则不同,他的笔法是那样传统,他的为人又是那样低调,因此不为评论家所垂青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而我,如果不是接受稿约,也不会那样去反复细读他的作品,也就不会发现他的诗或柔或刚,或刚柔并济,而且这两种看似对立的元素却在他的整体创作中由恬淡的基调所统领,终至融和。也许,正是这种对立统一的双重诗性,让江岚在不断的实践中锤炼了高超的诗词技艺,更由此造就了魅力江岚!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党委书记、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湖北省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首届荆楚诗坛聂绀弩奖获得者)
责任编辑: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