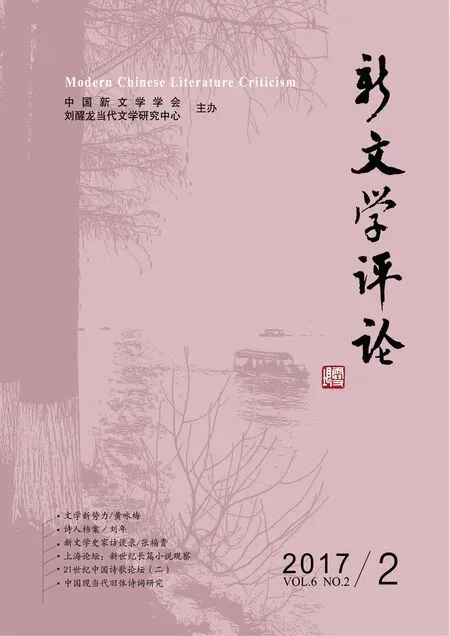多重世界中的心灵异象
———黄咏梅小说读札
2017-11-14◆李冰
◆ 李 冰
多重世界中的心灵异象———黄咏梅小说读札
◆ 李 冰
一、 “世界”的多重性
黄咏梅小说里的世界极为广阔,她将人物置身于不同时空下的现实之中,比如荒蛮遥远的山村、偏僻保守的小城、人欲横流的都市、喧嚣庸俗的市井……其实,在她的小说里还隐藏着另外一种“世界”,即那些性格与境遇迥异于常人的人物创造出的另一种“世界”。
叔本华认为,意志表现为某种无法满足又无所不在的欲求,表象是意志的客体化,表象和意志共同构成现实世界。每个人都有独立且异于他人的意志,意志作为一种精神的存在是千姿百态的,人作为意志的“主人”,其表象是千差万别的,因而每个人的世界自有独特之处,每一个人面对的世界是不一样的,因为他在创造着对世界本质的主观理解。黄咏梅的小说便展示出此种“世界”的多重性。
二、 “他们”之于世界
他们处于底层,构成这个社会最基础的部分,受到种种的压抑,承受着各自人生的苦难。黄咏梅将视线投于此处,描蓦出他们千姿百态的生存方式,体察其内在情感的精微,展现了一幅幅灵魂挣扎的图景。
他们是——《契爷》里叫花子似的卢本、《何似在人间》里为死人抹澡的廖远昆、《少爷威威》里的理发师魏侠、《达人》里的下岗工人丘处机、《瓜子》里的保安开成和他的女儿、《负一层》里的看车人阿甘、《暖死亡》里职场失意的林求安、《单双》里对数字极为敏感的李小多……
面对着世界的压迫,他们自有不同的姿态和各种应对的方式。
契爷卢本在常人眼中如怪物一般,“他无论什么时候都让人感觉破破烂烂的,就像鼻涕一样软塌塌”,“在卢本身上,却看不出任何好好坏坏。人们都怀疑他因为常年坐在小石墩上边,某些部分都变成石头了”。小说提到他本是卢氏旺族的少爷,对卢本何以落魄至此并未作明确交待,别人说他命硬,“他把家里的人和物都碰没了”,其人生历程必定是不平淡的,想必他承受过不少苦难,在历史的潮流中苟存性命,装傻是他的一种生存的策略。因为命硬,人们把子女“契”给他以阻挡霉运,令他成为众多孩子的“父”,但他又受到“儿女们”的捉弄。他不事劳动,拒绝了寡妇阿琴,对生活无欲无求,这何尝不是他应对世界的一种方式?
他更凭借一种所谓捉坏信息的本领在人们心目中成为神一般的存在,
卢本从香港那一趟之后,人的确变得神神叨叨了,并且他的眼睛开始眯起来,眯得世界都被眼皮挡住了一大半,他对很多东西开始视而不见了。
最奇怪的是,卢本带回了“信息”这个莫名其妙的词……卢本所看到的信息,谁也不曾看到过,到底是什么形状长什么样子?从他给某个人身上捉除坏信息的动作来看,我猜,信息是一种类似虱子一样的东西。
当国道修通之后,小城变得不再那么封闭,卢本也能顺应世事的变化,帮过路司机做事赚一两块钱的小费,他介于神与乞丐之间,他若不是极愚极痴者,便是大智大慧之人。黄咏梅在小说的结尾处给予了暗示,卢本为夏凌云的怀孕背锅,是为他早先阻断夏凌云的幸福而赎罪,他穿上文胸装疯以逃避流氓的欺凌表现其智慧的一面,这些都足以证明他并非愚痴。他对这个世界保持若即若离的态度,从不主动地去争取些什么,或许是这个世界带给他的伤害过于巨大。黄咏梅没有直接去写卢本的内心世界,而通过种种事件的讲述,让我们得以窥视其内心之一斑。
《何似在人间》里的廖远昆早已勘破生死,在动乱的年代里,当他看到武斗失败的阿爸在劫难逃,便往石灰坑里扔下家里最值钱的东西——月饼,引导阿爸直面死亡;他从未流过眼泪,而且干着最卑贱的营生——为死者抹澡;他对那些死者缺乏敬意,在为他们抹澡时嘴里总是叼根牙签;他甚至为小青死去的丈夫戴上笑面壳,令那张摔坏的脸不再让人恐惧;他还用牙签调换银粒,使邓耀宗没有钱去买孟婆汤,因而无法忘却犯下的罪孽……他的种种行为使得他在村民们的眼中是个荒唐的人。透过这些荒唐事,我们却能看到他洞察世情的内心,以及内心柔软的部分。因而,在他所爱的人小青离去后,从来不哭的他放声大哭也就可以理解了。廖远昆看似无情,却是最有情的人。
他也早已看清这个世界的荒诞本质。
对于廖远昆来说,这世间根本不存在什么荒唐不荒唐的,再荒唐也比不过老天爷这个魔术师,手指头一点,就把人的魂魄给勾了去,并且他只勾人的魂魄,人的身体他根本是不收的。廖远昆替很多死人抹过澡,他越来越清楚,那些身体都是老天爷不收的肉和骨头,抹澡只是为了使后人安心而已。
廖远昆和卢本,这两人当是黄咏梅小说中最具智慧的人,他们饱受苦难,人生极为坎坷,却能用独有的姿态面对这个世界,令自己得以在这个世界占有一席之地。
三、 世界之于“他们”
世界处于混乱和变易之中,不仅在认识上困难重重,要想很好地把握更是件不可能的事情。尤其当今之世,经济的发展,信息的增殖,城市的扩张,令人无所适从,也加剧了理解及把握的困难。人的经验是局限的,面对纷繁复杂、瞬息万变的世界,便会产生彷徨、疑惑、无依之感。
对于小说《少爷威威》中的魏侠来说,世界的变化让他无所适从,
魏侠心里空空的,像一座无人的古堡。一切隐匿在这个城市里的声色犬马,都被他像屋顶上一只斜着眼的乌鸦般死死盯住。
古堡、乌鸦,魏侠心里一阵莫名。在这么精彩的午夜时分,怎么会想到这些古里古怪的东西?莫非,自己真的OUT了?
作为都市里昔日的东山少爷,已然韶华不再,但他企图拥有一个年轻的女友以抵抗时光的流逝,召唤回青春。然而一切已然不是他所想象的那样,这个世界里的人和事,不再是他所理解所认知的了,由此造成认知与真实世界的错位。因而他在一次聚会中,面对烧钱游戏既震惊又无法理解,他竟然还着了一个小孩子的道,进了拘留所,失去了工作。
他终日沉浸在旧日时光里,并苦苦追寻那个回不去的世界,自然遭遇失败和失落,成为时代的弃儿。未来对他来说是黯淡的,令他迷茫不已。
世界是强大的,他们之于这个世界是无能为力的。小说《达人》中沉迷于武侠世界的丘处机也有过侠义行为,他帮助六个上访的老人屡遭碰壁。他终于认识到自己的弱小与无力,根本无法对抗这个阶级固化的世界,便放弃了虚幻的想象,以一种切近现实的姿态面对这个世界施加给他的种种压迫。那颗侠义之心被弃置不顾,他不再是一个侠客,而是凭借着小市民的精明和狡黠,用颇为巧妙的方式向交警队长行贿,以令自己得以较顺利地生存下去。
世界也是极为诱人的。小说《瓜子》中的小区保安开成尽管忍受着种种欺压与不公,也要让女儿成为一个都市里的人。女儿更认为都市是一个美妙的所在,“在我看来,管山就像一只瘪瘪的破塑料袋。而乐运小区却像一个装满了漂亮礼物的大礼包”。
为了达此目的,父女俩都付出了代价。除了生存压力还有在异乡不可避免的孤独,开成甚至幻想出用吃瓜子的方式去抵抗孤独。
开成的女儿最后从回乡的火车上逃了出来,独自往城市走去。谁能预料日后她在这个花花世界里的命运呢?“笑,众人陪笑;泪,独自垂泪!”唯有孤独和痛苦可以被确定。
四、 心灵的异象
世界施加压迫及苦难于人的方式也是各种各样的,人们有时称之为命运。人在其压抑之下,多少会造成内心的扭曲,产生程度不一的精神变异。黄咏梅则将这种扭曲与变异推到极致,让我们看到种种心灵的异象。
小说《负一层》中的阿甘是黄咏梅创造的诸多人物中最为奇妙的一个,她无法按照常人的方式感受真实的世界,她能听到车辆之间的交谈,却连经理的模样都记不清楚,她生活在现实与虚幻想象的交界处。
这是阿甘用半生培养起来的最大的本事。打个比方吧,阿甘总是认为天下雨跟她是很有关联的。她实验过好多次,每当她心情差到极点,郁闷到要爆炸,甚至伤感落泪的时候,天空忽然会一阵狂风大作,接着电闪雷鸣,最后倾盆大雨。这样,阿甘就坚信了,原来老天下雨是因为自己心情不好的缘故。但是,也有好多次,遇到阿甘心情舒畅、满心欢喜的时候,天也会下雨,可阿甘也有理由:一定是有人的心情不好了,那个人心情不好的程度盖过了自己的好心情,所以老天眷顾那个人,于是——下雨!
自圆其说是阿甘这些年培养起来的本事,阿甘自圆其说的时候,就要自言自语,阿甘自言自语的样子,被不熟悉的人总看作是精神有毛病,只有熟悉的人才知道,这跟电影里那个男阿甘喜欢自己跑路没有什么区别,只是,阿甘用嘴巴跑,兜来兜去,兜了一个大圈,然后回到原点,回到的原点看上去还是原点,其实早就已经是阿甘自己重新描过的原点了。这样,阿甘听到看到的,就不再是别人听到看到的了。
阿甘在自己的内心重新建立了一个世界,她活在其中自得其乐。
阿甘也跟常人一样拥有对异性的欲望,但情感却被投注于死去的明星张国荣身上,因为死人不会提出问题,也不会给她出难题,她可以用自己的方式与之交流。但她终究无法跟早已死去的张国荣约会,便将街头的摩托仔幻化为张国荣,她并非不知道这其中的差别,只是她愿意去这么想。摩托仔带给她性的愉悦,也带给她飞翔的快感,让她从负一层的压抑中得以暂时解脱。她知道他不是张国荣,但依旧将他当成张国荣而接受下来。这不是自欺,而是她塑造生活的一种方式。她在自言自语、自圆其说中构建她的世界,因而她也是那世界的主宰,在那里有她独特的生活方式,并从中得到满足,获得一种生存的意义。
她却将真实世界里的那些疑惑像烧鹅似的悬挂到天上,即将问题悬置,其后不再理睬,然而“那悬而未决的一个小点,总是沿着问号的流线体,滑了下来,继续成全阿甘明天要挂上去的问号”。问题不住地产生,然而总是被悬置,阿甘的世界终究被不断增殖的问号压垮、摧毁。冷酷的现实和她创造的那个自我世界是不相容的,当幻想的肥皂泡被刺破后,她无法在想象中进行一次真正的飞翔,只好坠落到坚硬的地面上来。
小说《暖死亡》中主人公林求安的心灵世界呈现出一片荒芜的景象,其精神空间被不断膨胀的吞噬欲望挤压,几近于虚无。
林求安200公斤的身体,如一座大山般静默,只有两颊的肌肉在有生命地运动着,无穷无尽地重复律动着,在这样的律动中,他身体内部有一条肉眼看不到的河流,从他的喉管一直奔腾而欢快地流淌下去,这就是林求安整个世界的律动,仿佛天真的塌下来也无从阻挠他的这种奔腾的欢快。这动作又是那么持久,以至于他把朝阳都咀嚼成了夕阳,自己都浑然不觉。
林求安似乎丧失了思想,只依本能而活下去,他在逃离这个世界。即便偶有思考和梦境,也是与吃有关。他的个人意志转化为一个无底的胃,除了吞下大量食物之外再无其他欲望,甚至夫妻间难得触发的一次性爱也因不可遏止的吞噬欲望而中断。
为了减轻体重,林求安割掉了大半个胃,不仅失去了胃口,甚至失去了肉体疼痛的感觉,“他就像灵魂被切掉了一半一样”,他还失去了一个正常人对世界的正确感受,
他最近总是有幻觉,他坐在沙发上,无来由的就会发现自己的手臂好像被卸了下来,被放到了沙发的另外一头;他躺在床上,老是觉得他的头跟身体分离了;他站在阳台上,又以为自己的腿已经踩进了一楼花坛的草地上;他喝下一杯凉开水,立刻感觉到他的喉管被牵拉到了饮水机里边,咕嘟咕嘟地冒着泡泡……
手术是对林求安仅有的欲望的阉割,失去一切欲望之后,也就失去了生活下去的支撑,“林求安开始有意无意地想象死的情景”。
他担心死后的火化炉能否装得下自己的身体,这多少带有些反讽的意味,小说便有了荒诞感。为了寻找答案,他不得不克服重重困难亲自跑到殡仪馆询问。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林求安的内心突然充满了爱意,灵魂似乎苏醒过来,心灵呈现出另一番景象。对死亡无所畏惧,对世界便不再恐惧,殡仪馆之行后,他从他那个不断萎缩的自我世界里走了出来,重新回归了他所逃避的那个世界。
黄咏梅赋予《单双》中李小多这个人物以神奇的能力:
只有在做某次倒数运动的时候我才可能无条件地舍弃一些东西,因为,倒数的时间是有限的。倒数的节奏,好像一个人在等待一个预定下来的死期那样,充满了紧张。而只有在那样的紧张里,我的注意力才能高度集中,才能听到一些喧嚣的人声里难以听到的东西。
她是黄咏梅小说中最具意志力量的人物,遭遇也最为悲惨,性格最为暴烈。
在小说开头,作者就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地狱般的图景——这个充满戾气的家庭,父亲暴力,母亲冷漠,哥哥廖小强则是个只会流口水的白痴。李小多因一个错误来到这个世界——母亲数错了日子怀上了她。她是个多余的人,备受父母的虐待与排斥。出于自我保护和生存的本能,她用数数来建立起能够把握这个世界的幻象。在不断的自我暗示下,她不仅对数字极为敏锐,对现实也极为敏锐,她似乎能洞察世界的一些秘密,比如面对一堆花生米或一棵小树所有的叶子,能准确地说出是单还是双。于是她试着将她面临的困难置换为一场场赌局,运用她所拥有的能力取胜,以求得摆脱生活的苦难与生存的困境。然而,她与父母赌哥哥廖小强的生死却导致父亲弃家出走,她赌六合彩导致母亲卷款而逃,她与向阳对赌后动用刀子杀死对方,最后一赌付出的是生命的代价。一次次赌博都是她对自我拯救的企图,每一次似乎都赢得赌局,却只能让她陷入更大的不幸。
她凭借着自我的意志,试图改变世界的秩序,从而改变命运。然而世界之强大不是她能够改变的,也远非她想象的那么简单,猜数并不能纾解她的生存困境,一次次赌局是对自己失败命运确认的延迟,最后,她只好用刀子即暴力来破局,也令自己滑向毁灭——她用生命为注,在一种“赢”的幻象中丧失生命。
李小多面对冷酷的世界毫不妥协,从不认输,以一种胜利者的姿态走向死亡,她是一个悲剧英雄式的人物,她在属于她自己创设的世界中极力创造她自己——她意识中的具有意志力量的人。
五、 生存的寓言
黄咏梅的小说很多可以看作关于人类生存的寓言,是对人与世界关系的隐喻。逃避、置换和遮蔽是人类应对复杂难解荒谬绝伦的世界的方式。
置换,李小多(《单双》)有一种重建现实的企图,她将世界的复杂性置换成输与赢的二元对立,她的人生是一场又一场的赌局,她不只是用金钱,而且用她的青春和生命下注。
逃避,逃出这个世界,或许是林求安(《暖死亡》)潜藏在内心深处最大的愿望,他那贤惠的妻子张小露则用食物为他搭建了一道隔离墙。他逃避着现实,用食欲安慰自我对这个世界的极度失望。
遮蔽,阿甘(《负一层》)用遮蔽问题的方式以应对生活中的难题。她用幻象来掩盖真相,拿张国荣的形象一厢情愿地遮蔽着摩托仔,享受生活和飞翔的乐趣。
这也对应着人面对客观世界的三种态度:
一是主体有着过于强烈的生命意志,改造客体。
二是主体放弃了生命意志,自我逃避。
三是主体弱化了的生命意志,悬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