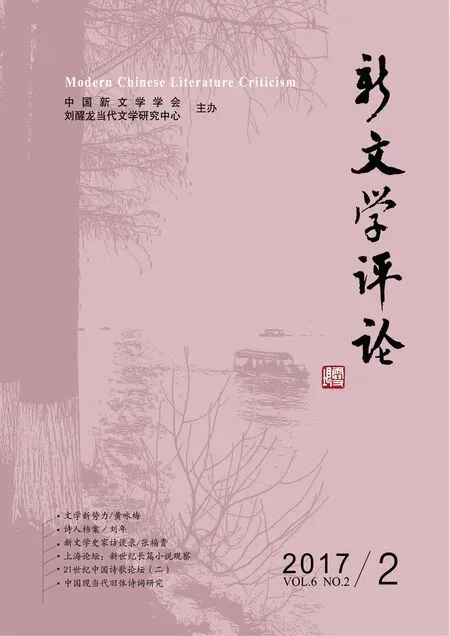萧红、萧军小说黑土地民俗叙事的地域特色与精神气质
2017-11-14段友文陈娟娟
◆ 段友文 陈娟娟
萧红、萧军小说黑土地民俗叙事的地域特色与精神气质
◆ 段友文 陈娟娟
在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园地里,以萧红、萧军为代表的东北作家群,秉承鲁迅开创的启蒙精神,延续着“五四”以来对乡村、妇女两大题材书写的传统,通过民俗叙事展示了东北黑土地独特的地域精神。萧红真挚细腻的情感、卓尔不群的才情和萧军坚韧强悍、粗犷刚烈的“大勇者”个性让他们在文学的天地中激扬文字,驰骋出无限风光。二人都有在东北成长的经历,黑土地默默地哺育着他们,滋润着两个激情澎湃的灵魂。“个体生活的历史中,首要的就是对他所属的那个社群传统上手把手传下来的那些模式和准则的适应。落地伊始,社群的习俗便开始塑造他的经验和行为。”所以,萧红、萧军挥洒出的文字中必然会充溢着浓郁的乡土风味,涌动着白山黑水深沉博大的魂魄。
以萧红、萧军为代表的东北作家群的创作与本土民俗文化存在着难以割舍的关系。民俗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民俗最能代表民族‘精神’,最能表现和体现出本乡、本土、本民族的一般人的意识、思维和心理状态及活力。”民俗事象纷繁复杂,从作为生存基础的经济活动到相应的社会关系,再到上层建筑的各种制度和意识形态, “大都附有一定的民俗行为及有关的心理活动”。因此,文学作为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必然受到民俗文化的浸润,蕴含着本土民俗文化元素。通过文学作品,我们可以对一方土地上民众的生活方式、精神状态有一个初步的认知,同时对同一区域不同作家的作品进行比较,亦能从中探究不同作者在反映一地风俗时的不同视角。本文试图通过萧红和萧军小说黑土地民俗事象的发掘,探讨二者民俗叙事的共性和个性,窥视东北民众的思想情感及东北黑土地地域精神。
一、 特定时空背景下的东北乡村日常生活
民俗文化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与空间上的延展性,这使得特定的时空背景成为民俗的承载体。20世纪上半叶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风雨飘摇、民瘼深重的时代,东北这块广袤的黑土地更是被推向了灾难的深渊。
东北地区位于东北亚区域的中心地带,东、北、西三面分别与朝鲜、俄罗斯和蒙古国为邻;隔日本海和黄海与日本、韩国相望;南濒渤海与华北区连接,战略地位极为重要。这种特殊的地理空间既有利于俄罗斯文化触角的伸入,也便利了日本文化在日军率先登陆东北后的迅速蔓延,使得东北地区在本土文化基础上,吸纳混杂了诸多外来文化,也为东北民众与外域人频繁的交往提供了一个平台。东北民众与中国内地省区的民众相比较,有着更开阔的视阈,更广博的胸怀,其精神血脉里也更多了几分黑土地民俗文化的野性特质。
从绝对地理环境来说,东北地处北纬45°附近,地理环境极其复杂,分布着山脉(大兴安岭、小兴安岭和长白山)、密林、草原、沼泽、江河、平原等。同时这里气候恶劣,漫漫冬季里寒风凛冽、冰天雪地。这一方面锻造了东北人民以渔猎为主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在适应自然、征服自然的过程中形成的积极豪迈、粗犷雄强、勇悍尚武的地域精神;另一方面促生了东北丰富的物产资源,吸引了一大批黄河下游的人们来闯关东,东北人民在众多民族的杂糅之中蒸腾和激荡出一种生存竞争下的勇敢倔强、积极进取和勇于追求幸福生活的顽强意志。
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中华民族饱受战乱,历尽磨难,那铺天盖地的蹂躏与践踏,激起了广大民众奋起抗争的勇气,苦难与抗争成就了中国人民拯救民族危亡的历史功绩。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使清政府失去了对朝鲜的宗主权后,日本从此扫除了中国控制朝鲜的势力,并将势力渗透到了中国东北,之后日俄在中国东北的斗争愈发激烈。随着世界局势愈加动荡,英德矛盾的尖锐使得双方各自寻找盟友,英国与日本勾结签订了互助同盟,日本在德美的默许、英国的支持下立场更加强硬,于是日俄战争1904年爆发,最终日军在辽阳击败俄国陆军主力,占领东方第一军港旅顺,后在对马海峡歼灭了俄国长途跋涉的波罗的海舰队,这样日本在东北的势力得到迅速扩张。随之,日本的铁蹄肆无忌惮地践踏着东北黑土地,蹂躏着东北民众淳朴善良的灵魂。狂风般袭来的灾难像熊熊燃烧的烈火,炙烤着东北民众的焦灼伤痛的心,每一位东北人的愤怒被激发到了极点。萧红、萧军和他们的父辈兄妹们一样勇敢地投入到了汹涌澎湃的斗争潮流中,他们奋笔疾书,站在了思想阵地的前沿。民族救亡的思潮召唤着每一位东北民众,30年代东北农村大地从死寂沉睡中觉醒,民众冻结着的思想开始松动,农民不再一味顽固、闭塞、保守,而开始关注家园的存亡,许多民众甚至毁家纾难、投军从戎。
一地的自然景观和世俗风情等文化习传一起勾勒出该地的地域风情,这种地域风情又“以其潜在的方式向人们渗透着某种地域性的文化生存状态”,并自觉不自觉地规范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
萧红出生在宁静而落后的呼兰县城一个乡绅小康之家,“这里的居民大都是些保守而又迷信的农夫、手艺人、小贩、几个读过些书的塾师,以及所谓的乡绅们”。她的大多数乡土文学作品影射的都是这个让她爱恨交加的家乡——东北北部地区呼兰河小城及附近的村子。
萧军的家乡在辽宁锦县沈家台下碾盘沟村,距锦县西北近百里,属于辽西山区的腹地。“这里其实是东北开发历史最悠久的地区,大凌河与小凌河养育了辽西的古文明——红山文化。战国七雄并立时,这里属于燕,设辽西部。公元十世纪契丹人建立辽,是北宋时期北方的一个强国。”因此这里可称为“东北古代文明的前哨”。这里的民间艺术形式非常丰富,有大鼓书、唱秧歌、驴皮影等。但是自然资源却日趋消减,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代的变迁,这里的河流成了季节河,群山因没有了丰林和茂草而显得赤裸消瘦。于是“穷山恶水”便成了现在人们对这块土地常用的形容词。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食物是生存的第一需求,它不仅“能满足人们的生理需求,而且也因其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在一定程度上也满足了人们精神层面的需求”。不管生活如何穷困,食品总会给人以诱惑,给人以生存的希望和乐趣。
由于受纬度、地势、海陆位置等因素的影响,东北区属大陆性季风型气候,自南而北又跨越了暖温带、中温带与寒温带。其北部以种植春小麦、马铃薯、大豆为主,用它们作原料延伸出来的食品种类有:由小麦制作的面条、馒头(油炸馒头)、饼、饺子等;由大豆制作的豆腐、豆腐脑(穷人的美味佳肴);由黏米制作的粘糕(制作过程极具东北特色)……此外,还有用油炒出来的蚕、凉粉、炸鱼、饭团、烤玉米等等。有些食物的加工甚至受到了相邻国家的影响,如面包的普及就是如此。冬小麦、棉花、暖温带水果在辽南可以生长,但是在辽西由于土质差,多丘陵,这些作物的生长十分艰难。萧军作品中写到的这一带食品大概有:盐渍的咸菜、酱黄瓜、香瓜瓢、短绳似的绿豆角、凤仙花梗、咸肉、米、面、米粉做的干粮等。过节时会摆酒席,猪耳扇是上等的好菜。汪大辫子从狱里出来饿到极点时,最想吃的就是高粱米饭,再加一点豆酱和葱汁。零食有落花生、西瓜子等,由于多沼泽和山林的缘故,人们把河鱼在石片上煎烤着吃,还会经常上山打野兔子、狐狸等。此外,这一带的民众都喜欢饮酒,红事、白事、甚至平时遇上开心的事儿都要喝上几盅。两地调味品大多是有御寒作用的葱、蒜、辣椒等。当然,这些食物品种,大多数散布在民众日常生活中,也有一部分会出现在特殊的日子里,比如清明、中秋等节日,基于灵魂信仰及对未来幸福美好生活的期盼,食品的制作方式极为讲究,花样翻新。因此,同处东北,由于自然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不同地域的食俗也存在差别,辽西民众的食品种类及其制作方式明显不如北部地区丰富和精细。
人有社会性,人的社会意识、价值观念必然会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予以体现。从民俗学角度来看,民众在诞生、成年、结婚和死亡这几个阶段举行的特定仪式,就是“将社会个体生命加以社会化的程序规范和阶段性标志”。
萧红在《生死场》、《呼兰河传》、《后花园》中描写了东北地区原始驳杂的人生礼仪 。分娩有禁忌:五姑姑的姐姐生产时不能压柴草,只能像鱼一样在土炕上翻滚。婚姻风俗原始又野蛮:金枝嫁给成业是因为怀了他的孩子;王大姐没有媒妁之言就私自搬到冯磨倌的小屋里;冯二成子和王寡妇因同为生活的痛苦而大哭就住到了一起,两个寂寞的灵魂相互安慰着;团圆媳妇是用财物交换来的童养媳。丧葬礼俗中蕴含的是深刻的伦理道德观和对正常死亡与非正常死亡的区别对待:人死了有“报庙”的环节,祖母死了家人到龙王庙报庙,但是产后死的王大姐、未成年的小团圆媳妇还有因淹死、车祸死亡等非正常死亡的人都不能去报庙。作者还用大量笔墨描写了类似于现在花圈店的“扎彩铺”,“大至喷钱兽、聚宝盆、大金山、大银山、小至丫鬟使女、厨房里的厨子、喂猪的猪倌,再小至花盆、茶壶、茶杯、鸡鸭鹅犬,以至窗前的鹦鹉”,“凡是好的一律都有,坏的不必有”。
萧军作品投射的辽西一带的人生礼俗同样富有浓郁的地域特色。已婚的林四姑娘和本村青年杨三偷偷生的孩子一样得到了家人极度的喜爱;井泉龙一句话就把女儿大环子许配给了刘元。地主杨洛中过寿时的场面极其宏大:寿日前几天就开始杀猪宰羊,还要向村里人借一些需要的东西——锅、盆、桌、凳、铺铺、盖盖,亲朋好友也会陆续前来。寿日中午,在阵阵爆竹声中,拉开了拜寿仪式的序幕,唱礼先生在笙、管、云锣等雅乐声中主持拜寿,由家族内外,按着顺序,男女一对对地参拜,这时,乞讨的花子响着竹板唱着喜歌凑热闹,拜寿结束后人们开始吃酒席。丧葬亦有讲究:人死后要先准备好绳索、抬杠、挖好坟坑,办丧事时一般会有唢呐和大鼓来奏乐,往坟地送棺材的路上,棺材后面要跟着两人,一人手里提一壶高粱酒,另一人手里拿一些纸箔,棺材沉下地穴后的第一锹土要摔在棺材盖上,之后还要每隔七天烧一次纸箔,直到七七四十九天。同时丧葬观念也很特殊,他们认为坟墓里“埋得宝物越多就更能旺地气……发达子孙”,这里的“宝物”是一些值钱的东西。有权势的家族还会有自己的祖坟,朱三麻子死后就被埋在杨家坟地外的一块田端上。
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生礼俗渗透出来的是东北粗犷、纯朴的风俗民情。在这块黑土地上,儒家文化支配的传统价值观念较为疏离淡化,但寻常百姓对不可知事物的崇敬畏惧和对美好生活的无限憧憬却清晰可见。
二、 奇风异俗中蕴含的民众心理情感
萧红擅长描写民众的心理情感,在她看来,农民虽然没有高层次的文化修养,但也有专属于他们的独特精神盛宴,这种静穆中的狂欢弥散着他们的精神享乐,也在宣泄着他们的压抑和愤懑。
首先,呼兰河城每年都会有一些形式各异的盛大集会,如放河灯,野台子戏,娘娘庙会等。这些活动扎根在每个人的心中,而且将大家的心情牵引到兴奋的制高点。放河灯是七月十五盂兰会,这是中国传统的鬼节,人们为让那些“横死”的冤魂死鬼得以托生投胎准备了灯,希望这些灯能照亮从阴间到阳间的路。看放河灯的时候,“街道都活了起来,好像这城里发生了火灾,人们都赶去救火的样子。非常忙迫,踢踢踏踏地向前跑”。唱野台子戏是为了给龙王还愿,唱戏的时候“并不是简单的看戏,而是接姑娘唤女婿,热闹得很”。四月十八的娘娘庙会也是为鬼神准备的,无论男女老幼都会来逛。看起来热闹动人的场面,却反衬出乡土生活的封闭和单调。其实这些活动中更侧重于寄托民众美好的生活愿望,鬼神意识已经不是很浓厚,它们真正的价值在于调剂民众沉闷、寂寞的生活,让人们暂时卸掉生活的重负,让紧张的精神得到放松。
此外,还有一种活动十分独特,那就是萨满教支撑下的“跳大神”。萨满教是东北本土的原始自然宗教,到20世纪初,萨满文化在东北某些地区已经转变为制造迷信和悲剧的精神工具。《呼兰河传》里为小团圆媳妇驱鬼时举行的民间“跳大神”活动令人触目惊心。小团圆媳妇是一个“黑乎乎、笑呵呵的”、健健康康的十二岁小姑娘,但那些一直按祖宗规矩生活着的人们认为她“不像小媳妇”,于是对这个小姑娘开始了整治和管教。他们异常虔诚地用滚烫的热水来给她洗澡,为她祛邪驱鬼。来看洗澡治病的男女老少不下三十人,个个眼睛发亮,有的叫好,有的狂喊,有的虽然心慈流下了眼泪,但却并不觉得这样做有什么不对。看到她被烫昏过去,人们赶紧泼凉水救醒她,等她醒了之后又用开水烫她,直到她昏死在缸底。愚昧的民众把“跳大神”当作一种娱乐和消遣,他们幸灾乐祸地观赏别人受苦遭难,以此来慰藉自己空虚的灵魂。残忍、麻木滋生出来的病态心理让善良的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成了残害自己身边人的刽子手或帮凶。
除了大型的集会,人们在茶余饭后还会有自发的小聚会来暂时滋补心中的孤寂。他们端着饭碗或拿着针线活,地点一般都在院子里或者某家的炕头上,话题大多是家长里短。农民没有时间观念,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世世代代生活的法则。由于生活方式简单,娱乐活动贫乏,炕头聊天便兴盛起来,于是“长舌妇”比比皆是。说长道短、闲言碎语比普通的聊天更能刺激人的神经,带来异常的兴奋的同时,也满足人的好奇心和攻击欲。这是一种非常便捷的放松方式,它不会影响农人的耕作,但却可以给民众的精神带来强烈刺激,影响他们的精神生活,给受害者造成巨大精神压力,甚至可以谋害性命。王大姑娘与冯歪嘴子恋爱同居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他们骂人家“长的一身穷骨头穷肉,那穿绸缎的她不去看,她看上个灰秃秃的磨倌,真是武大郎玩鸭子,啥人玩啥鸟”。《呼兰河传》中的团圆媳妇也是随着流言蜚语的火焰见长而走向死亡的,二成子也在长舌妇的逼迫下过着悲惨窘困的生活。民众们在乐此不疲地捕风捉影、编造故事、飞短流长,窥探他人隐私的阴暗心理跃然纸上。


盗匪遍地的特殊现象也在淋漓尽致地诠释着这一特点。萧军的生活环境和他的作品无时无刻不贯穿着盗匪形象,渗透着侠义精神。萧军的几个叔叔先后做过盗匪,当过骑兵、义勇军。萧军的《第三代》也给我们呈现出一幅东北“胡子”的世界及其生活形态的巨型画卷:作品描绘了农民怎样一步步被逼上山当土匪,也形象展现了敢于挑战传统的辽西山区凌河村农民的苦难以及为了求生存而选择的道路。最具鲜明地域特色的还是在这块深厚的土地上大放异彩的土匪隐语,作者的许多作品对此表现得淋漓尽致。如在《八月的乡村》中:“还不如现在去到那‘绺子’(一帮)挂个‘注’(入伙)混二年”;“炮头”是指土匪队中的前锋,“秧子房”是土匪中看管肉票的;称胡子的首领为“当家的”,称胡子为“马鞑子”;称睡觉为“躺桥”,称放哨为“晾水”;称枪为“胳膊”,称绑来的人质——肉票为“秧子”或“财神”等。《第三代》中这群绿林好汉有他们的“绺规”,侯七曾做过海交的“小把式”(护兵),“崽子”是子弹,“开瓢”是杀头的意思,“跳子”是胡子们称官兵的隐语,“螳螂子”即不中用的人,“土包”为吝啬之人,“鬼豆腐”即诡计,“推八门”是指胡子中的迷信,以八卦的生克来决定他们应走的方向。
这生动有趣的土匪行话背后承载着的是一份厚重的地域风情,“土匪文化”是东北历史文化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在东北这片神奇的黑土地上,“胡子”不同于平常意义上的“土匪”,而是一群“义匪”。他们不仅有严厉的行规,而且干的是杀富济贫的义举。凌河村老英雄井泉龙就说过:“胡子们连我们的屁也没有抢一个”,“胡子”俨然成了“行侠仗义”的代名词。不难看出,“土匪”这种行当在这里已经内化成了一种民众悲壮的生存状态。他代表的是民众生存的勇气和威武不屈的抗争精神,也正是这种精神孕育了崇尚武力、刚烈彪悍、粗犷豪爽、见义勇为的地域传统性格。
女性身上永远闪现着美丽的光环,因为她们是生命的孕育者。除此之外,在中国女性身上更有勤劳、勇敢、贤慧、善良、充满母性温柔的爱等特点,这些特点更令她们的魅力持久而弥香。

而萧红笔下的女性更多的是温顺和柔弱。美丽的金枝对待丈夫成业的打骂,不是将柔弱凝集,就是把温顺深含,她没有反抗的能力和魄力;王家大姑娘黝黑的皮肤、两条粗大的辫子得到了乡邻的夸赞,但是当她和冯歪嘴子同病相怜而走在一起后却引起村民极度的厌恶,接二连三的谣言和刁难最终还是让王大姑娘悲苦离世;勤劳的王婆在被迫卖掉家里的老马时痛不欲生;打鱼村最美丽的月英瘫痪在炕后只能嚼着无尽的泪水痛苦度日……而男人们对老婆除了打就是骂。这一群女性勤劳、善良、美丽,但她们是那么不堪一击,连自己的生存都无法保障,更不用说支撑她们的家庭了。

三、 萧红、萧军文学创作折射的东北地域精神
(一) 雄强的生命意识


与萧红作品中的朴素倔强的生命意识相对照,萧军的作品中弥漫的更多的是东北民众强烈的反抗意识。在由短暂的春天、深邃的秋空、冻结的河水、大半个年头干涸的凌河共同建构的时空里,家乡农民痛苦地挣扎与反抗着,同时也在简单地思索着生与死。他们的生活中洋溢着野蛮的气息:《八月的乡村》中的青年寡妇李七嫂直率地和农民唐老疙瘩保持着情爱关系;《第三代》中林青的女儿四姑娘嫁给了一度显赫的上等贵族之家,然而她还与自己喜欢的杨三偷情并生下了孩子,令人惊奇的是这种“野合”事实上得到了父母及村民的默许;而“投降”过来的杨三放荡地同许多女人保持着性爱关系。他们的“生”不受封建礼教的羁绊,突破了世俗的偏见,活得狂放而潇洒。乡民的“自我意识”使他们对于“死”也有独到的见解:在埋葬三麻子和春二奶奶时杨五爷感慨道:“人是什么呢?生了死,死了生……我们若不死……小孩子怎能会长出来呢?人还是应该这样才对,像凌河的水似的,流啊,流啊……新浪换旧浪。”
辽西民众自由狂放、坚韧质朴的地域性格鲜明突出,他们与生俱来的反抗魄力,更是让人赞叹不已。土匪精神——只要有人要毁灭我的生活,我就要起来反抗到底——无时无刻不在淋漓尽致地发挥着它的巨大威力。在对付大地主杨洛中和官府的斗争中,“胡子们”夜袭凌河村、火烧杨家柴堆、绑架杨洛中的儿子并“撕票”割掉他的耳朵……井泉龙领头反对地主,鼓动村民打胡子,率领村民抵制为地主护院的不合理行为,支持胡子打击地主的嚣张气焰,对官兵把无辜村民抓走的行径敢于挺身而出、仗义执言。翠屏与大环子、四姑娘也走上了叛逆的道路。他们无所畏惧,死在他们心中算不了什么!翠屏在丈夫大辫子被抓后对邻居说:“大辫子就是教他们砍了头我也要生活下去啊!我有孩子……他们是一年一年向上长大的,就是在钉板上我也要滚着活下去。”辽西民众强悍野性的生命力在这里得到淋漓尽致的表达。
上述这种生命意识和生死观是在凝聚了多种因素之后逐渐形成的。其一,东北的气候远不如中原温润,地貌也极其复杂多变,这一方面给东北民众的生存带来了极大的挑战,让他们明白了生活的艰辛和死亡的无常;另一方面,这也磨砺了他们坚忍的意志和顽强的信念,鼓励着他们积极进取,为了生存而进行不懈的斗争。其二,东北地区地处中国边陲,该地区的民众与外国人交往必然会很频繁。然而封建社会末期中国因落后而导致被外国人压迫的阴影一直没有得到消除。这种卑微的生活姿态一方面孕育着一种无奈的豁达,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积蓄着一股顽强的意念。其三,农民的生存空间很特殊,前院生活着人、家禽和牲畜,左右的地里种植着蔬菜、水果以及庄稼。放眼望去,视域内的某块地就是家族墓地。他们可以很淡然地去谈论一个村近年死去的老邻居或是邻村的熟人,老人可以很从容地谈起自己死后的事,在他们心里死亡是那么司空见惯。恐惧不是没有,而是早已习以为常,习惯渗透于心就幻化成了豁达。

(二) 质朴粗犷的民风习性
东北地理上的偏远闭塞使得人们视土地为命脉,加之求生本能和原始欲望在农民心中占据重要位置,使得农民对庄稼、牲灵产生了极其强烈的感情,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畸形的爱。“无论一棵菜或是一株草也要超过人的价值”,这正是农业社会的特征,也是农人所崇拜的道德价值观念的体现。对农人而言,无论是一匹马、一头牛或是一只羊,都是他们的命根子,甚至看得比他们亲子女还重要,于是我们就不难理解《生死场》中赵三就因失手杀死了小偷而不得不卖牛偿还,从此陷入痛苦并结束了一生;二里半加入义勇军的同时不得不舍弃了心爱的老山羊而产生的无比痛苦的心情;以及老王婆为了还债被迫牵着她那匹老马去屠宰场时的悲怆和哀怨等等,诸如此类的情感都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八月的乡村》中的三东家发誓要守着这样一片宅子和一千垧地;陈柱在鼓舞士气时也在强调着土地的重要性,“东家的儿子、闺女们全念书,念完书就做官,做官就有了钱,有了钱就买地,钱越来越多,田地也越来越多,结果有钱有地的子弟永远是用不到劳一点力气……”《第三代》中从俄国归来的林荣深情地唱着:“我们吃的是黄金似的小米呀……三月桃花色的高粱米饭呀……哪里长出的树木啊,就爱哪里的土地。”这些都典型地反映出了人们对土地、牲畜的无比依恋和热爱。

感情粗糙对于普天下的农民是正常的,因为每个人都尴尬地生活在难以言说的贫困中。当一个人从灵魂到肉体都在不停地为生计操劳忙碌时,温情和爱距离他是多么遥远!东北农民似乎更甚,一方面是因为东北处于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边缘地带,受传统文化影响相对薄弱,知书达理在这里没有深厚的生存土壤。虽然后来有大批关内汉人“闯”来,但是多为下层人民,求生的艰难以及底层身份使他们缺少接触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的机会,甚至还具有粗俗野蛮的成分,所以他们仅有的琐碎的中原文化根本无法对东北原生文化形成大的整合与涵化。另一方面,东北地区独有的自然景观整体上的“雄犷、伟烈、严酷”,决定了生活于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在为生存而同自然搏斗的过程中需要付出“巨大的、强悍的、艰难的”劳作,需要“强悍的、粗犷的乃至野蛮的意志、精神和心理”,久而久之,就会转化为一种“雄犷的、粗放的”粗疏的人格和身心特征,鲜有细腻精致的个性。
尽管人的情感浸透、饱含着血泪,表达方式略显粗糙,但依然厚重有力。王婆在女儿小钟死后说不后悔,这能是真的吗?恐怕她真正不后悔的是自己对劳作的勤勉和专心,而对女儿怎能割舍得下骨肉之情呢?所以后来她又说:“可是邻人的孩子却长起来了……到那时候,我好像忽然才想起我的小钟。”“我接连着熬苦了几夜没能睡,什么麦啦,从那时起,我连麦粒也不怎么看重了”。成业在摔死孩子后,“年轻的妈妈过了三天到乱岗坟子去看孩子……成业他看到了一堆草染了血,他幻想着是小金枝的草吧!他俩背向着流过眼泪”。翠屏在入绺多时后便成为“胡子女管家”,虽然同羊角山上的人相处融洽,但当她出狱后的丈夫汪大辫子和孩子让她回去时,她还是动摇了;汪大辫子离开胡子山时一再“恳求”刘元给家里带个信,最后刘元才说:“你见到我的妈妈和第三个妹妹……就说不要惦记我……我的脑袋还很好地长在脖子上。”可见人类固有的情感是不会因性格品质的粗粝、表达方式的粗疏而消失的,反而会被这种质朴粗糙发酵得愈加严肃和厚重。
(三) 愚昧和善良建构的思想二重性
东北地域相对偏远,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封禁,这种原始、封闭、落后的地域经济文化在东北人心里投下了愚昧、麻木、保守的阴影。在这里,乡民的生命力是被压抑的,被赤裸裸的贫困及其伴生物——愚昧压抑着。自私狭隘的他们喜欢看别人的不幸,在他们心中只有自己和自家,没有集体意识,更不会有共赢观念。农民的自私愚昧使得家庭邻里之间的氛围带上了残酷的色彩,同时也带给他们与外力压迫程度不相上下的严厉的报应与惩罚。
呼兰城东二道街上有一个五六尺深的大泥坑,混沌不堪,陷溺车马行人,淹死猪狗鸡鸭。但是呼兰人宁可绕道而行甚至铤而走险,也不试图去改变现状。他们没有一个人想着用泥土把泥坑填平,甚至恨不得每天都有东西陷进去,从而得到片刻的“欢愉”和“消遣”;只因那个牙科医生广告牌上画的牙齿太大,人们便不再光顾,即使牙疼得非常厉害,也没有人进去求医。团圆媳妇的婆婆请萨满来跳大神真的是要治儿媳妇的病吗?在她的内心深处隐隐有一点私心:这样也能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到她家。农人们坚决反对任何改善他们生活的举动,在这个欢欣消逝、恐惧弥漫的黑暗深渊中,谁要是呈现出一点生命的新意和亮色,就会被强大的传统激流所吞噬。《第三代》中凌河村的农民们,“如果遇到天气晴好,喜欢从自己的家里活动出来闲走在街上,或是聚集在谁家墙院的前面……也许把背脊倚靠了墙壁,手交叉的藏在袖筒里,消遣地唾着口水,发挥着各种奇妙的意见,讲谈着各样的事情……冬天人们唯一的趣味就是盼望能够发生一点值得谈论的谣言,即使为了这谣言而发生一两场决斗也觉得是分内的勾当”。汪大辫子、林青被无缘无故抓走,村民们却无动于衷,井泉龙动员村民失败后无奈地说“讲讲公理的人总不像有酒吃的时候那样多?”他们畏首畏尾、固步自封、目光短浅,同时却将农夫的勇敢自信、淳朴健康的优秀品格视为自大和傲慢,真是可怜又可悲。

当然和谐融洽的乡土关系隐藏着闭塞守旧的农民意识,善良淳朴的农民也透露出愚昧无知的一面,他们最容易被迷惑,一旦被愚昧附身,带来的后果可能无比惨重。总之,善良与愚昧,淳朴与守旧,共同编织着乡村社会的人际关系之网。
结语
透过萧红、萧军的乡土文学创作,我们隐隐嗅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东北民众雄强坚韧的生命力、质朴粗粝的情感和愚昧却善良的品性。雄强的生命力锻造了他们坚忍不拔的精神,给予他们生存下去的勇气和力量;质朴粗粝的情感积淀了他们爽朗豁达的情怀,使他们的生活飘散着单纯而又快乐的芳香;而愚昧与善良的品性却引发了村民之间的一场场无硝烟的战争,于是悲剧成了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情节。这些地域品质从该地民众诞生起就渗入了他们的血液之中,共同谱写了一曲曲悲喜交加的时代乐曲,成为他们奔波劳碌的内在驱动力,也正是这些地域精神支撑着黑土地上的东北民众世世代代生生不息。

注释
:①露丝·本尼迪克特著,王炜等译:《文化模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5页。
②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③齐秀娟:《地域文化视野中的萧红小说及其创作心理研究》,东北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
④任金凤:《萧红对北方乡村的客观再现与主观沉思》,《边疆经济与文化》2004年第10期。
⑤葛浩文:《萧红评传》,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9~10页。
⑥程义伟:《东北土匪文化与现代作家萧军的文学创作》,《小说评论》2007年第1期。
⑦朱希祥:《东北人的食品与生活——萧军、萧红作品中的饮食文化》,《食品与生活》2000年第3期。
⑧萧红:《萧红全集(下)·呼兰河传》,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版,第720页。
⑨萧军:《第三代》,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1页。
⑩萧红:《呼兰河传》,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175页。












山西大学文学院;商务印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