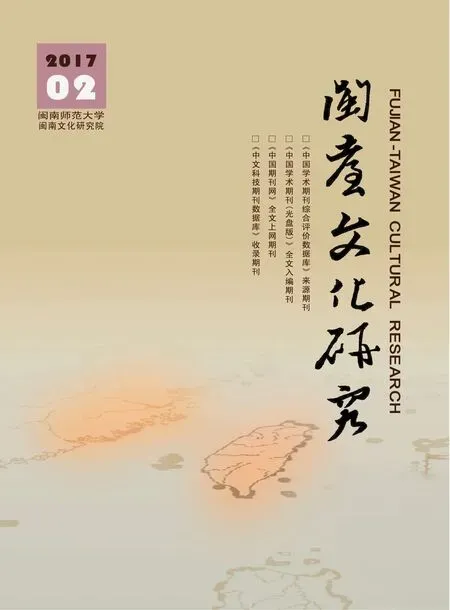宗教意识与人性视角下的生态思考
——论台湾当代作家王鼎钧的散文《那树》
2017-11-14陈想
陈 想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两岸文化发展研究中心,福建福州350007)
宗教意识与人性视角下的生态思考——论台湾当代作家王鼎钧的散文《那树》
陈 想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两岸文化发展研究中心,福建福州350007)
在《那树》中,王鼎钧运用象征的手法,将人性中的美与善赋予“那树”。与此相反,人类则被人性的恶所吞噬。在宗教“慈悲为怀”“生命轮回”等观念的深刻影响下,王鼎钧赋予树主宰命运的神性,使树实现了神性和人性的统一。同时,拟人、夸张等修辞手法的运用,不仅写出了树的坚强与无私,人的冷酷与残暴,而且表达了作者对人与自然的热切关注,对人类肆意破坏生态环境的极度痛恨。事实上,“那树”最终被砍伐的悲剧,指向的是更深层次的人类的悲剧。人类的贪婪与短见是造成悲剧的根本原因,但作者具有“宽恕一切”的宗教思想,始终没有出离愤怒。通过《那树》这篇“通达”的散文,作者展现了悲天悯人的宗教情怀,表达了对生态问题的极大关注,对人性之恶的无情批判,对人类社会的深刻思考。
宗教意识;人性视角;《那树》;王鼎钧;生态散文
中国台湾的“自然书写”(或称“自然写作”)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随着科学技术不断发展和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一系列环境问题由之产生。台湾有识之士“一开始即面对了崩坏的环境”,产生了“人类对待自然道德选择权合理性的反省意识”。于是,他们纷纷开始了有关台湾自然问题的书写。这些作品中,被大陆多个版本的语文教科书收入的散文《那树》与一般的“自然书写”不同,王鼎钧并非从自然生态的考察和动植物的观察描写入手,而是从代表人类物质文明不断进步的城市建设与自然生态的冲突不断加剧的角度切入。通过一棵象征高贵人性(甚至是神性)的树与一批现代化的人之间的强烈冲突,以及代表自然与生态之“善”的“那树”最终被砍伐、连树根也被闷死的残酷结局,一方面,作者无情地批判了人类破坏自然与生态环境的“恶”,体现了他对不断恶化的环境的关切,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另一方面,作者运用极具象征意味的手法,展现了他“对美好人性的守望”,对自然神性的崇敬,以及希望以此唤醒人类爱护自然、保护生态的恻隐之心;再者,也可管窥作者对宗教尤其是佛教的痴迷、对“慈悲为怀”和“生命轮回”的笃信。此外,树的一生与其他生命的关系也展现了人性的善恶与生命的轮回。
一、宗教意识
《那树》中,经过两天两夜的暴风骤雨,树木全被吹断,房屋倒坍无数,只有“那树”屹立不动,庇护着生灵。事实上,“那树”给人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安全感,更是心灵和精神的寄托。据记载,王鼎钧的母亲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宗教信仰十分坚定,这不仅较早地启蒙了他,而且深深地影响了他的一生。王鼎钧曾说过:“我是基督徒,但是在文学的欣赏和创作方面佛教对我的影响较多……作家也像佛一样,他不能改变因果,但是可以安排救赎……他同情每一个人。”显然,无论是基督教还是佛教,都对王鼎钧的思想和作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就《那树》来说,一方面,当危急的警报声响起时,住在不安全的旧公寓里的人们就会在树洞里插上一柱香——在这里,王鼎钧同情每一个人,当人们遇到无力抗拒的灾难时,他便像普度众生的佛一样为人们带来精神的寄托;另一方面,当人们把香插在树洞里时,树就成了“佛”的载体和“神”的象征——在人类无法抵挡天灾人祸时,只有神与佛才能成为人们心灵的慰藉。
王鼎钧曾多次指出:“神无所不在,在希望中也在绝望中,在胜算里也在败象里。”不言而喻,王鼎钧的这一思想认知是根深蒂固的,因为:在文学作品中,他常常用反衬的手法写到神的无所不在。不过,他笔下的人总是忘了神的存在,只有身处绝境时才积极寻求神的帮助。表现在《那树》中,人们总是忘记树的存在,只有在狂风骤雨来临、人力无法抵挡时才想到一直守护在身边的“那树”。在那充满宗教仪式感的行为中,树不仅守护着人的肉体,也呵护着人的心灵。树的神性还体现在:风平浪静之时,树总是不求回报地给行人带来凉爽,给鸟儿带来自由,给孩子带来欢乐,给情侣带来甜蜜。在这里,树甚至成了整个自然界的代表,它总是默默地给予人类以无私的援助和无限的关爱。值得注意的是,树不仅对人类加以庇护,对其他生物来说,它同样展现了预知生死、慈悲为怀、普度众生的“神”(“佛”)的精神。《那树》中,当那棵百年老树预知到自己将被砍伐后,便告诉“体内的寄生虫”——树干里的蚂蚁,让它们大搬家。在这带有强烈的宗教神话色彩的叙述中,王鼎钧进一步展现了“那树”的通灵神性及其对自然万物的怜爱。
纵观王鼎钧的散文,不难发现其“通达”的特点。在一次访谈中,作者讲道:“人和人为什么冲突?就是都认为自己是对的。其实,在佛家居高临下来看,都是错的,但是他不能不那样做,纠缠一世,到死方休,甚至于按照佛教的理论,还要轮回,还要斗,所以双方都值得同情。”显然,以佛的眼光俯视芸芸众生,按佛教因果报应的观念关照人事,世间的一切都是“轮回”的、没有止息的。所谓“六道轮回”,现在,人们剥夺大自然中树的生命,之后,大自然必将狠狠地报复人类。佛教的轮回观在生态问题上显然是有其积极一面的。人的寿命只有几十上百年,因此,“及时行乐”就成为人类主要的生存理念之一——既然生命如此短暂,不如尽情享受。显然,这给生态保护带来了极大的威胁。所以,在这里探讨“轮回”是大有必要的。
在远古时期,由于科学技术的落后,人类还处于蒙昧状态,对大自然的神秘充满敬畏,对传说中的神灵满怀虔诚。如今,随着科学知识不断的丰富,人类认识世界的能力不断提高,但是,人类仍旧没有走出迷茫。“上帝曾说:‘你绿在这里,绿着生,绿着死,死复绿。’”借着上帝之口,作者由衷地赞叹着树的生生不息与无私奉献。在这里,树已不单单是树,事实上正代表着生命万物。由此可见,作者通过对“那树”的精心描写,试图向我们展现的,不仅是绿色生命的延续而且是世间万物的生命轮回。树的“死亡”并不代表生命的停止,它在被迫害前让蚂蚁王国搬迁,其实也是一种生命的延续或者说是轮回,但与一般的轮回不同,这种轮回是通过其他生物的存续得以实现,充满了宗教的神秘色彩和神话的传奇色彩。
众所周知,许多古代哲学家都曾对“轮回”作出过重要论述。例如毕达哥拉斯,他是古希腊提出灵魂轮回说的第一人;再如柏拉图,他曾在《理想国》中借助厄洛斯之口阐述了人类灵魂的轮回过程。其实不仅哲学,几乎所有的宗教都有“因果报应”和“业障轮回”之说,佛教当然不会例外。在“轮回”哲学或宗教思想的影响下,王鼎钧让树的生命在蚂蚁王国的存活上得到了延续,实现了“轮回”。我们完全可以将“那树”和人类进行类比:生活中,有很多母亲为了挽救孩子的性命而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这些孩子显然正是母亲生命的延续。因此可以说,树在这里实现了神性和人性的统一。
《那树》中还有两处不容忽视的细节描写:其一,乡下来的清道妇认为“那树”是通灵的,在被砍伐前,就预先知道了,并将灾祸提前告知靠它生活的小动物们;其二,在“那树”被砍伐后,只有与树为邻的老太太固执地说听到了老树的叹息声。通括起来看,似乎只有淳朴善良的人才听得到大自然悲切的呼声。看似荒谬,实则批判了现代人的麻木。当然,这也说明自然万物都是有灵性的。吊诡的是,蚂蚁们在离开前围绕树干一周的举动宛若一种宗教仪式。其实,无论是远古的先民还是某个部落的土著,甚至是现代一些地区的人们,在祭拜祖先(神灵)或其他宗教仪式中,常常围着某个人或物转圈。被围的人或物正是所谓的 “神灵”(或者说是 “神灵的象征”)。荣格(Carl Gustav Jung)曾记录过澳大利亚一个土著部落“春之祭”的仪式:人们在地上挖一个椭圆形的洞穴,在其周围铺满灌木丛,使其看上去像女人的生殖器,随后,他们环绕这个洞穴跳舞。可以说,大部分的部落都有生殖崇拜,因为:生殖崇拜在本质上是对生命和希望的崇拜。“春之祭”体现的就是人们对生命的崇拜,蚂蚁们对树的环绕同样如此,当然,同时还带有感恩的意味。“那树”正如一位母亲一样,无私地孕育了蚂蚁家族;有了树,蚂蚁就有了生命,生活就有了希望。
二、艺术手法
早在18世纪的欧洲,“生物链”(biological chain)一词就被普遍使用,从而成为一个常见的术语。英国学者詹恩斯认为,“生物链”这一术语除了突出人类与自然界其他动植物联系的密切外,还特别强调生态圈内的平等公正,也就是强调人与其他生命在自然界中的地位是平等的。毋庸置疑,在“生物链”上的每个物种都具有同等的价值,每种生物都是自然的代表,文中的那棵树就象征着整个大自然。在两天两夜的狂风大作、暴雨肆虐中,“那树”屹立不动,全然不似其他被拦腰截断的树和被狂风吹倒的房子。丹纳曾指出:“艺术的本质在于它把一个对象的基本特征,至少是重要的特征,表现得越占主导地位越好;艺术家为此特别删节那些遮盖特征的东西,挑出那些表明特征的东西,对于特征变质的部分都加以修正,对于特征消失的部分都加以改造。”诚如其所述,艺术形象是生活真实与作家心象结合的产物,作家通过选择客观事物并结合思想情感表达的需要,对客观对象加以调整和改造,以求展现作者想要突出的事物的某一重要特征。也只有这样,艺术形象才有可能成为经典,艺术作品才有可能永世留存。在这里,王鼎钧运用夸张的艺术手法,写“那树”甚至一片叶子都没有掉下来,实际上正是他对“那树”牢固稳定的特征的突出与强调,对“那树”坚强执着的品性的赞美与喜爱。正因为有了这种特性,“那树”才给予人们极大的安全感。显然,树在这里象征着美好的人性,既有男性(父亲)坚强、刚毅、深沉的特质,又有女性(母亲)温柔、慈祥、博爱的特性。
有人不禁提出质疑:文中的“那树”被作者写得太神了,现实中并不存在。事实上是因为作者在行文过程中运用了象征的艺术手法和夸张的修辞手法。不过,退一步来讲,即使如以上质疑者所述,也不妨碍作者的写作与表达,因为“作家对对象世界的理解、反映和阐释,只要合情合理,他的作品就会具有‘真实性’的品格;而具有‘真实性’品格的作品,能让读者产生信任感及认同感,并因其与‘善’、‘美’相统一而为之所吸引、所感动,从而获得思想上的启迪和精神上的享受。”王鼎钧对“那树”的抒写,显然是合情合理的。正因为恰当地运用了夸张、拟人等修辞手法,才成其为一篇经典的散文作品。
人们常说“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丰富的社会生活,但与此同时,它也带来了数不胜数的、不可忽视的麻烦甚至是危机,其中之一便是对自然生态和社会环境的破坏。有研究者就指出:王鼎钧“在老树象征体系的最深层,揭示出了台湾当代社会中工业文明对传统文化的步步进逼与蚕食。”可谓一语中的。事实上,压路机将“那树”的根须碾压进灰色的水泥路下,体现出的不仅是工业文明对传统文化的逼近与蚕食,而且是工业时代乃至后工业时代对美好人性的侵蚀与摧残。然而,这似乎并不影响“那树”对人类的态度,它像我们忠贞不渝的恋人一样,秉承着“纵使虐我千百遍,我仍待你如初恋”的理念,同时又像我们的衣食父母一样,无怨无悔、尽己所能地奉献着自己的一切。而人们,似乎仍旧心安理得地享受着树所付出的一切。
曾经,一些工头和科员多次试图将“那树”毁灭,它都坚强地、乐观地、幸运地活了下来。可是,“好景美丽不长在”。经济的繁荣发展使人们的生活节奏不断加快,于是,人们慢慢地变得焦躁起来,渐渐地对树产生了反感。随后,车站、果摊、幼儿园等纷纷搬走。尽管“那树”给人们带来了清凉,给孩子带来了快乐,但人类却远离了它,远离了自然。即便如此,“那树”依旧“屹立不动”,连一片叶子都没有落下。树作为扎根大地的土著,冒着生命危险,顽强地绿着,像神灵一般悉心地守护着一代又一代的自然界精灵和逐渐冷漠的人类。这里,作者再次用拟人的手法写树像母亲一样,用夸张的手法写到树连一片叶子都没掉,同时,用树的“静”和人的“动”形成鲜明的对比;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进一步突出树的坚韧、顽强、专一、无私和宽容,表达对树的敬意与喜爱,对人的批判与担忧——人类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变得浮躁、功利起来,人性中的黑暗面不断地侵蚀着人类的精神世界,进而逐渐对身边的自然事物的美与善视而不见。
20世纪频发的战争使台湾社会的各个方面均遭到严重破坏。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台湾处于恢复期,政府亟需通过发展经济来解决民生问题,从而放松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普通民众则急于改善生活状况,再加上环保意识的淡薄,便在忙乱中忽视了环境破坏的严重后果。因而,台湾的经济发展了,环境却被破坏了;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却日益加剧。《那树》中,一驾驶者酒后驾驶,撞到树干后死亡,交通“专家”竟然宣判树要偿命。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导致树被“杀害”的理由竟是如此荒唐、如此可笑,作者流露出的反讽意味可见一斑。
此外,作者在描写屠杀情景时,使用了“咬”“嚼碎”“白森森”“骨粉”等十分残忍、异常血腥的字眼,无不挑战着读者的心理极限。树对人的恩将仇报、冷酷无情极度的忍让,也对人类肆意破坏环境的后果充满了无尽的担忧,但是,它只能在倒地时发出一声声呻吟和一阵阵沉重的叹息。诚然,那一阵阵叹息是树的无可奈何的哀叹,但又何尝不是作者的沉重叹息呢?通过“那树”惨遭肢解、挖根的悲惨场面,作者所要表达的不仅是对它的留恋和哀悼,而且是对无法改变的“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的无可奈何和满腔愤怒。
三、悲剧色彩
鲁迅曾指出:“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由此观之,树的毁灭也是一种悲剧,因为它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众所周知,悲剧的观念“是在人类感受到自我与整个宇宙、整个大自然、整个世界的分裂和对立中产生的。整个宇宙、整个大自然、整个世界是人类生存的环境……它的意志与人的意志常常是对立的。”换句话说,虽然人类属于整个宇宙、整个大自然、整个世界的一员,与其关系异常密切,但整个宇宙、整个大自然、整个世界均有其自身的规律,而且这种规律是人类意志所不能控制的;于是,在人类与宇宙、自然、世界的分裂、对立中,人类的悲剧观念便产生了。但是,人与自然的对立并非从古至今一直存在。我们知道,中国早就有了“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人与自然的“统一”事实上远多于“对立”。在农耕时代,人们总是开源节流、不违农时,所谓“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像这样,男耕女织,自给自足,中华民族延续了几千年。然而,自人类进入“工业时代”后,人与自然的“对立”渐渐超过了“统一”,人类对自然的破坏日益严重,人与自然的关系日益紧张,人性中的恶不断地暴露出来,当然,大自然对人类的惩罚也随之而来。我们知道,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求变求新的过程。人在情感上对自然母体本能的依恋与人的内心对不断发展的社会的期盼所形成的冲突,使这个社会不得不在悲剧性的矛盾中屈辱前行。毫无疑问,王鼎钧正是体会到了这种悲剧意识,才将它内化并集中展现在“那树”这一特殊的形象之中。
显然,人的欲望是永远都无法满足的,正是人类的贪婪(无休止地、一味地、不顾一切地向大自然索取)造成了今天的悲剧。更可怕的是,人类已经变得麻木不仁。“那树”的最后结局是:代表工业文明的“电锯”在深夜里无情地将其“屠杀”“肢解”,它的“头颅”(树桩和较大的树根)也被挖走,刽子手们残忍地切断了它的“动脉静脉”(较大的树根),修路工人无动于衷地将它的“坟墓”(树坑)填平,让它的“子孙”(较小的树根)一起“陪葬”,并将其一起“闷死”在地下。伐木工人们一系列训练有素的动作,仿佛刽子手将一位蒙冤的好人先凌迟处死,然后分尸,最后活埋。作者运用拟人的手法,写得生动形象、真实可感,让人读之发颤。
文中还有一处“皮里阳秋式的细节描写”值得注意:在“屠杀”过程中,刽子手们举镐挥斧的影子投射在路面和公寓的墙上,如“巨无霸”。在大自然面前,人类真的能如巨人一样,将自然踩在脚下吗?人类真的可以征服自然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事实上,那巨无霸的形象只是漆黑的影子,是虚幻的而不是真实的。也就是说,路面和墙上的巨人形象只是人类在幻觉中的自我想象,只是人类在现代科技映射下的自我心象(心中的形象)。文中,刽子手们虽有“利斧”和“美制十字镐”,但仍旧付出了比预想多得多的汗水。表面上看,“那树”虽被砍伐但根未腐朽,依然可以顽强抵抗;事实上,这是作者借“那树”之口,对人类疯狂地、残忍地破坏生态环境的又一次强有力的控诉。从这皮里阳秋式的、极具讽刺意味的细节描写中折射出来的,是人类的盲目自大与冷酷无情,是人类对科技的过分推崇与盲目自信。这是“那树”的悲剧,又何尝不是人类的悲剧?
事实上,“那树”虽然被屠杀殆尽,但它还有灵魂。摩托车骑士挑战法律的权威,“以违规为乐”,在树坑未被填平前仍旧向前冲去。结果,这些人个个受伤。在这里,虽被挖根但未完全死去的“那树”被作者塑造成了一个公正的“上帝”形象(或者说是“神”的形象)。“人在做,天在看”,违规的人必然要接受惩罚,所谓“因果报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王鼎钧的宗教思想渗透在文中的每一个地方。其实,面对大自然,人类一直有一颗敬畏之心,但如今,这种敬畏已被发达的科技所带来的优越感挤压到了心中的某个角落。在这里,作者的内心是十分复杂的,既对发达的现代科技和肆无忌惮的人类充满着悲愤,同时又倍感无力,因为人是最易健忘的动物,时过境迁,大自然对人类的惩罚必将被忘得一干二净。从这个角度看,《那树》所写的,不仅是表面上的树的悲剧,更是深层次的人类的悲剧。
重新回顾“那树”的一生,愈见其神性、人性和悲剧色彩。当树还是幼苗时,上帝便伸手施洗,如同基督徒的受洗仪式。显然,“受洗”就意味着洗去一切污秽、一切罪恶,使受洗者如获新生,同时也表明信徒与主同在。随着树的慢慢长大,它开始为人类带来清凉、遮风挡雨,为孩子们提供免费的活动场地,为小动物们提供永久的栖身之处。而后,当树“冒死掩覆已失去的土地,作徒劳无用的贡献,在星空下仰望上帝”时,“没有说什么”,“上帝也没有”,“一切预定,一切先有默契,不在多言。”“那树”之所以“不言”,是因为宗教存在的意义就是“爱”,越是黑暗越需要光明与希望。显然,“那树”在这里扮演了上帝的角色,它不求回报地给予了人们无限的爱。然而,对于“那树”所付出的一切,人们都不以为意,大概是习惯了——因为习惯,所以觉得理所当然。最后,忘恩负义的人们甚至将那无私的、赤诚的爱铲除殆尽。人类的所作所为让我们震惊,更让作者愤怒,由之,他创作出了《那树》这篇名作。不过,由于王鼎钧深受宗教(特别是佛教)的影响,面对“那树”和人类的悲剧,他始终没有出离愤怒。可以说,“那树”自始至终的沉默无声不仅显示着它上帝式的宽容,而且展现了作者悲天悯人、宽恕一切的宗教情怀。
总之,在这篇著名的生态散文中,王鼎钧通过对一棵富有神性的大树最终被铲除殆尽的悲惨命运的哀叹与同情,展现了他对宗教、人性、命运、生态的深刻思考。在他的笔下,“那树”不仅仅指那一棵树,也不单单指植物界的树,而是指像“那树”一样的人和物;它不仅具有高贵的人性,而且具有生命和希望的神性。显然,作者在赞美树的同时,也表达了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几多无奈和无限哀伤,对人性和人类社会的深刻思考与无情批判。
注释:
[1]吴明益:《台湾自然书写的探索——以书写解放自然BOOK1》,新北市:夏日出版社,2012年,第10页。
[2]主要有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九年级下册)、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九年级上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九年级下册)等。
[3]孙景鹏:《人性的掘进与守望——论刘庆邦<红煤>中的终极关怀意识》,《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4][6]张冠梓,王鼎钧:《天地有文学,杂然赋流行——-著名散文作家王鼎钧访谈录》,《南方文坛》2013年第3期。
[5]王鼎钧:《左心房漩涡》,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87页。
[7][17]课程教材研究所、中学语文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编著:《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 语文九年级下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75页。
[8][美]霍尔,诺德拜:《荣格心理学纲要》,张月译,郑州:黄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78页。
[9]王诺:《欧美生态批评:生态学研究概论》,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年,第100页。
[10][法]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第27页。
[11]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51页。
[12]黄重添、徐学、朱双一:《台湾新文学概观》(下),厦门:鹭江出版社,1991年,第195页。
[13]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03页。
[14]王富仁:《悲剧意识与悲剧精神》(上篇),《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
[15]万丽华、蓝旭译注:《孟子》,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5页。
[16]孙景鹏:《没有“茴香豆”,就没有<孔乙己>——试析<孔乙己>的细节描写》,《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责任编辑 李 弢〕
Ecological Thinking on Religious Consciousness and Human Vision——On Modern Taiwanese Writer Wang Dingjun’s The Tree
Chen Xiang
In The Tree,Wang Dingjun symbolically imparts human’s beauty and kindness into “the tree”,while humans are swallowed by the humanity’s evil.Being profoundly affected by the religious concepts as “compassion” and “life circle”,Wang Dingjun gave the tree divinity that can master their own destinies,which made the tree achieve the unity of divinity and humanity.At the same time,using rhetoric and personification,it not only revealed strong selfless tree,and cold-blooded and brutal people,but also expressed author’s concerning about the people and nature,and ultra hates on the people who destroyed the balance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In fact,the tree’s being cutting-down finally demonstrated a deeper-level tragedy of human.Human’s greed and shortcoming are the causes of the tragedy,but the author’s religious thoughts of“forgiving” has never magnified his anger.Through the well-knit prose,the author shows the religious feeling of compassion,the great concerning about ecological problems,ruthless criticism on the evil humanity,and deep thinking on human society.
religious consciousness,human perspective,The Tree,Wang Dingjun,ecological prose
陈想(1992~),女,福建福州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师范大学两岸文化发展研究中心2016级硕士研究生。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国现代小说文体的审美构筑形态研究”(2015BWX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