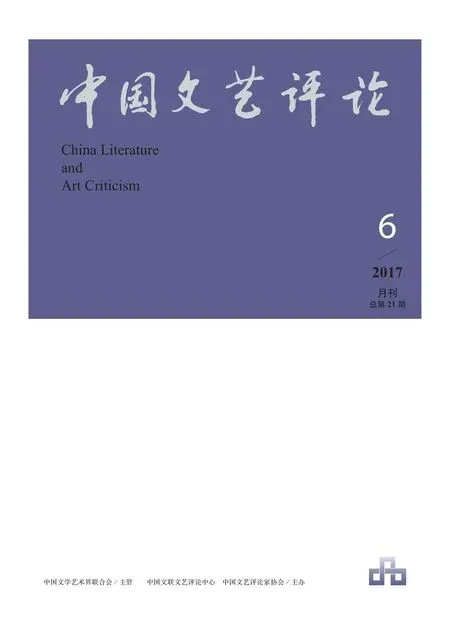观点摘编
2017-11-13
观点摘编
电影“中国梦”应是个人梦想的升华
陈犀禾、刘吉元在《电影艺术》2017年第2期撰文指出,中国梦要求电影呈现的是国家梦,梦的主体为国家,是基于国家立场,而不是个人立场的想象。电影的中国梦也是理想之梦,梦的内容不是个人欲望的满足,而是个人梦想的升华,是超我之梦、集体之梦、国家之梦。而当下中国流行电影的梦幻机制和题材元素并不必然满足中国梦的要求,甚至存在严重的缺陷。“四大幻”(科幻、魔幻、奇幻、玄幻)走向猎奇、胡编乱造、感官刺激。喜剧走向低俗,以消费历史的方式制造笑料,依靠挑战角色的生理极限生成笑点。武侠电影鼓吹暴力,其塑造的形象不堪中国梦之英雄形象的重任。青春片热衷于展示商业时尚、青春狂欢、感官体验、情感创伤和性。中国电影要为梦幻机制的快乐原则中注入更多积极的价值,提升电影的思想、人文和美学品位,使中国电影在奔放不羁的梦幻想象里有更多对国家、现实、社会和人性的积极思考。
写作者和批评者的尊严亟待重建
霍俊明在2017年4月26日《文艺报》撰文指出,与当下诗歌的火爆、分化、裂变、多元和无序的状态形成极大反差的是无力的、失语的,甚至不作为的诗歌批评。诗歌批评深入当下、直指命脉、一语中的、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能力普遍偏弱,更多的批评者沉浸于碎片化的诗歌文本“咀嚼”和诗人个案的“表扬稿”。越来越多的几无标准和建设性可言的资本批评、媒体批评以及无节操的诗歌批评正在大行其道。时下的诗歌批评者不仅缺乏批评的勇气,处于无效的失语和不作为状态,而且还沦为了文化投机者和捡拾诗歌垃圾的人。人们忽略了资本和媒体环境形成的诗歌之“伪”和诗歌之“恶”。媒介话语一旦受到追捧成为一种主导性权力,这种媒介就不可能不偏不倚。资本和媒体塑造并规训了这个时代的诗歌生态,更多的人却是沉浸其中难以自拔。面对发达资本与媒介时代的诗歌“伪”“恶”以及批评的不作为,面对分化、分层的诗歌现状,亟待重建写作者和批评者的尊严。重新做一个诗人,重新做一个批评者。这既是美学的问题,历史的问题,也是紧迫的现实问题。
中国当代写意油画应注重其“书写性”
郑工在《艺术探索》2016年第4期撰文认为,对写意油画而言,强调“书写性”最大的作用就是激发自我意识,但没有放弃对象世界,而是强化艺术的个性,也没有让感性的形式完全蒸发,而陷入空洞的概念游戏。其最重要的特征是让抽象的形式出场,现场感十分重要,这就是当代中国的写意油画者们为什么热衷“写生”的原因。他们是让现实的存在于临场状态中敞开,同时也让自我的意识敞开,看到那些看不到的东西,因为他释放了形式对事物的压抑。书写是流动的,也是开放的,有着许多不确定性,包括方向上的不确定性。
艺术中的美是“有我”的美
杨振宁在2017年2月12日《光明日报》撰文指出,科学里蕴藏着美。正如物理学的发展要经过四个阶段,不同的步骤里都有美,美的性质不完全相同。物理学家通过一组方程式来了解宇宙结构。方程式“住在”我们所看见的一切一切里,它们非常复杂,有的很美妙,有的则不是那么美妙,还有的很不容易被人理解。但宇宙结构都受这些方程式的主宰。无论漫长的时间还是短短的一瞬,都受着这几个方程式控制。这是一种大美。这些方程式是造物者的诗篇。因为诗就是语言的精华。造物者用最浓缩的语言,掌握了世界万物包括人的结构、人的情感,世界上的一切都浓缩在“诗人”——造物者写下来的东西里浓缩起来了!其实这也是物理学家最后想达到的境界。然而,科学里终极的美是客观的,没有人类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些美了。可是没有人类就没有艺术,也就没有艺术中的美。换句话说,科学中的美是“无我”的美,艺术中的美是“有我”的美。所以说,科学中的美和艺术中的美是不同的。科学追求的是认识世界、理解造化,并从认识中窥见大美。而艺术创作的本质应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唐朝的画家张璪语)。既有“写实”的美,也有“写意”的美。但若是完全朝着背离造化的方向发展,就会与美渐行渐远。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最大问题是“作家缺席”
郜元宝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2期撰文指出,进入1990年代以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理论兴趣锐减,“文学理论”差不多成了架空的怪物。与之相关的“文学批评”处境更糟。过去习惯的批评模式是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的分析,即作家论、作品论、现象论。这些批评操作既缺乏原创的“理论”,更不具备上下几千年宏阔的历史视野,只是围着作家打转的抬轿子营生。于是,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三足鼎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变成了文学史研究一统江山。有意无意都要显示其“历史癖与考据癖”,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大势所趋。与其推崇陈寅恪的“诗史互证”,不如重新审视鲁迅对中国古代文学和新文学的论述,特别是《中国小说史略》《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等经典的文学史描述方式,即牢牢抓住作家主体为中介来考察社会政治、思想文化与文学演变的关系,改变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中“作家缺席”这一最大的问题,描绘有血有泪有笑的活的文学史。
今天的中国需要“深度启蒙”
阎国忠在《艺术百家》2016年第5期撰文指出,站在中国的角度思考当今中国美学问题,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现代启蒙教育仍是我们必须要讨论的主题。现代启蒙教育与西方的17至18世纪启蒙运动不同,与20世纪初在西方影响下形成的启蒙主义教育也不同,可以叫作“深度启蒙”。现代启蒙教育的着眼点不是个体,而是群体,是整个中华民族。它不仅是教育界、知识界的事,更是全民的事,本质上是人民群众的自我教育。现代启蒙教育是在马克思主义引导下进行的,不仅意味着个性的解放与个体的全面发展,而且意味着建立起人与世界、人与自然的合理的关系,将人的解放与世界的解放、自然的解放结合在一起。现代启蒙教育实质上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是社会主义的新人教育。显然,启蒙教育不仅是审美教育问题,但主要途径应该是审美教育。其他任何教育,比如政治、道德、宗教、文化教育都只是涉及人的精神生活的某一个方面,并且主要诉诸理性和群体,唯有审美教育涉及人的生命整体,既诉诸理性,也诉诸感性;既诉诸群体,也诉诸个体,是真正全面发展的教育。正因为这个原因,审美教育虽然是同样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却能够将其融入人的内在欲求和冲动中,成为人净化和完善自我的自觉行动。资本给人带来的创痛是全面的,审美教育是它的伴生物,同时也是它的对立面。
中国文艺术语彰显中华文明独特性
袁济喜在《甘肃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撰文指出,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思想史上,文艺术语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精华与奥秘所在。道、气、性、势、格、思、境、心物、意境、神韵、神思、意象、情志、格调、情景、趣味、境界、意在言外,这些充满着民族气派与风韵的术语、范畴、创成于当时,留存于当今,亘续于未来,早已超越专业范围,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血脉与中华思想文化的瑰宝。中国古代文艺术语从结构来说,是从天地人三者关系中衍生出来的产物,它与一级术语与范畴既有关联,又有区分。有的术语是与哲学、史学所通用的,可以将其视为一级术语,比如道、性、气、文、质、和、情、心、意、风、清、自然、雅、命、素、悟、真、善、美、味等,这些术语出现在文艺学经典,我们不能人为地将这些通约与通用性的术语画地为牢,列入某个学术与学科的专属领域,这样做显然是不符合中国思想文化术语基本事实的。另一种是属于二级术语范畴文艺术语的,一般为组合型术语,如文道、文笔、文气、文采、文华、文质、意象、意境、情景、物境、气韵、气象、兴象、兴寄、兴味、兴趣、传神、神韵、韵味、滋味、畅神、妙悟、神思、风骨、清朗、逸品、气象、气骨、雅俗、风雅、风教、野逸、涵泳、闲远、温柔敦厚等等。此外,还有鲜明的描述性与形象性,以命题方式表述的文艺术语。中华思想文化中的文艺术语,可以洞悉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意绪,从而了解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直接表达出我们这个民族的思维方式与性格特征。
当今书坛呼唤“得意之作”
郑荣明在2017年5月17日《中国艺术报》撰文指出,当下在“展览”模式下出现的创作,有三个明显的特征,即模仿复制性、形式制作性、书写技术性。从表面看,书写的“训练”系统更为完善和更为有效,“书法家”的产生也形成了类于“流水线生产”的简捷,这就出现了目前很“直观”的一种热闹和繁荣。但只要稍有书史概念和审美意识就能够辨析,这是一种很虚假的“繁荣” 。创作者的“得意”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快感” 、一种自我满足的“生产”刺激,这与古人所谓的“得意忘象”有天壤之别。而真正的识者肯定是不屑的,更遑论会有艺术及审美上的价值评估和判断,因为这些根本谈不上“意境”的构建,更谈不上美学上的妙思和风格上的营造。学界对当今书坛越来越重的“文化缺失”的忧虑,其根即在于此。循此而论,我们呼唤“得意之作” ,一是书法的创作者要增强“书史”意识。我们必须厘清什么才是书法的“经典” ,必须辨识书法传承的核心价值和审美范畴,必须体察古代书法家“得意”何在,做一个明明白白的创作人;二是整个书法界要构建书法审美、书法风格的钩沉、研究氛围,特别要引导纯粹的创作者关注书法的文化品格和艺术品质的塑造。
(责任编辑:陶璐)
⋆本刊转载部分文章的稿酬已按法律规定交由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转付,敬请作者与该协会联系领取。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珠市口西大街120号太丰惠中大厦1027-1036室,邮编:100050,电话:010-65978917,传真:010-65978926,E-mail: wenzhuxie@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