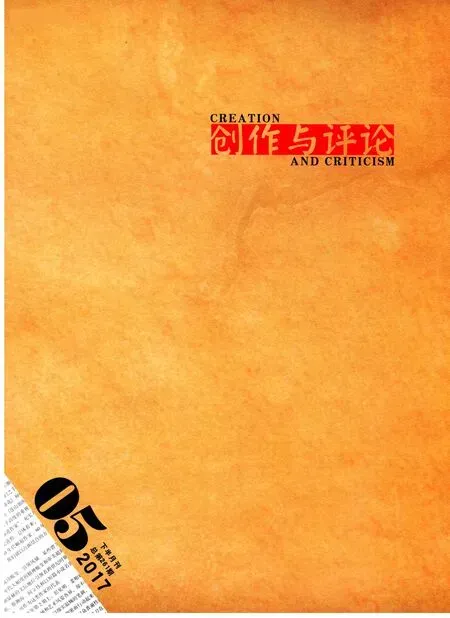『80后』文学的创作实绩及症候探析
2017-11-13徐勇
○徐勇
『80后』文学的创作实绩及症候探析
○徐勇
一
今天,当我们使用“80后”文学这一概念的时候,往往需要加以严格限定,否则便可能失去其概念范畴的有效性与阐释力。因为,“80后”作家的分化已经十分明显,不像十数年前,“80后”几可等同于“青春文学”作家,主要是由新概念一批作家构成,在这之后,随着很多非新概念“80后”作家的崛起,“80后”越来越呈现出双峰并峙的局面。后者是通过传统期刊渠道成长起来的一批“80后”作家,与通过媒体制造的“80后”明星作家风格明显不同。
但是,近几年来,情况又有大变。虽然“80后”作家仍旧可以大致分为两类群体,但“80后”作家的创作却呈现出趋同的倾向,“80后”作家也越来越走向成熟。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新概念“80后”作家的“去青春化”倾向。或许,这与“青年文学”的接力棒被媒体转让给更年轻的“90后”有关,或许也因为“80后”一代已并不太年轻,青春正逐渐离他们而去。在前几年,这一“去青春化”倾向,还主要体现在个别作家身上,比如说蒋峰,虽新概念出身,但他的创作始终与新概念“80后”主流保持一致,近期创作出版的长篇《白色流淌一片》更是显示出“80后”文学应有的高度和成熟。另外,像张怡微的创作,也常常在青春和“去青春”之间徘徊,其早期创作,带有明显的青春时尚的余韵,但自从创作《你所不知道的夜晚》(2012) 和《细民盛宴》(2015)以来,张怡微离青春文学越来越远。就新概念“80后”作家的“去青春”倾向而言,今年发表的张悦然的长篇《茧》(《收获》2016年第2期)是一个标志和象征。这部新作虽然在形式上同她此前的作品并没有太大的变化,都是采取混合视角。混合视角是“80后”青春文学惯常采用的视角,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之为“80后”文学的标志。虽然说,这仍是在表现创伤与成长的主题,但在作品中,作者不再在一种静止式的时空中展现其青春忧伤与感叹,而是把故事内容转向具体历史语境(而非像《誓鸟》和《红鞋》以及《葵花走失在1890》那样在一种虚化的历史背景下展开叙事) 之中,显示出“80后”作家(不限于“80后”新概念一族)少有的历史感和历史担当,实在让人惊叹。在这之前,曾有张怡微的《你所不知道的夜晚》和颜歌《我们家》,也都是试图在历史的背景下表现家族成员的兴衰,但因为两部作品都并不突出成长主题,它们虽有“去青春化”倾向,但并不具有代表性。张悦然是“青春文学”的代表作家,她这部作品以具体历史背景表现成长主题,某种程度上可以看成是对此前“80后”新概念作家成长写作的某种颠覆和突破。从这个角度看,《茧》的出现,标志着“80后”新概念一族的“去青春化”从自发到自觉的转变。此外,还有李晁的《迷宫中的少女》和王若虚《火锅杀》等,也可以放在这一脉络中加以考察。与这一“去青春化”相呼应的,则是“80后”新概念作家的分化,像郭敬明向影视导演转型,张悦然进入高校讲堂,马小淘、李晁、陈崇正等加以各地作协或文联主办下的传统文学期刊编辑部(这些编辑在以前主要是由传统作家构成),而颜歌、张怡微、霍艳等则作为文学博士的身份出现,这样一种分化,其带来的必定是“80后”新概念作家内部的分化,及其向传统作家身份靠拢,“青春文学”作家的标签日渐不显。
应该说,向传统文学或文学传统的靠拢,表明的是“80后”青春作家历史感和文学史意识的增强。就像艾略特所说的,传统“它涉及一种历史感……这种历史感迫使一个人不但用铭刻在心的他们那一代人的感觉去写作,而且他还会感到自荷马以来的整个欧洲文学以及处于这个整体之中的他自己国家的文学同时存在,组成了一个共存的秩序……就是这种意识使一位作家成为传统的。与此同时,它使得一位作家敏锐地意识到他在时间中,在同时代诗人中的位置”。对“80后”作家来说,只有成为传统的一部分,才能显示其“共存的秩序”的文学史价值。此前,因为媒体制造的倾向,他们大都采用时尚文体和残酷青春的写作,类型化和自我重复比较突出,文学史意识淡薄。类型化写作是与(后)工业时代的文化产业联系一起的,它是一种以某些所谓的抽象模式或要素(如永恒的青春主题)等共时性元素为其存在形态的文化产品,因此,反历史和“灵韵”的缺失,是其显著特征。类型化写作曾造成“80后”青春文学的个体性严重不足,诸如七堇年的《被窝是青春的坟墓》《尘曲》,颜歌的《马尔马拉的璎朵》《良辰》和《桃乐镇的春天》,以及张悦然的《十爱》,马小淘的《火星女孩的地球经历》,张怡微的《青春禁忌游戏》《怅然年华》等等这些作品,只要抹去作者的名字,彼此看不出有什么区别。可以肯定,“80后”青春作家文学史意识的增强,与他们的年龄的渐长、(创作和生活)经验的积累日厚和创作存在方式的改变有一定的关系。相比之下,那些靠传统期刊成长起来的“80后”作家则各个风格鲜明,甫一出场即表现不俗。
文学史意识的增强,某种程度表明了“80后”文学的成熟。其标志就是出现了一大批风格鲜明的“80后”代表作家,诸如蒋峰、孙频、甫跃辉、双雪涛、张悦然、颜歌、笛安、李晁、文珍、春树、郑小驴、马小淘、马金莲、蔡东、朱个等等。与此相对应的是,还出现了一批代表“80后”文学创作成就的中长篇代表作,长篇代表作有蒋峰的《白色流淌一片》、颜歌的《我们家》、李晁的《迷宫中的少女》(小长篇) 和张怡微的《你所不知道的夜晚》(小长篇)等。中短篇更是灿若星辰,如王威廉的《非法入住》、双雪涛的《跛人》、笛安的《光辉岁月》、甫跃辉的《秘境花园》(也叫《弯曲的影子》)、文珍的《第八日》、孙频的《同体》、马小淘《毛坯夫妻》等等。“80后”文学开始真正进入到文学史“共存的秩序”中,而不仅仅是时尚文学的代名词。
二
虽然可以肯定“80后”文学已经真正登上历史舞台,但仍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有些问题的重视与否及其能否解决,某种程度上甚至能决定“80后”文学创作到底可以走多远。
题材和主题仍旧是困扰“80后”作家的主要问题。即使是像张悦然的《茧》这样的寻求自我突破之作,其仍旧是在成长主题上缠绕,更不用说像王若虚的《火锅杀》,虽然在题材上有让人瞩目之处,但其实是把社会上的黑帮故事放在大学校园的背景中展现。这两部作品,某种程度上代表了“80后”的努力的方向和限制所在。当他们在题材上试图创新时,如张怡微的《细民盛宴》、杨则纬的《于是去旅行》,主题却自觉不自觉地回到他们所惯常的创伤书写或成长之痛上来。反之,当他们想在主题上有所开掘时,题材却仍旧显得陈旧,如双雪涛的《聋哑时代》、李晁的《迷宫中的少女》。而即使是像王威廉的《获救者》那样,试图从题材和主题两个方面进行突破时,却又陷入了主题的现代主义探索与题材的奇观化效果的奇怪耦合中,小说中先锋与通俗的结合,与我们通常所见的好莱坞电影模式颇为相似。这样一种二律背反表明,经验问题仍旧是限制“80后”作家的重要方面。比如说张怡微,她的小说,总是围绕家族或从家族入手,写人情冷暖和世态炎凉,虽写得触目惊心或细致入微,但总感觉似曾相识。一直以来,他们太过看重自己的经验,不断挖掘,难免会有枯竭或自我重复之处。要么是避实向虚,其走向极端就是幻想文学,如郭敬明的《幻城》和双雪涛的《翅鬼》,或者像张悦然、颜歌那样向抽去具体时空的历史索取,如《誓鸟》和《关河》,简直成了架空之作。或是寓言写作,如颜歌的《异兽志》。在这两者之间,做得较好的有双雪涛的《天吾手记》(发表前,也叫《融城记》,曾入围第十四届台北文学奖年金奖),虽然带有穿越小说的痕迹,但其试图在形式的创新和哲学层面多方探索,让人耳目一新。
题材和经验问题的自我重复背后,是第一人称主观视角和混合视角的普遍使用。“80后”作家普遍青睐第一人称主观视角,这一倾向还带来另一副产品——混合视角——的出现。所谓混合视角,是指第一人称主观视角和第三人称限制视角的混合(而非结合)。表面看来,小说的叙事是由一个个不同的第三人称限制视角的叙述构成,但其实是第一人称主观视角的变体。其最为典型的是笛安的“龙城三部曲”,三部小说(《西决》《东霓》和《南音》) 分别由西决、东霓和南音三个视角分别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讲述的故事构成。三部小说其实就是三个人分别以自己的视角讲述的故事,他们的讲述构成同一个整体的故事(同一个家族的故事)的不同侧面,只是讲述的角度不同,因而呈现不同的面目。混合视角的使用,在“80后”作家比较普遍,颜歌的《关河》(长篇),张怡微的《下一站,西单》(长篇),以及笛安的“龙城三部曲”和《告别天堂》等,是其代表。张悦然的新作《茧》,也是此例。对于混合视角来说,其困难在于,虽然在整体上小说叙述主观色彩很浓,但因为小说采用不同的第三人称限制视角,不同第三人称限制视角的叙述必须(或原则上应该)个性鲜明,而不能彼此类同或相似。在这方面,很多“80后”作家往往不太注意,以至于虽视角人物不同,但整体叙事风格前后一贯,有多人一面的感觉。笛安的“龙城三部曲”和《告别天堂》是其典型。
混合视角的使用,表面看来是在使用多重视角,但其实仍是第一人称主观视角的变体,主观抒情色彩很强。换言之,这其实仍是一种倾诉文体,是独语体,而非复调。同一个故事或同一件事,被不同的叙述者从不同角度呈现和讲述,虽能造成叙事上的繁复的效果,和云遮雾罩的印象,但其实表现出的是对已有经验的过度倚重和不断挖掘。某种程度上,这种独语体,反映的是叙述者/作者或主人公的孤独而封闭的内心,他们不愿把视角向外伸展,故而往往倾力或聚焦于个人经验的各种讲述的实验当中。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混合视角的使用,就小说文体而言,它还是一种中篇小说串珠的做法,合起来看虽像长篇,但其实更像一个个中短篇。因此,就长篇小说的结构而言,它其实并不严谨,有时显得十分松散。这一点,在张悦然的新作《茧》中仍表现明显,而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决定了“80后”作家在整体上都不太擅长长篇小说创作。
三
如果说经验问题仍旧是限制“80后”作家文学创作的重要症结所在的话,这正好可以解释“80后”文学创作整体上的另一矛盾现象——即有代表作家,没有(长篇)代表作品——的产生。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首先,因为媒体的宣传和介入,造就了“80后”“新概念”一族代表作家,如韩寒、郭敬明、张悦然、蒋峰、颜歌、七堇年、王若虚等等,他们名气很大。但因他们走的是传统作家之外的另一条路,可以不经过传统期刊发表这一环节而出版长篇小说,凭借市场和时尚主题/题材——倾向于成长之痛或残酷青春之类的主题——的持续生产而生存,他们的作品类型化现象比较突出,就此而论,新概念制造出一批代表作家,但无代表作品出现。其次,与之相反但又相似的是,新概念之外的“80后”作家这几年虽有大幅度的涌现,但因为第一,他们出道较“新概念”一族要晚,而大都依靠传统期刊和文学出版,这就决定了他们整体上偏向于中短篇小说创作,而不太擅长长篇。这是一种先发表后出版(在今天逐渐演变为时间上同步的形式)的文学生产机制,与“新概念”一族可以跨过发表的文学生产机制明显不同。传统文学期刊中,发表长篇小说的本已不多(坚持定期发表长篇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家,诸如《收获》《当代》等,而像《人民文学》《花城》《钟山》《大家》等刊物,只是不定期地发表长篇,有些则主要是发表中短作品,如《十月》《上海文学》《山花》《西湖》《天涯》等),如此有限的篇幅常常倾向于留给长篇写作经验丰富的前辈作家。在这当中,《收获》有过几次集中篇幅刊发以“80后”为主体的青年作家专辑,但在主打的每期长篇栏目中,却很少留给“80后”(张悦然的《茧》发表在今年第2期),只是在每年的两期长篇小说专号中,会有“80后”作家的面影浮现(如笛安的《南方有令秧》、七堇年的《平生欢》和王若虚的《火锅杀》)。这样一种机制,决定了“80后”大都是从中短小说起步,他们这方面用力很大,涌现了一批相当擅长于中短篇小说的作家,比如说甫跃辉、孙频、双雪涛、王威廉、李晁、朱个等等都是。只是近几年来,政府与国家资助力度加大,加之各种基金会(如中华文学基金会)和民间资本积极介入,非营利性文学资助成为当前纯文学生产的一种重要的补充方式和传播方式。这一背景下,出版了一些“80后”作家的长篇作品(更多的时候是出版中短篇小说集,如《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但因为这些作品多是作家的长篇处女作,并不太成功,比如甫跃辉的《刻舟记》、曹永的《无主之地》、杨则纬的《我只有北方和你》(非处女作),甚至孙频的《绣楼上的女人》等等。第二,或许也因为受制于已有的、有限的、贫乏的经验。相比较而言,“80后”一代人整体上要较他们的前辈在经验上要贫乏单一得多,他们生活在一个物质相对丰富的年代,少有生活的磨难和波折。这就决定了在篇幅容量上,相对贫乏的经验与经历比较适合于中短篇。他们聚焦于已有的经验,用心往下,是空间上的深挖掘;相比之下,在纵向上或历史时段的把握上则用力不够。有些作品,虽试图从纵向的角度展开,但很大程度上仍然可以看成是中短篇小说的结集,最为典型的莫过于双雪涛的《聋哑时代》。
这也决定了“80后”作家(包括新概念一族)长篇小说的一个普遍特点,即虽看似长篇,其实为短制。这一情况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小说各部分之间,似断似连,很多时候并没有连贯的故事主线。叙事随意而线索多线交叉展开是“80后”作家们喜欢采用的结构方式。《聋哑时代》自不必说,颜歌的《异兽志》和《声音乐团》,蒋峰的《恋爱宝典》、张怡微的《下一站,西单》,张悦然的《誓鸟》,以及《茧》,都是如此。这与他们喜欢采用的混合视角有一定的关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样一种体制就一定不好,因为像蒋峰的《白色流淌一片》就堪称当代文学中的精品,虽然其也是由多个中篇连贯而成。这里的区别在于部分与部分之间的关系。如果部分与部分之间,只是视角上的转换,或故事的多个侧面,而无内在的整一的气脉,这样的长篇只不过是中短篇的集锦。相反,对于那些长篇,各个部分之间,表面看起来往往只有人物关系的联系,既没有一以贯之的故事,也没有贯穿始终的主要矛盾或线索,但各个部分之间有其内在的风格上的一致性或笼罩整部小说的格调、氛围上的相互渲染,这样的长篇,虽看似中短篇的随意集合,但其实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比如说奈保尔的《米格尔街》,和艾伟的《整个宇宙在和我说话》,就是这样的范例。另外,缺少节制和主观色彩强烈也是部分“80后”作家的长篇看似长篇,其实只是中篇的扩展和膨胀的结果。缺少节制和主观性较强其实是一体两面,表现在小说中就是倾向于倾诉。这在杨则纬的小说中表现最为集中,诸如《我只有北方和你》《最北》,甚至发表于2015年的《于是去旅行》,都是如此。另外像笛安的《龙城三部曲》、张悦然的《茧》等,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种情况。
四
可见,对于很多“80后”作家来说,普遍存在这样一种矛盾现象,他们往往注意形式上的创新,甚至也刻意营造结构(最典型的是颜歌的《声音乐团》和蒋峰的《恋爱宝典》),但很多时候只是为了形式而形式,并不能掩盖经验上的不足,相反,倒常常显示出对叙事及其技巧的忽略。可以肯定,某种程度上,在他们那里,混合视角的使用,并不是为了叙事上的创新,而毋宁说是为了倾诉的方便。不同视角的转换,只是为了更加方便倾诉和不受第三人称限制视角的限制。这一点在张悦然的近作《茧》中仍表现明显。他们的作品可以写得非常有(内心的)深度(像孙频、张怡微、李晁),有(时代的) 力度(像甫跃辉、双雪涛、马小淘),或者(历史的)厚度(像张悦然的《茧》),甚至也可以很有思想(如王威廉),但却往往只是在某个点上用力,比如孙频擅长对主人公的那种具有创伤的内心矛盾的挖掘,张怡微善于对人情冷暖的体察和把握,甫跃辉和文珍则敏感于全球化大都市中青年男女主人公的内心困惑、焦虑与不安,朱个则喜欢把主人公置于一个虚化具体时空背景的小镇,杨则纬倾向于聚焦于成长过程中的个人的多愁善感,等等,一旦脱离了某个点,“80后”作家们就会感到迷茫,或踟蹰不前。某种程度上,“80后”作家不擅长或不太用力于长篇小说的创作,正与此有关。他们在某个点上用力,攻击其一,不及其余,很多方面往往就会被忽略。但另一方面,这也表明或意味着作家们各自风格的形成和创作的成熟,他们扬长避短,或者说找到了自己的兴趣点,不断推进。这恰恰就是所谓的辩证法。一个作家,仅仅囿于自己的风格,而不能不断超越自己或自我创新,这样的风格成形或成熟从另一个角度看又何尝不是自我桎梏?
对于“80后”作家而言,这种困境的出现不仅仅是因为历史感的贫弱,甚至也不是创新意识的不足,这些都不是。某种程度上,宏大叙事的阙如是造成“80后”文学难以飞升的重要原因。这当然不是要“80后”作家重拾前辈作家们的宏大叙事的余唾,也不是要他们重建另一套宏大叙事,而只是想指出,当他们在放逐或回避宏大叙事的时候,其实是把宏大叙事作为一套观察和思考问题的角度与方法也一同抛弃了。他们的前辈,如新写实诸代表作家,在书写日常生活的平庸与琐碎时,其实是有宏大叙事作为背景的,不管这一背景是以反讽的姿态或是作为远景出现。也就是说,他们虽反对宏大叙事,自顾自地建构了一套日常生活的书写形态,但宏大叙事作为一种视角、一道目光,却是贯穿始终的。他们越是反对宏大叙事,越是表明宏大叙事的不可磨灭与不可化约;这从方方的小说创作的轨迹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她的《风景》《白雾》《白驹》系列最为典型地表现这一辩证法。但对于“80后”作家们,他们的作品却是一种宏大叙事普遍缺席的真空状态:他们的小说要么时空模糊(如张悦然、颜歌、七堇年、朱个),要么沉溺于全球化的悖论情境中,以一种消费主义的文化形态或身份认同的混杂等多重形式显现。这使他们的创作在整体上呈现为一种碎片化的、零散的状态,这是那种本雅明意义上的瓶子打碎后还没有“重新粘合”的中间状态,他们仅仅专注于瓶子被打碎后的碎片般的存在,既不关心或询问其碎片化的前身、瓶子的有无,也无意于把它们粘合完整。某种程度上,这是造成他们的作品(包括很多长篇)从总体上看很多都是中短篇小说的重要原因,也是他们为什么写不好或回避长篇的重要原因。因此,对于“80后”作家而言,他们需要重建的,是作为方法和视角的宏大叙事,是隐藏在宏大叙事背后的永恒的乌托邦冲动的“记忆”和“回声”,是卢卡奇意义上的“先验世界结构的总体性”坍塌后对“隐藏着的生活总体性”的重建。从这个意义上说,“80后”文学还是一种中间状态的文学;因此不难(或不妨)得出结论,就整体走向及创作实践来看,“80后”作家们并不缺技巧,甚至也不缺经验,他们缺乏的是引渡他们的“涉渡之舟”,虽然这一彼岸并不总是存在。
注释:
①T.S.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塞尔登编:《文学批评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11页。
②参见谢有顺:《让更多的青年作家发声》,李德南:《遍地伤花》(总序),河南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2页。
③本雅明:《译作者的任务》,《启迪》,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90页。
④卢卡奇:《小说理论》,《卢卡奇早期文选》,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6页。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 马新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