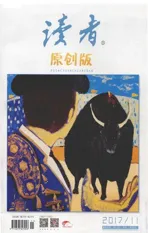绣花的爹娘
2017-11-13文|虹珊
文|虹 珊
绣花的爹娘
文|虹 珊
以为他们会吃不香睡不稳,会觉得孤单寂寞,会衣带渐宽,但这些令人担心的现象并没有出现,除了偶尔的情景联想,竞猜一下他们曾经生活了70多年的村庄之现状,两个古稀老人似乎都是祥和甚至愉快的。
两年前,他们坐在大包小包的生活物品中间,被我们运到了新的村庄。新村庄距离我居住的城市不足20公里,人烟稠密,水草丰美,田园广袤,不仅有人工渠傍村而过,而且出门不足50步,便能与小溪相遇,与位于深山老林且吃水艰难的老家相比,实在好太多了。这里是苏浙水乡。
两个人对新村庄啧啧称赞,但我们对老家的挑剔也招致了他们的严重不满。父亲说:“任何时候,人都不能忘本,老家再不好,也养育了你们十几年。”母亲什么都不说,但手里的活,全都是依着老家的规矩打理:柴火灶炒菜,柴火炉煮饭,开水用铜壶慢慢烧开,洗碗用食用碱缓缓浸泡,做豆腐用石磨细细地研,炒花生用河沙柔柔地焙。那些亮锃锃的电器,我们刚拎回去时,母亲会真心实意地观赏一番,但之后就毫不客气地将它们打入冷宫。
种地也是。先要用锄头除尽杂草,接着将每个土疙瘩逐一粉碎,把地精心梳上好几遍,然后再直直地起垄,一行行撒上沤好的粪,最后才撒种。新村庄的人觉得惊讶,每每经过,总要停下来看两个老人劳作,离开时,免不了要诚恳地奉劝他们说:“化肥、农药、除草剂这三件宝,一下子就能把地管好,你们都这么大年纪了,还把种地当绣花,何苦呢?”新村庄的人也很热心,有人将拖拉机、收割机“突突突”开到他们面前说:“用我的机器吧,多省事。”两个人却一律笑呵呵地谢绝了。
养鸡更是。在新村庄,在我们的强烈反对下,他们终于不再养猪了,但养鸡却是必需的。每天清晨,他们都要将萝卜、白菜、红薯、南瓜藤剁得碎碎的,掺上玉米面煮熟,再撒上少量的沙子,拌匀后倒进鸡槽。下午,他们会将许多鲜嫩的草整筐整筐地倒进鸡舍里,让鸡们尽情地扒拉啄食。当然,仅止于温饱显然是不够的,隔三岔五,父亲还会把他的二胡拿到院子里,悠悠然拉上一阵,让鸡群充分享受乡村音乐。在如此这般的照料下,15只鸡只要一看见他们,就会从鸡舍的各个方向撒开翅膀,争先恐后地向他们奔来,一只只都自信美丽得像花孔雀。
逢节团聚,家里的几个孙辈总要亦步亦趋地跟在他们身后,看他们琐琐碎碎地忙,可终究没看出头绪来,不就是喂鸡吗,为什么还要扔草、拌沙、拉二胡呢?父亲得意地说:“草里有虫,虫子可以提供蛋白质;掺沙嘛,是为了让鸡蛋更结实;至于拉二胡嘛,自然是为了让鸡娃们更高兴,高兴了就会下更多的蛋。”母亲接口道:“这样你们才能吃到最好的……”还没说完,她就赶紧掩了口,但我们每一个人,都听懂了她隐下的那些话。
相聚匆匆,很快我们就开始陆续返城。两个老人把平时积攒的纸盒和包装袋全部拿出来,给我们分装豆腐、青菜、土豆、鸡蛋、糍粑等各种各样的自产食品。我们说吃不了这么多,别装了,可他们倔强得像木头,恨不得把整栋房子都塞给我们。临走前,趁着天黑,我悄悄把鸡蛋放回厨房,要知道,已经谢了窝的那群鸡,无论怎么精心喂养,一天最多也只能捡回一个蛋。可是没容我走多远,他们的电话就追来了,只好返回。母亲说:“傻囡,我们到这里来住,不就是为了方便你们拿东西?你们这不要那不要的,我们不是白搬家了?”她依然掩着口,但还是坚持把话说完了。不久前,她右边的一颗牙脱落,她以为难看,不免羞涩,所以每次说话,总要拿手遮挡。
除了接受,我没有别的选择。正在目送我们的那两位老人,为了让儿女享受到世间的美,他们倾尽一生,把土地当花绣,把日子当花绣,把生活里的每个细节都当花绣着。可是,一年又一年,每当从包裹我的温暖岁月中醒来,我都会看见,他们的目光又暗了一寸,牙又掉了一颗,发又白了一缕。
在他们的注视下,我却一点儿也不敢回头,只能顺着时间的方向,带着他们用心与魂绣出的花朵,往前走,再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