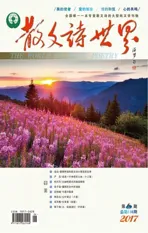燕子也是拆迁户(六章)
2017-11-13安徽潘志远
安徽 潘志远
燕子也是拆迁户(六章)
一网收复世界
几乎所有的网,都是关系网,蛛网也不例外。
与法网沾边,不存在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对蛛网而言,城市是它最大的遗漏。
以乡村为依托,蛛网一直坚持它的民间立场:几根树枝,一角屋檐,一扇破窗,便已足够结网。
从不主动捕捞,收获再多,也与贪婪无关。
在一隅,静静张网以待;是谁昏了头,瞎了眼,或者急急逃窜,不看前路。
触网:是落叶,暂且当沙发打盹,做一个白日梦;是露珠,暂且当明珠,一颗即将被太阳没收的夜明珠。
小虫触网,也可以当一顿美餐,倘若我正饥饿。
那个在枝头,总是高喊“知了”,自命不凡的家伙——我结网的目的,一大半是针对你,粘住你的翅翼,让你触网时有一刹那的后悔,从此变得谦虚,且接受教训。
安徽 潘志远
更多时,网被你撞破,没关系,我会慢慢修复。
居网思考,一切都变得简单。我在网内,世界在网外,我与世界仅一网之隔。
有蛛网,一切都变得轻松。我一网收复自己,也收复世界。
漏网之鱼的感恩
我是一尾漏网之鱼。不是网破了,使我有机可乘。
也不是网眼太大,看不上我的瘦小。
我怀疑是网起了怜悯之心,故意对我卖一个破绽。或者悄悄提了一下,我才得以从网的胯下钻过。
总之,是网对我网开一面。我成为一尾漏网之鱼,急急逃生,惶惶逃生。
逃生后,却高兴不起来,只为网对我网开一面。那是多大的恩情,这一辈子我将无法偿还。我心难安,为此我快患上抑郁之症。
那是网一生中最大的舞弊、最大的过错。轻易放生一尾鱼,网一生也无法弥补。
我想说出我的感激,可我的嗓子早已喑哑。
我嗫嚅着嘴唇,想借水、借一条河传导我发自心底的感恩,却一次次被人视为泡影。
我快乐地活着,就是我对网最好的报答。
在下一次落网前,在刀架脖子上,在被掏心摘肺时,我遍体鳞伤。
油锅里最后一跳:不是我的垂死挣扎,是我使出最后的力气,表达网对我网开一面的愧疚之情。
燕子也是拆迁户
道路拓宽,赶上了。说行大运,倒霉,都已不在话下。
老屋行将拆迁,十头牛也拉不回。
条件谈妥,理赔到位。挖掘机轰鸣,张牙舞爪:摘除门窗,猛捣老屋后背,最后一个泰山压顶——老屋坍塌,拆迁队员们满意而归。
只是苦了梁上燕子,它们的旧巢倾覆,顿时化为齑粉。
好在卵已孵化,梁间燕子初长成,刚随父母飞到野外觅食。
拆迁是白昼商定的,绝对的阳谋,没有一点黑幕。但燕子不在家,也没有谁告知燕子拆迁日期。
燕子不知道它们的巢穴将毁于一旦。它们将餐风露宿,没有丝毫思想准备。
燕子也是拆迁户,没有赔偿,也该给个说法;
或者提前打个招呼,留一点空间,让它们寄居到他人檐下,另谋高就。倘若撞上大户人家,雕梁画栋,也算是它们前世的造化。
燕子在老屋的废墟上盘旋,去意彷徨。五里一徘徊,呢喃,吴侬软语:不适合表达愤怒。
一阵牢骚,一阵埋怨,一阵叹息,在风中若有若无……
三只江鸥
三只江鸥,将自己打开,
像三张膏药贴在风中,谁也无法撕去。
月亮发炎,一夜夜肿大。三张移动的空白膏药,在岸边缩小,固定成一团,
收敛了一条河的历史。我的目光诊断,为一座城市把脉。
病,或不病,我说不清,会被当成庸医、江湖骗子。
说得清,也没人相信。或者有人会找我麻烦。
江鸥又一次将自己打开,贴向夜的肚脐。
水边路灯发光,一块块坏死的肌肤。黄的,像一个疮,熟了,正在通头……
手术刀已经生锈。我低头再河堤上寻觅车前子的踪影。久远的乡下秘方,只是尚缺一口仙气,或那个人的一口唾沫。
一块修行千百年的石头
这块石头真是一块石头。
多么呆,多么傻,多么悠闲,多么大智若愚!
被人踩了也不吭一声,踢了也不抱怨。
看见悬崖下有人,也不偏一下,直直砸下去,正中一颗脑袋。把人砸伤了也不知道喊救护车,没有一点怜悯,典型的铁石心肠。
一块石头闯了大祸,却让人自己买单。证据确凿,也无法量刑审判。
一块石头就要砸下来了!请抬头,请躲闪。
一块石头悬在头顶,多么沉默,多么隐形,多么与世无争。何时滚动,不可知;何时砸下来,难以预测。砸中不该砸中的脑袋,是它的罪孽;砸中该砸中的脑袋,是它的造化。
它修行了千百年,在尚未风化之前,终于砸中了目标。
掷地有声。
小草折服,俯下一片。
泥土配合,给它一个笑窝。
血赏脸,为它开
万点桃花。
藕有所得
当一枚荷钱摆上水面,它要买下一池清波,甚至水底蓝天,还有你的倩影。
我真佩服它的气魄,或者天真。
一枚荷钱,仅一枚荷钱,就敢出手。
如果它就止于这一枚荷钱,与池塘,与蓝天,与你对峙,决不妥协,该多好!
可它开始掏第二枚了,接着掏第三枚,一枚一枚排满池塘。
满眼贬值的荷钱啊,终于只换来一把把碧伞,一件件青色的裙裾。
伞遮雨,裙裾当风,买荷一笑。
当霜收拾完枯荷的残骸,清水之下,淤泥之中,有人挖掘
藕有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