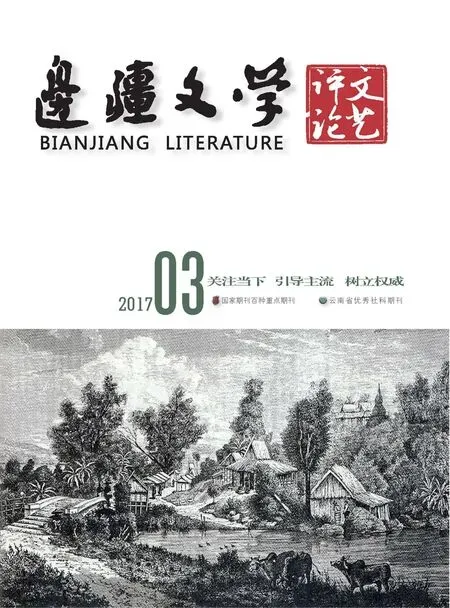捍卫诗的纯洁和历史(访谈录)
2017-11-13周良沛
边疆文学(文艺评论) 2017年3期
周良沛 蔡 毅
捍卫诗的纯洁和历史(访谈录)
周良沛 蔡 毅
被采访人:
周良沛采 访 人:
蔡 毅访谈时间:
2017年1月3日下午地 点:
周良沛先生家中蔡 毅:
周老师您好!您是我国著名的诗人、诗评家、诗选家和编辑家,长期以来活跃驰骋于中国文坛和海外文坛,写作出版和编辑了大量作品,令我敬佩叹服。今天就专门来与您谈谈您的创作与评论。周良沛:
不用客气,欢迎聊聊。蔡 毅:
周老师,您从事文学至今,一共出了多少本书?周良沛:
我出版的书有三十多本,其中诗集七八本,散文四五本,评论三本,余下就是杂文、回忆录、长篇传记等。我编的书,大概有二百多部,有“五四”后诗家的诗选集、全集,有《中国新诗库》《旧版书系》《云南文学丛书》《抗战诗钞》《中国新诗百年选读》等。式(2)中第一项为顺时针光束的一次环行,Sagnac相移是φR/2,φ是Y波导上/下分支尾纤输出的平行线偏振光的初始相位,偏置相位是-π/4;第二项为二次环行,Sagnac相移是φR,偏置相位也是-π/4;第三项为三次环行,Sagnac相移是3φR/2,偏置相位是零,所以三次环行对解调输出无影响.同理,由式(3)(4)(5)可知,一次环行影响5、7时隙的解调输出,三次环行影响6、8时隙.
蔡 毅:
用著作等身,编书无数来形容您的成果一点都不为过。光您编辑出版的书其数量就远远超越许多专门的编辑家,甚至一个编辑室。您一生为之倾注的心血和巨大的劳动量让人感动和望尘莫及。周良沛
:咱们不说这些客气话。我和科班出身的许多人不同,我没有学问,没学过什么理论,谈不上什么学术观点,完全是个门外汉。我只读过小学,进过中学门,正在内战内乱,学校很少开课,从来不知道混文凭是个什么味道。抗日战争期间,曾随流亡学校四处流亡,后寄寓于教堂的孤儿之中,从小受过西方文化影响。一九四九年底,十六岁时进入解放军,随横渡长江的大军南下,以后戍边服役、认真自学。十九岁后在军外报刊发表作品、出书。随之从连队进入文化部门,渐渐又干起为人做嫁家、终生相守的编辑劳动,长期担任《诗刊》编委;香港《海岸线》执行编委。我读的是最丰富、深刻的人生大学。虽然至今仍在创作、选编,没一点空闲,忙忙碌碌,也庸庸碌碌。蔡 毅:
周老师您好像曾被打为“右派”,吃过不少苦?周良沛:
我从1958年至1979年,劳改了二十一年,1978年最后从劳改队直接调到北京,才结束了苦难生涯,回归正常生活。有人说我是个奇人,为什么会对新诗了解那么多情况,编辑出版了那么些作品。其实,我就是个左派,送进劳改队,我也不停地为强加给我的“右派”帽子翻案,为此,在劳改中始终视为“反改造的人”。十年动乱“砸烂公检法”时,因为大街上的大字报有1955年方纪将我调到天津作为“包庇右派”一事在揭发。为此,我在劳改队又与文艺黑线挂上了钩,在劳改的大监又关进了小监。那时,昆明抄家的书没处堆放,就转移到劳改队。劳改队也没有那多“小号子”,我就睡在从城里转移来的书堆上,改成“小号子”的闲屋,用木条钉死了门窗,我就从木条间的空隙所透进的光线读书。那时年轻,视力好,记忆好,除了平日劳改队也鼓励读的马列和鲁迅,这回又读到大量抄来的各种书籍,包括一些视为的“禁书”。我过去在教堂时就什么书都读,现在有这样的条件,就更是放开来读。有了这样的经历,就不怕别人蒙我,听别人板着脸孔教训我。我就知道马克思是怎么说的,鲁迅是怎么说的。因此,我一出狱,就南北奔波,找巴金说,想恢复新诗运动的历史真相,出些好多年没出的,包括徐志摩等人的诗。当时,这是个烫手的山芋,最后,靠巴老帮忙,把这事交给了他侄子,在四川负责出版的李致,于是《徐志摩诗集》《胡也频诗稿》《戴望舒诗集》等才得以首批问世。蔡 毅:
想不到周老师还有在劳改队睡在书堆上随便读书的奇遇,太好了,因祸得福。我们在“文革”后期和下乡之后,根本找不到书读。往往得跑好多地方,想尽办法才找得到一两本可读之书。因为它们或被作为“封、资、修”的东西封存,或作为“毒草”禁书不让人碰。我就曾因为那时爱读书遭灾受难,被当作异类排斥、批斗,现在想起来恍若隔世。周老师,想请您谈谈您的文艺观、美学观和诗学主张。周良沛:
我有幸自新中国成立前就开始学习新诗,在圈内摸爬滚打至今。对“五四”新诗的开创元老,只要健在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都有不同程度的接触了解。对俞平伯、冯至、艾青、田间等,均在不同的机缘中成为忘年之交。他们对我了解、熟悉早期新诗运动的状况,提供了很多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我又有幸见证参与了新诗发展的整个过程,也就自信有一份当事人的发言权。对于诗歌,我历来主张:“诗就是诗”,认为诗最根本的就是思想与情感的结晶,是具有诗思之诗美,并具相应的艺术方式所表述之作品。我曾这样写过:“每一首真正的诗,都应该是诗人一次新的艺术创造,是自我,也是诗的一次崛起。创新,就像人体的血液循环一样,在沸腾艺术的生命。” 诗是社会文明的内核,它在内容上总得有点真、善、美,以及激人向上的东西。我既拒绝为艺术而艺术躲进象牙塔远离社会生活,同时也拒绝以庸俗社会学简单地配合、迎合政治任务,将标语口号类的东西当作诗。我认为:若有“纯艺术”,只要它是“艺术”,不论纯到什么程度,一概欢迎。同样,对于诗的功利性和社会性,只要写的是可以成为艺术品的东西,更要欢迎支持。过去有人曾批徐志摩的“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在梦的轻波里依洄”的诗句,认为它是没有立场者的自白,但谁也不应该否认它是诗。因为作者擅长巧妙地把人生的全部复杂性做诗意的提炼处理,用清丽的诗句抒发了细腻的情怀。它表现的迷茫、彷徨、苦闷的情绪,也是提供了对此种人生的认识。这一认识作用,不能完全视为消极的,由此确定它是人生不辨方向的自白。相反,艾青复出后,他的诗《浪尖上》在一九七八年朗诵会上,“一切政策必须落实,/一切冤案必须昭雪”获得十五分钟经久不息、暴风雨般的掌声,但那是口号,是政治主张而不是诗句。若将掌声当作诗的裁判权,就很不好了。这是庸俗社会学,虽涉及艾青,我也批评。我认为:他那《大堰河》有很多好东西,但开篇“她的名字就是生她村庄的名字”之行文的西化,是不宜同前者一同提倡。我认为:诗歌艺术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政治也不能等同分行抒写的自身,但它对于为诗者的成败,却有撇不开的作用。这和我前面反对运动中用政治口号的配合、堆砌,图解政策,取代文艺的态度是一致的。那样,只能用所谓的“政治”葬送艺术,用所谓的“艺术”庸俗化了政治。我们要防止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蔡 毅:
说得好!我就喜欢多听听周老师对诗歌,对文坛的一些看法。周良沛:
过去,不论左翼、右翼,以人划线,都不可取。郁达夫,我不以他在鲁迅一边点赞,反之,我也不否定他。他不是都写得很好,不过,他写人的性之苦闷,从过去以苦行僧的标准要求人的状况下来看它,不是惊喜,就是否定。恩格斯讲:人能够以婚姻把性爱与情爱结合在一起是时代的进步。对此,我们也是在进步中。我们不是禁欲主义,邵洵美的诗,谈性写性,就写得很美,比现在那些写“下半身”的,高明多了。可也不是纵欲主义,那样,人就是畜生。现在的市场文学就是感官文学,绘画也如此,整个时代都在变化。我反感那些变色龙似的人物,随时走红,实用主义到了极端。如所谓的“朦胧诗”, 有的朦胧诗集里没有一首诗朦胧,是个最大的伪命题。可有的人,就随着对它的热议,瞎吹乱捧,肉麻。有人看了我过去的有关批评,问我怎么那样冷静,就没有卷入当时的热闹?我则告诉他,那“热闹”就不完全是真的,不少是“炒”起来的。我没有什么眼光,无非按良心办事。“炒”它的,无非有利可图。世间所有的名利,看穿了都是身外之物。给你名你受得了多少?给你利你吃得了多少?人只要能掌控自己的命运就最好。我在劳改队,等于判了无期徒刑。修成昆铁路时,与抢劫犯、小偷、妓女在一起,后来又与右派在一起,很多时候,我不如人,哪里最苦,就推你去,只有认命!谁叫你被人搞成“右派”呢?你既是 “右派”,就是要这样“改造”你?就是要你在石头里种出庄稼来!祸兮福兮,福兮祸兮?但我并没有堕落消沉。人要自重自爱自强不息嘛。我不愿渲染被劳改的苦难,有些人受了点苦就叫破天,生怕别人不知道。其实苦难确实考验人,既会摧毁人,也会成全人。它不全是简单的迫害,也有锻炼的作用。看看许多知青成为市场的能人,成为最高领导,就知道:苦难对人,不全是坏事。周良沛:
我最喜欢鲁迅,对鲁迅我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的《全集》我读了四五遍,从头到尾地读。孔乙己仅三千来字就写出了典型人物,现在许多名家,写了多少大部头,有几个创作出了一个典型人物?鲁迅《野草》里那么多象征主义的手法,不完全是传统的,它留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说老实话,若不是鲁迅,别人根本写不出来。我年轻时思想很“革命”,毛泽东推荐的《红楼梦》,不仅不喜欢,还看不下去,感觉家长里短婆婆妈妈的,很无聊。等我懂事,到了劳改队再读它时,就感觉它真是深刻、真是伟大,布局严谨巧妙,内容博大精深,恩爱怨仇能浓缩透视整个中国社会。《三国》《水浒》赶不上它。人的感觉和认识是在改变和深化的。我感觉“五四”后的诗人对我很新鲜,但感觉不到深刻。文学有很多偶然的原因,像雪莱一句 “既然冬来了,春还会远吗” ?马克思就评价很高,重视它特别的隐喻与象征。蔡 毅:
周老师,您最重视自己的哪一部作品?周良沛
:我的《丁玲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出版,62万多字。1996年又第三次印刷。还要重新再版。现在,美国亚马逊是卖两百多美金一本。蔡 毅:
周老师当初是怎么会要写这本传记的?周良沛:
十月文艺出版社想要给丁玲出传记,就去征求丁玲意见,她回答说自己生前绝不愿看到别人写自己的传记。后再问她若百年之后谁写合适,丁玲就说请周良沛写。丁玲去世后,我怕有负死者,就不得不写了,这是我的责任。于是我就下功夫写了这本书。昨天胡可同志打电话给我,说他又看了我写的冯达,说不能随随便便就讲人家是叛徒、特务,要有事实依据嘛。他如此说,自然是过去听多了骂冯达是叛徒、特务的。可见,事物是很复杂的,有时,还不在事实是怎么样,还有人需要它是个什么样的问题!若以人划线,胡也频遭反动派杀害,徐志摩为他出书、筹款、看望未亡人丁玲就会变得不可理解。徐志摩是否是铁板的“右翼”?咱说不了,具体到这一事实,此中还是有他的人道性、正义感,或曰人性。正视他的人性,也不等于人性论。我的书,对于丁玲究竟是莎菲,还是叛徒?是“三八节有感”的罪魁?或是 “一本书主义”的祸首?我采用了不少过去未被人用过的材料和真实具体的描述,以思辨色彩的文笔,用以塑造一个完整真实的丁玲,让这个我国现当代最著名的作家,也是受“左”的迫害最深,时间最长,经历最坎坷的人活现在读者面前。它受到广泛鼓励,对我也是最大的安慰。当然,现在来看,也有不满意的地方。若再次修改我可以写到一百万字,使之更丰满。若再改,就更通不过,目前能够再照原来的版本出版,我也很感动。我愿用丁玲得灾难来还原她的伟大。别人同情、怜悯,认识她,我不愿这样,更不想简单地写成控诉书。假设我没有受过灾难,是写不成《丁玲传》的,将心比心嘛,我从自己的受难来体会、认识她。灾难、磨难来了,谁想推是推不掉的,既然来了,只有面对,哭哭啼啼,成不了事,只有在灾难中磨炼自己。错划右派二十年,不是一句“改正”就“改正”得了的。灾难来了,既是痛苦难当,也是可遇不可求,它让我对人生和社会认识有了深化的提高,所以,我不愿简单地诅咒、抱怨,我不记仇。它也带给我一笔精神财富。这不是感谢灾难,是灾难让我懂得了许多平时不可能懂得的事。蔡 毅
:周老师,我真好奇,您怎么会与那么多文坛大家、前辈那么亲密,有很深厚的交往和情谊?周良沛:
我是文艺界的小兵,过去,人与人的关系,老作家真的是把我当作自己子女一样看待。大大小小的事,我都记得清楚。只是我早早地动笔写了它,别人还迟迟未动笔吧,等他们回忆的旧事写出来,你就可以看到,那是时代赐给大家的,不仅是给我!蔡 毅:
有人问,你怎么不成家?周良沛:
若成了家,我能像现在这样吗?国内和海外都有不少人认识我。不是我真有什么本事,而是这个时代成全我。有人要叫我写回忆录,我已写过很多,再写,自己重复自己就没意思。不过,六十年前,总政治部主任萧华知道我就是井冈山那地方的永新人,认为写土地革命时的情况很有价值,还有上井冈山时的毛泽东,都有可以写的。想起六十年前领导的嘱咐,也有过这么一点想法。想试写一点小说。现在,我是拿起笔来想写就写,放下笔就不想,没什么写得顺与不顺的问题。不像许多人那么周密地计划、构思。六十年前,也曾写过一些散文化、诗化的小说,没有写好。到现在,再试试吧。目前,我是用汉王笔,用电脑写。如今已有网上已披露的三卷六册的百年新诗选,一本个人的散文集,或者还有两本旧书新版。蔡 毅:
不简单,您一直工作,抓紧时间干事,很了不起。像周老师这个年纪的人,很少会用电脑。周良沛:
我没什么太明白的计划,随遇而安。人若只是吃饭睡觉,那就是行尸走肉。今天上午我就写到石祥,《十五的月亮》的词作者,就想到一个人一辈子能留下一点作品就不得了。“五四”以后,许多曾写过大量作品者,但到现在有谁还记得他们?无数的作品已经被人们遗忘殆尽。所以我不想让许多有意思有历史价值的事也一风吹,什么痕迹也没留下。本来我想写一本百年新诗史稿,想将中国新诗的历史作个回顾总结,但这样的书有几个人看?现在借正在编的这套《中国新诗百年选读》,传达我的想法就很好,除选编别人的作品外,当中也夹有我写的二十来万字的介绍与评述,为纪念新诗诞生一百周年做一些事。上天既给了我机会,我就紧紧抓住不放。浩大的工程,一个人干,很不容易。好在我熟悉相关历史,认识许多作家和他们的作品。拥有的资料也多,像当年冯至编的《沉种》《骆驼草》,我都全,《语丝》《创造》《新月》《现代》《北斗》等等都是全套的在。像这本《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他拿出一本比砖头更大更厚的书),三十年前琉璃厂就卖一千块,是近半年得工资,我也买了,其他人谁会买?现在省图、云大图书馆都没有。你去哪里找?坐拥无数资料,能干的事也就多,永远也写不完。蔡 毅:
周老师的积累真是了不得,可以建一个现代文学史和新诗研究所了。许多研究者也可以到您家找资料,访谈求学。您做的许多事,是一个班子才做得了的事。周老师您有没有带几个学生,教一些弟子?周良沛:
没有,我没有那个条件。组班子的事,那只有当官的人将它当作行政行为才行。人活到这把年纪,不世故也识点世故。你找人用人,要不要付劳务费?我付得起吗?你认为干的事有价值,人家认同吗?书就能出吗?叫我拿钱出书,一来我没有这个闲钱,二来也八十多岁,要向九十走了,还需要保留一点晚节。为此,只能孤军奋战,单人独干。钱钟书就说过:诗是语言的艺术。连ABC都不认识还讲什么现代派?正因为我对许多事熟知,所以别人休想来蒙我。当然,一个人样样都知道就成妖怪了!我的孙子评价我说:“爷爷脑子还可以,可手机都不会用,是世界上最笨的人”。蔡 毅:
周老师您跟蔡其矫也很熟悉?周良沛:
其矫,是归侨,先前分在安全部门工作,是丁玲把他弄到“文讲所”,才圆了他的文学梦。他是个天生的诗人。接地气,又总活在他诗的想象里。按他的资历,是可以当高官的。但他用审美的观点看生活,并不汲汲于功名。他写的诗比较洋气,也很人性、温暖。他是中国新诗的探索者,深受美国诗人惠特曼的影响,以自由奔放的语言风格和我行我素的意象写作,其特立独行的行事作风在中国诗坛独树一帜。他有许多人根本达不到的水平。我支持他,评论过他。蔡 毅:
这次编《中国新诗百年选读》,有什么新的发现和体会?周良沛:
这次选编,校正了许多问题。选编的作品有的也有明显的局限性,但它有代表性,有它独特的点,是作品留下的那个时代,不可轻易否定。新诗百年,作品我们是按年代排列为序,由此纠正了一个历史的误判。过去所有人说起新诗都是将胡适或刘大白算作第一人,认为是他第一个写的“白话诗”。而我则按史实,将郭沫若扶正为第一人。他于1916年就写出《维纳斯》。这一史实不能漏过。郭沫若自己一九五九年五月也在《文学知识·答青年问》时说过:“我写新诗比胡适等人要早”。胡适是一九一八年才写新诗的嘛。但郭沫若的此诗写出来并未公开发表,到一九一九年收入《女神》时才首发。Venus,通译为维纳斯。内容不长:“我把你这张爱嘴,/比成一个酒杯。/喝不尽的葡萄美酒,/使我时常醉!//我把你这对乳头,/比成两座坟墓。/我们俩睡在墓中,/血液儿化成甘露!”此诗表现青年正常的性爱追求,吟诵争取恋爱自由、个性解放的斗争,不乏针对封建礼教的锋芒,何尝不是人性、人权、人道之所求。作为百年新诗的首篇,具有特殊位置和意义。这一传奇,正好作为新诗面市的时代背景。蔡 毅:
好!郭沫若之《女神》开一代诗风,以其“狂飙突进之时代精神”之作超前于“白话诗”,周老师的研究将改写部分新诗历史,太有贡献了!而且从诗歌的角度讲,郭沫若的诗影响远胜于胡适,比他写得好,有气势,有意境,有才情。发人之所不能发,写人之所不能写,《女神》的出现,标志着新诗走向阔大和成熟。周老师您在2015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诗歌之敌》中,详细阐明了您的诗美学、诗学观,我拿到手就感觉沉甸甸的,有坚守,有批判,有信仰与情怀,令我心头一惊。因为同类书名的作品,我只见过李建军写过一本《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李建军是中青年一代,他也是文坛上一匹黑马,敢说敢讲,直言无忌,写下了不少漂亮有锋芒的文章。周良沛
:《诗歌之敌》一书是借用鲁迅先生早在一九二五年就写下的《诗歌之敌》之篇名,加上闻一多先生“人们在发现不是诗的时候才知道什么是诗”之名言,对中国诗歌历史和现状及发展历程加以总结而编成这一本书。它比较全面完整地体现了我对诗歌、诗坛的看法和态度,也展示了我从事诗歌创作多年来的心路历程。我强调各种观点、理论的确立成形,常常是无法避免与其他异见的摩擦、对立、争辩和斗争,才得以丰富和强壮。任何一个真正的诗人,要写出像样的作品,即便不是那么自觉,也无法离开他民族、哲学、文化的基础。任何“配合政治”,远离文学自身特质的分行文字不可取,那些远离人间烟火之颓废、虚无的、纯以自慰的诗之梦呓,同样不可取。我在书中,对“朦胧诗”、“现代派”、“表现自我”、“扩张自我”、“危机与繁荣”、“诗与政治”、“新诗与传统”、“理想与标准”、“含蓄与晦涩”、 “崛起的美学原则” 等许多问题都做了自己的思考与答辩。我强调诗道有正有歧,有大道有小路,任何时候都不能忘了出发的初衷。诗歌和文学传统是薪火相传的,传承绝非保守封步,恰是拓展开阔诗路的起点。坚持人生信仰,包括对诗的真诚,分清晦涩、含混、凌乱、恍惚,剔除非诗、伪诗、假诗、赝诗,诗歌才能大步前进。蔡 毅:
周老师的许多观点值得重视和重申。现在很多人对新诗发展的历史根本不懂,却自高自大自鸣得意,实际浅薄得很。周良沛:
对新诗百年的历史,我们需要好好总结,千万不能患上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健忘症。我最欣赏聂鲁达一九七一年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所说的:“诗人之敌,莫过于他自己没有与同时代的最被忽视、最受剥削的人们找到共同语言的能力。”“诗人不是‘小上帝’,决不是‘小上帝’。他并没有超越从事其他职业的人之上的神秘命运。我过去常说,最杰出的诗人乃是每日供应我们面包的人,也就是我们身边的、不自诩为上帝的面包师。他们为了尽社会的义务,从事揉面、上炉、烘烤和每日送面包这样一些既崇高又卑微的工作。如果诗人有这种纯朴的觉悟,也就有可能把这种纯朴的觉悟组成一个其结构既简单又复杂的伟大的艺术品的一部分;这就是建设社会、改造人类生存的,为人们提供面包、真理、美酒、梦想……”让诗歌和文学成为建设我们新生活的钢铁与面包,是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个国家与诗之根本的根本。因为近百年的新诗运动,无论是创作实践或理论,每前进一步,都因时因地无法不遇到不同之“敌”的干扰、破坏,不正视它就无法向前。战胜和清除了各种诗歌之敌,诗应能阔步前进。蔡 毅:
周老师说得太好了,感谢您。我还想问最后一个问题,周老师您现在每天怎么安排时间,有些什么娱乐活动?周良沛:
我每天晚上睡四个小时,白天睡两个小时,六小时足够了。晚饭后看一两小时电视或读读报刊。不可能有什么空闲。蔡 毅
:难怪周老师耄耋之年还干了那么多的活,出了一本又一本书,让我们这些年轻一点的都感觉惭愧,同时也非常敬佩,真心地向您学习!(本文由蔡毅记录整理)
责任编辑:万吉星
展开全文▼
展开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