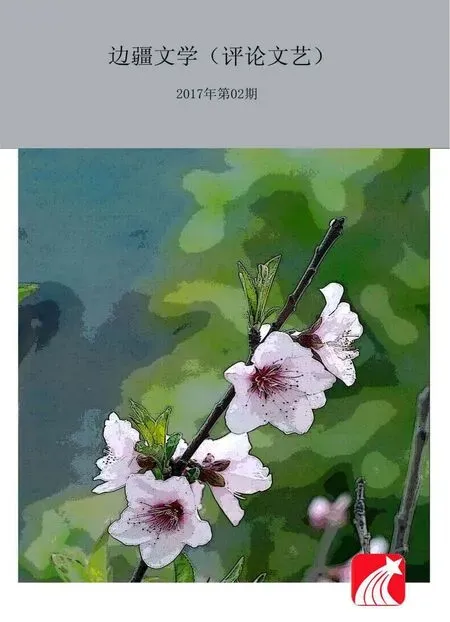文心的探秘与构建
——蔡毅访谈录
2017-11-13王海东
王海东
文心的探秘与构建——蔡毅访谈录
王海东
采访者手记
:蔡毅是云南省知名的文艺理论专家,著述甚丰,已出版十余部专著,洋洋数百万言,其学术旨趣主要在于研究文学创作究竟是怎样发生与进行的,创作中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追求价值、创造价值这一类核心问题,同时关注国内与世界文学前沿问题,笔耕不辍,创作亦盛,可谓集理论研究、文艺评论与文学创作于一身,且成绩斐然,而一以贯之的文心便是文学价值论。文学价值就在于选择与创造,以创造为本体,以选择为核心方法,而价值则是目的论,由此构成一个理论大厦。无疑,为我们理解文学提供一个新颖的视角。被采访人:蔡 毅
采 访 人:王海东
访谈时间:2016年11月30日下午
地 点:蔡毅家
王:对您的采访难度较大。因为,您不仅是一位学者,长期研究文艺理论,而且还是一位作家,出版过散文随笔集,此外,您还从事文艺评论工作。更为关键的是您关注的面非常广,涉及文学、艺术、哲学等多个领域,且侧重于基础理论研究与探索。所以,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不知您是如何处理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蔡:理论研究、创作和文艺评论这三者,对我而言比较自然,没有什么矛盾。它们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我早年喜欢创作,学写点诗歌、散文和小说。同时,也喜欢探究更为深层的理论,想探究现象背后的东西。逐渐就转向文学理论和哲学,又因1985年调到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从事编辑和研究工作,就进一步系统研究文艺理论。与此同时,那个时代对文艺理论的探讨也极为活跃,我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其中有的刊于《文学评论》一类刊物,多篇文章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引起了一定的好评和社会关注。这样,更促使我继续进行理论探索与创新。对理论的兴趣就促使我把研究重点转到创作理论研究。为了不脱离创作实际,也由于在阅读之中,读到一些好的作品,故而也就写了些评论作品,只是没想到,三十年来,也写了不少评论文章。时常被人谬称“评论家”,其实我自己看重的是理论。
王:可谓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蔡:是的。当时搞文艺评论是业余爱好,类似于“副产品”。不过意义也重大,是对一些作品和作家的深入学习与研究剖析,从中也磨砺思想,增强体验,补充实感,密切与文坛的联系。
王:看来这三者对您而言是一体的。理论研究使人深刻,能够统摄各种经验材料。创作使人空灵,能够培育编织想象与经验的技艺。批评使人清醒,能够形成评判优劣作品的眼光。
蔡:是的。于我来说,三者还有一种互补关系,也就是说,有些经验是个体性的独特感受,往往是理论论述无法容纳的,那么我就可以通过散文随笔的写作来叙述。而文艺批评,往往是阅读感受、体验的最好表达方式,为优秀作品点赞,给糟糕的作品差评,对文坛和时风给予及时的批判与回应,这种方式最直接。三者的交替穿插和叙述互补,是极为有益,也是令人难以割舍的。
王:是呀!这三者您都有丰硕的成果,不过对您来说,您最为重视的是何者?及其原因?
蔡:我最为关注的还是文艺理论研究,一直希望能够贡献一点新理论,新知识出来。
王:是的。通过阅读您的《创造之秘》和刚结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文学的价值选择与价值创造》,就能窥见您的“良苦用心”——力求提供一套新的文学理论。那么,你的理论构建工作进行得如何?有没有一个范畴来统摄之?
蔡:我之所为可用创作发生论和文学价值创造论来简明概括自己的理论。
王:不知您的学问生涯可否作阶段性的区分,也就是您思考的核心问题及解答方案是一直连贯的,还是有明显的分期?
蔡:严格地说,我这几十年来所思考的问题有变化也有坚守,那就是集中思考一些文学的基础和本质问题,尤其是创作发生论与价值论,我认为它们是最重要的问题,比起许多现象性、边缘性问题更有意义。阅读、写作与评论,基本上都是围绕这些问题逐步展开的。大体来说,早年在文学创作发生论上花的时间和精力多一些,新世纪以来,则侧重于价值理论研究。
王:您的研究有一以贯之的东西,就是您的“文心”。您一直在寻求的就是文学之道。从您发表的重要文章,也能看出这一点。
蔡:是的。“文心”是为文之道,是文学潜隐的核心。“文心”可以雕龙,可以雕虫;可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也可淆乱是非唆人作恶。相比很多学者注重某一个作家研究或者某一作品研究,我则更注重对文学这一创造性的精神活动根本性问题的研究。寻求对始基性、本源性和核心问题的新探索与回答。
王:这是最为艰难的工作。不知您做出这种选择有没有受到一些人的影响?即在您的学术生涯之中,有没有对您影响较大的师长与朋友?
蔡:做出这样的选择主要是自己的兴趣爱好以及理想。当然也有老师的影响。对我影响最大的老师是赵仲牧先生。
王:赵先生对您主要有哪些影响?
蔡:赵先生思维严密、视阈辽阔、知识丰富,更善于条分缕析,犹如思想的解剖刀。年轻时,每当我认为自己有一些新观点新创见时,与他讨论,经他分析和追问之后,就显得非常单薄肤浅了。只好再努力思考和研究,再不停地探索完善。任何问题一到他的思维之中,就变得清晰起来,这种逻辑分析性思维,能够推着我进一步去思考,去寻求创新,而不止于既得的小收获。他那种对思想创新的渴望和要求,为我开辟了一种高远深邃的境界,使我明白创立一个新观点是微不足道的,还要去寻求更远大更根本的创新创造。
王:是的。赵先生极为重视理论创新,一生孜孜以求创造自己的“开显哲学体系”,永远都是以伟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作为自己的对手和参照。
蔡:他永远都有新的想法,“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犹如云中龙,自由地翱翔于思想的汪洋大海,追求宏阔高远之境。使我深知“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明白为学的深邃境界,不断地向真理之峰攀登,学无止境,创新也无止境。
王:所以您也格外重视创新。
蔡:一个学者没有独特的创造,即创新,就没有什么价值。我的理论研究工作就在于探究文学创作究竟是如何发生形成的,创造的秘密何在?文学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它究竟有何用,如何自觉而主动地把握它,掌控它为己服务?
王:我国古代的文心就是文学之道,那么您的文心就是文学价值论。然而,进一步如何展开呢?
蔡: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和不断的提炼,我将自己的想法概括为几句话,提升为一个极简要的表述或命题,其结论或者说文心可以简单地表述为:价值是一切文学创作所追求的根本目的。文学价值就是创作者通过选择与创造所形成的。再精简地说,价值就是选择加创造,选择加创造才能产生价值!
王:请您阐释一下这个命题。
蔡:文学创作发生论研究完成后,我就集中研究文学价值论。早在七八年前,价值、选择和创造这几个核心词就居于我的文学理论研究的中心位置。经过反复的咀嚼,不断地揣摩和多年的探究与写作,虽未能构建出令人满意的理论框架,但是也有一些进展,相关著作已经写成,很快就能出版面世。关于文学价值论的理解,首先是要确认价值的含义,已经发表的专文《价值之定义与功用》就是回答这个问题的。我从多解论的角度,将“价值”的性质、特质、功能和属性揭示出来,不再纠结于一个单薄的定义,而是在复合型的现实中,将其意义呈现出来。人类在对价值的探索过程之中,愈加认识到价值是人类追求的核心,是思想与精神动力的原点。价值在重建人文传统、确立科学精神与文学艺术的合法性上,都承担着奠基作用。人类对价值的追求也是一个永不停歇的过程。
王:的确,学术界对“价值”的界定非常多,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考察,以免误用而增加错误。这一概念,从种差加属的角度,是无法定义的。您选择多元描述性定义,有语言哲学之风。您对价值的理解,有没有摆脱二元论思维?
蔡:超越了二元对立的思维。学界不少人争论价值到底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这是多余的探讨。于我而言,价值既能被发现,又能被创造,主客一体,很难做出清晰的分别。
王:我完全赞同您的观点。其实从建构主义来看待价值,更为妥当。价值是人文世界之物,既有主观性,又有实在性。那么,价值与真理是何种关系呢?
蔡:价值与真理不同。真理是不变的,而价值是可变的。真理只能被发现,价值则被创造。
王:我的看法与您的不完全一致。二者有别,这个没问题。感觉你所说的价值有点类似于“相对真理”。在我看来,真理是绝对的,但是也离不开人类的建构,即其绝对性也掺杂着主体性,所以黑格尔说“实体即主体”,绝对的上帝就是绝对精神。而这种建构性丝毫不影响其绝对性。有没有一些价值具有绝对性呢?比如自由和理性,虽是创造的,但具不具有绝对性与普适性?
蔡:嗯。毫无疑问,自由与理性是具有绝对性和普遍性的。你说的是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了,即价值哲学问题。对价值进行更为深刻的挖掘,也就是探究价值的相对性与绝对性问题,非常有意义。
王:澄清“价值”后,请您进一步谈谈文学价值论。
蔡:确立价值的普遍性和重要性之后,当然能否适用于科学?还不好说,但是对于文学、哲学、历史、艺术、宗教和社会科学等都能适用。就能肯定价值、价值观和价值论对文学创作,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甚至是第一位的意义。进而论述一切创作都是为了追求价值、创造价值,可以说“价值为王,价值至上”。价值才是文学创作追求的根本目的。然后我想说的是一切真正的文学创作,既是一种思想、情感与审美的建构活动,又是一种精神价值的生成、创造活动。创造价值就是创造新的意义世界、符号世界和精神情感世界,它让人活得更加有滋有味,生命境界得以不断净化提升,人的精神面貌更加丰富多彩。
王:不仅是文学,所有的精神活动都理应如此。创造富有价值的思想,是一切精神活动的根本。所以每一位作家、艺术家、哲学家、思想家和科学家,都在创造意义世界。而他们的目的则在于为人类提供更具诗意的家园。这也是您一直致力的目标!那么,如何才能创造文学的价值呢?
蔡:我尝试着从多视角多层面去解答这一难题。从创作心理、思想实验、生活实践、内在修养等方面进行了探讨。除了将文学创作当成创造价值的活动之外,还将这一活动比喻为“炼金术”,也就是把日常生活中不起眼的生活事件与素材,通过选择、虚构、想象、综合、变形、提炼等多种方式与内心创造,生产出金子般的精神产品,让无价值之物或低价值的东西,变为充满价值的东西,以福泽人类。
王:所以您将“选择”也纳入到文学价值论体系之中,且是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也是方法论,创造是一种本体,价值是动机,也是目的。请您解释一下“选择”?
蔡:对,可以进行这样的哲学表述。既然文学是一种自由地创造价值的活动,就有如何进行创造的方法论问题。生活之中有很多原料,作家不仅从自己经验,也可以从他者的经验之中,一点一滴地挖掘,筛选自己需要的素材,犹如春蚕食桑,经历漫长的时间,吃了无数的桑叶,才吐出洁白无瑕的丝。而普通大众,则无心留意日常琐碎经验,好比吃桑而不吐丝的蚕,自然也就写不出好的作品来。
王:是的。与大众相比,作家不仅有这种自觉,即能够于细微处收集许多经验,而且还有一种方法的训练,也就是通过广泛的阅读、学习和研究,吸收有益的技巧,并在模仿、综合与创新之中,形成自己独特的方法。
蔡:对!技巧是一种叙述表达的本领,一种综合调控的水平,但又是一种师难传徒,父难传子的“玄妙之技”。但也不是独门绝技,而是可以学习,领悟和运用的。任何技法都不是从天而降的,没有不受前人影响的天才。
王:是的。其实只要深入研究,任何天才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前人的影响,即便被很多学者称为天才哲学家的维特根斯坦也受到叔本华,歌德和宗教的影响。释迦牟尼受过当时印度最完备的教育,古印度六派哲学思想,他娴熟于心。
蔡:写作技巧也是在长期学习、累积、借鉴、磨练和探究之中形成的。它犹如一把刀,能帮助你对混沌的生活、纠缠的事物进行有力的切割。有时如针,能够将经验、素材、感知缝制成精美的衣裳。有时如万能胶,能把一切貌似无涉的东西粘贴黏合,连为一体。有时如火,能把简单粗糙的材料锻造得浑圆晶亮,熠熠生辉。在长期的实践之中,反复练习,用心揣摩,领悟经典,则熟能生巧,巧中求精,技术技巧就生出来了。
王:作为方法论的“选择”意义重大。而中国古代文化重道轻技,您是如何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的?
蔡:由于长期撰写文艺批评,就看到不少遗憾的作品。有的善于讲故事,但缺乏深度,没思想。有的思想深刻,但缺乏想象力。有的想象力丰富,但叙述乏力,毫无吸引力。很少有作品能够兼具语言、素材、形式、故事和思想之美,能够集各种优势于一体,就堪称经典了。
王:是啊!尤其在商业化的今天,为名利和权力写作的太多,精品极少。您的理论建构有较大的时代意义。
蔡:很多作家已经缺乏文以载道的意识。文学创作与价值创造的任务就是写出生活之真、人性之美,追求文以载道,参与锻塑民族魂魄,对时代和社会有着自觉的担当,为时代画像谱写一代民族的心史。
王:嗯,这就是文学的时代使命与大道。也是您文学价值论的终极目的所在。
蔡:这是我努力的方向。因此,文学创作的目的在于道,而方法技巧的创新是有益于更好地呈现道。同时,高超玄妙的技艺,何尝不是一种境界呢?
王:是的。二者相生相济。没有道的技艺,永远都是一种技术。没有技艺的道,则似蓬头垢面的灰姑娘。在我们的谈话中,您多次提到“境界”这一概念,想必在您的思想中,也比较重要?
蔡:是的。这是下一步研究计划,探究文学价值与心灵境界的关系。
王:这个难度很大!当今英美哲学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心智哲学,流派多,争议大,令人困惑。
蔡:正如你所说,难度很大,我也还没有思考清楚,得慢慢探索。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们都在殚精竭虑探索的问题,往往是最为重要的问题,同样对我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越是对人类重要的,其价值越大,而这正是我的研究对象。我不喜欢在琐碎的问题上,耗费自己宝贵的时间。人生短暂,而我愿意将自己这短暂的时光交给最重要最核心最普遍的问题,因为它们意义重大,关乎着人类的兴衰存亡。
王:这就是您的精神动力。它支撑着您数十年静默于宅,抛开尘世的浮华与喧嚣,安然于自己的思想领地!您所提及的“好作品”,如何衡量?也就是您判断好作品的标准有哪些?
蔡:对我而言,凡是见识高、经验新、思想深、表述好、形式美,能够超过自己,给我以新奇感和思想情感启发的作品,都是好作品。令我喜爱并敬佩的,就是好作品,就是高明的作品。值得向其学习。
王:这不仅是您的个人经验,其实也是经典的标准。您如何看待眼下的文艺界?与80年代相比,最大的差异是什么?
蔡:对文坛的批评很多了,我也曾写过不少批评的文章。出版过《文坛与批评》一书。在此,我倒更愿意跟你们年轻人谈谈80年代的一些情形与感受。一是当时社会自由而有活力,充满着冲破一切的勇气。所以打破禁锢束缚的机会非常多。二是参与度非常高,参与人数众多,不仅搞创作的人多,搞理论评论的人也多,而且被关注度非常高。这当然与“文革”有关,一开放,各行各业的人都满怀激情地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无所畏惧。三是文艺禁区较少,年轻人敢于挑战权威,提出新观点。当时,我一反陈旧观点,批评反映论,提出文学是人学,文学创作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精神创造活动。一些生猛观点发表后,反响很大,多篇文章被转载。极大地激励我进行理论探索,且敢于摆脱所谓的权威,阐发自己的看法。我的《文艺沉思集》一书就是那时的结晶。
王:是啊。现在难度很大,不光禁忌越来越多,而且对于年轻人,别说挑战权威,就连发表文章都成为难事,得寻找各种关系,甚至还得送礼送钱,请客吃饭,才能发文章,如此一来,很多人也就无心于学问。而且学界往往还制约着年轻人发表自己的看法,这样的文章基本上会被“毙掉”。所以只好研究某一家,某一作品或某一流派的思想。当然,一般而言,年轻人也难以驾驭大问题,并提出新观点,做出令人信服的论证。但这不是拒发的理由。学界江湖化、帮派化极不利于青年学人的成长。更别说生存压力、家庭负担和社会恶性竞争,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蔡:也不要这么悲观。我们那时想读书,却无书可读。上山下乡,流放乡野,被耽误很多大好年华。饥饿与贫穷是常态,任何时代都难免。关键还是在于自己,如果能够坚守,做出成绩来,那么还是会得到认可的。
王:相比您的经历,我们这点苦算什么。给我们谈一些您的人生感悟吧。
蔡:自知者明,知人者智。先要清醒地认识自己,确立人生方向,树立高远理想。然后,沉下心来,一点一滴地积累,拼搏,锲而不舍,命运才会改变,理想才会实现。当然,个体命运也会受到大时代的影响。但是,若能坚守,终究会开花结果的,只是实现的程度不同罢了。我不赞成宿命论,动不动就说是命,把许多无奈之事归结为命是非常简单而无济于事的。
王:是的,宿命论者往往以之为借口为自己的懒惰辩护。其实是“命自我立,福自我造”,安于本分,勤劳耕作,思想的园地或多或少都会有些成果。那您对我们这些年轻的科研人员有什么样的建议?
蔡:对于青年而言,这个时代有其优越之处。国家富强,各种科研项目愈来愈多,扶持力度越来越大,条件日益改善,所以若能将这些优势条件与自己的研究有机融合,则可转不利为有利,促进科研学术更上一层楼。更为关键的是你们的起点高,不是在废墟之上,不仅有读不完的经典,还可以得到良师益友的指导与帮助。西学东渐,西方的观念与经典大量涌入,能够开阔视野,甚至是进行国际学术对话,走向全球,成为世界级的学者。我们那时的精神粮食稀缺,看样板戏,电影就那几部,更别说阅读国外经典,就连中国古代经典都难以读到。而今,互联网时代,咨询发达、信息传播快,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获得自己所需要的信息。不过,每个时代都有其不利的东西,你们所面临的困惑与诱惑也不少,也有不少新的禁锢在形成。放眼未来,虽有不少忧虑,自由创造的空间狭小,但还是能够积极地做一些事情,尤其可以发挥出版自由和网络发布自由等有利条件,进行创造与教化。关键仍在于个体自身努不努力,愿不愿意抓住思想中的核心问题进行研究,若静心研究,智慧地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则前途不可限量!民族国家的进步,是需要大家共同的努力才能实现的!
王:谢谢您的建议!我们今天的访谈到此结束。
责任编辑:万吉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