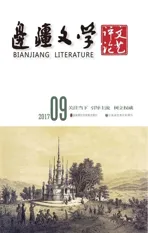风格故事:马尔克斯第一部小说《枯枝败叶》解读
2017-11-13孙金燕
孙金燕
经典重读
风格故事:马尔克斯第一部小说《枯枝败叶》解读
孙金燕
·主持人语·
马尔克斯《百年孤独》固然是传世名篇,但他的第一部小说《枯枝败叶》也同样是一部经典。青年学者孙金燕博士的论文,从四个层面完整地对这部小说进行解读,立意不凡,论证有力,见解独到。作者认为马尔克斯的每一本小说“都在写作‘自己的经历’,不是为了‘摆脱自我’,而是‘实录’他眼中风云变幻的哥伦比亚和南美大陆神话般的历史,尽管这些向来被视为‘魔幻现实’。” 而《枯枝败叶》作为他的开山之作,奠定了这种叙述基础。
巴尔扎克的《萨拉辛》之所以如此著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罗兰·巴特。巴特的《S/Z》对这篇小说的拆解式细读,成为后结构主义解读策略的先行者。然而真正把《萨拉辛》作为一个独立文本来做一种叙事技巧的阅读却是寥寥无几,大多数学者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巴特思想的影响,将文本强制与巴特的论调粘合在一起,这对作为个体存在的《萨拉辛》是不公平的。本文试图将文本看成一个独立的个体,以叙事学理论作为依据,主要从非线性叙事时间、“潜变化”叙述者以及身体伦理叙事三个方面对该文本的叙事技巧进行解读,并尝试进一步论述隐含在文本叙事背后的“逻格斯”叙事权威,由此证明《萨拉辛》作为一部现实主义小说所具有的传统思想主题,而并非巴特所谓的该作品思想主题的“虚无性”、“无中心性”。文章有自己的独特想法,值得推荐。(李 骞)
“众所周知,初次进行创作的人具有把自己的经历写进作品的强烈倾向,他把自己或者一个替代者放进他的第一部小说中,这样做与其说是由于现成题材的吸引力,不如说是为了摆脱自我后可以去轻装从事更美好的事情。这是我接受的极少数的一般规则之一。”这是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关于其第一部小说《玛丽》的表述。然而这种“规则”对于某些作家并不适用,加西亚·马尔克斯就是其中一位。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他的真实生活。从第一部小说《枯枝败叶》到最后一部《苦妓回忆录》,他都在写作“自己的经历”,不是为了“摆脱自我”,而是“实录”他眼中风云变幻的哥伦比亚和南美大陆神话般的历史,尽管这些向来被视为“魔幻现实”。所以,想要了解马尔克斯,从哪一部作品进入都不会失望。《枯枝败叶》作为他人生的第一部小说,则更可当作他此后所有小说的“雏形”来阅读。
一、讨论这部小说的原因:马尔克斯难以释怀的“伤害”与“同情”
从写作意义上说,《枯枝败叶》(1955)是马尔克斯的第一部小说,尽管它的发表迟于《第三次辞世》(1947)。大学二年级,他随母亲回出生地阿拉卡塔卡(Aracataca)小镇出售外祖父的房子,此次重返故地即使他萌生写一部家族史小说《家》的意愿,但把握一个大家族的命运,在他当时还有些力所不逮。于是,他五易其稿,最终在整体上成为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部中篇小说《枯枝败叶》:通过为一位自杀的大夫敛尸送葬的事件,以三个人物视角,描绘了一个叫马孔多的小镇上人们精神和物质双重困境的生活。书名则来自“当年外婆曾以遗老遗少的姿态,用这个既显轻蔑又富于同情的说法描述联合果品公司造成的破坏:枯枝败叶。”
关于这部小说,马尔克斯有着难以直言的发表困惑,也有着深刻的“同情”。
《番石榴飘香》对这部作品如此评价:“《枯枝败叶》是一本内容充实的书,它已经包含了马孔多所有的荒凉以及对昔日的眷恋,完全有理由使它的作者名扬拉丁美洲。然而事与愿违。任何一位作家只要写出一部优秀的作品便有权享受公众的承认、声誉或者说酬谢,却在许多年之后才来到他面前。当时,他的第五部作品《百年孤独》,出乎他本人的意料,先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后来在整个拉丁美洲,最后在全世界,像热香肠似的出售。”“热香肠”的比喻,来自马尔克斯对全世界评论界和读者追捧《百年孤独》的自嘲:“为什么我的一本我估计只有几个朋友会看的书会像热香肠一样到处出售。”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马尔克斯的自传《活着为了讲述》中,也常将《枯枝败叶》与《百年孤独》放置一起对比表述,重点不在它们的写作精神与形式,而在出版与发行问题上,尽管评论者更在乎前者:“早期的《枯枝败叶》无论从题材、主题,还是叙事风格上都可以看成是《百年孤独》的雏形。”以此,足见这部不仅未带来“公众的承认、声誉或者说酬谢”,甚至连面世都厄运连连的“优秀的作品”,与“热香肠”《百年孤独》一样,于马尔克斯这位后来的大师级写手而言,都有一种关于接受的困惑。比如下面这段描述:
“四年后,哥伦比亚文化基础图书馆馆长爱德华多·卡瓦列罗·卡尔德隆将《枯枝败叶》收入一套口袋丛书,在波哥大和其他城市的街头销售。稿费不多,但会按时支付。那是我拿到的第一笔稿费,对我而言意义非凡。这一版有几处改动,我认为并非出自我之手;在之后的版本中,我也没有刻意删去。差不多是三年后,《百年孤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版发行,途径哥伦比亚时,我在波哥大街头书摊看见多本首版《枯枝败叶》,每本一比索。我能拿多少,就买了多少;此后,这版又在拉丁美洲各大书店出现过,被当作古董书卖。两年前,一家英国古董书店出售了一本有我亲笔签名的首版《百年孤独》,售价三千美元。”
相比而言,对于“售价三千美元”的《百年孤独》,马尔克斯常常想淡化它的存在,比如在自传《活着为了讲述》中每每涉及到,也不过寥寥数语;倒是这部“每本一比索”的《枯枝败叶》,几乎贯穿他的整部自传,经常性大篇幅地讲述它的成书、出版、销售历史,即使是后来被普遍认可的《族长的秋天》《霍乱时期的爱情》《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等,都未能如此地被马尔克斯“在讲述中”重视。
多年后,马尔克斯称:“我非常珍惜随着我的荣誉而来的各种荣耀;但是,我更珍惜从我童年起就经受的种种打击、挫折乃至失败。我至今当然仍然清楚地记得伟大的编辑家吉列尔莫·德托雷先生,是他毫不留情地退回了我的第一部小说。”这位让马尔克斯“清楚地记得”的吉列尔莫·德托雷何许人也?便是当年有意愿出版《枯枝败叶》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洛萨达出版社的董事长,并在退稿信中措辞生硬:“此书毫无价值,但艺术上却有可取之处。”当然,他还有另一个身份,即另一位大师级写手博尔赫斯的胞妹诺拉的丈夫。
虽然声称“珍惜”《枯枝败叶》挫败的马尔克斯,看上去非常大度;然而“至今当然仍然清楚地记得”,又显露出某种难言的伤害。事实上,他的真实感受确实并非如此。他认为,退稿信判决书“回荡着委婉的措词、装腔作势和卡斯蒂利亚白人的自负”;当年洛萨达出版社没有选中出版《枯枝败叶》,“这是一个错误或者是一个恶意安排的事实,因为这不是一种文学竞赛,而是洛萨达为借助哥伦比亚作家进入哥伦比亚市场而确定的项目。而我的小说不是在同另一部小说的竞争中被拒绝的,而是因为堂吉列尔莫·德托雷认为它不值得出版。”
而与难以释怀于《枯枝败叶》的发表挫败相似,另一件让其耿耿于怀的事实,便是《枯枝败叶》的写作状态。他对当年创作这本书的小伙子“有点儿同情”,“因为他当时写得非常仓促,以为此生再也没有写作的机会了,这是他唯一的创作机会,于是他就把当时学到手的东西一股脑儿地塞进这本书中,特别是他当时从英美小说家那儿学来的创作技巧和文学手法。”
事实上,无论是吉列尔莫·德托雷所承认的“艺术上的可取之处”,还是马尔克斯“同情”的“学来的创作技巧和文学手法”,最终都成为了他在作品形式上的无可替代的风格标记。
二、一条浓缩的时间轴:两点半、一个下午与25年
后来的马尔克斯,无疑已被公认为是操纵时间的高手,《百年孤独》中那句被人谈论过无数次的开头:“许多年之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将会回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将过去、现在和未来挤压进一条浓缩的时间轴,为文学叙事提供了新的时间视点。以至于后来,连马尔克斯本人都急迫地想要逃避自己的影响的焦虑,终于在《霍乱时期的爱情》中以不显山不露水的方式开始,写过50来页才慢悠悠地让第一主角登场。而这种处理时间的方式,马尔克斯坦诚最初是受到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影响:
“如果我在二十岁的时候没有读到《达洛维夫人》中的这段话,可能今天我就是另一副样子了:‘但是,毫无疑问,(车子)里面坐着的是一位大人物;大人物遮掩着经过邦德街,凡夫俗子们伸手可及;他们可能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离英国的君主、国家的不朽象征这么近。等到伦敦沦为一条杂草丛生的道路,这个星期三上午在人行道上匆匆走过的人们全都变成了白骨,几枚婚戒散落其中,还有无数腐烂的牙齿里的黄金填塞物,好奇的文物学家翻检时间的废墟,才能弄清车里的人是谁。’”
马尔克斯声称:《达洛维夫人》“完全改变了我的时间概念”,“为撰写第一部长篇小说铺好了道路”[14]。
伍尔夫因其对时间的非常规处理,常常被归入意识流作家。她注重瞬间的心理真实,而非所谓的社会现实,在《现代小说》(1919)一文中,她明确表示:“让我们按照那些微粒落下的顺序,把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留下的印象记录下来;让我们把每种情景、每个事件在我们意识中留下的图像,不管表面看来多么支离破碎、互补连贯,都描绘下来。我们不可以想当然,认为生命中通常所谓的大事中比重通常所谓的小事中能够更完满地存在。”可以说,得其精髓的马尔克斯,在《枯枝败叶》中充分演练了这种时间技巧。
其一,他以“一个下午”的时间,回溯马孔多小镇“25年”的历史。
小说以第一句“这是我第一次瞧见死尸”的停尸待殓,到最后“棺材便晃晃悠悠地悬浮在灿烂的阳光里了,看上去好像一直沉船”,完成了三个人物外祖父上校、母亲伊莎贝尔和孩子为上吊自杀的大夫守丧送葬的缓慢过程。这“一个下午”的时间,通过孩子的疑问“我不明白为什么没有人来参加葬礼”,和母亲与外祖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在悬念中追忆了大夫与小镇的纠葛:
25年前,他带着大西洋沿岸总监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写来的信来到小镇找外祖父,从此寄居于外祖父家中行医4年,“因为香蕉公司开办了职工医院,四年来找他瞧病的人都不来了。他眼瞅着‘枯枝败叶’踩出了新路,但是没有吭气。他依然敞开临街的大门,成天坐在皮椅上,眼瞅着人们熙来攘往,可就是没有人登门求医。于是,他上好门闩,买了张吊床,往房间里一躲,不再出来了”;又4年,他与外祖父的养女梅梅搬到街角小屋公开姘居;11年前,人们发现梅梅失踪,在他家掘地三尺、追查未果;10年前,马孔多小镇陷入破产,“‘枯枝败叶’带来了一切,又带走了一切”,他作为当时留在小镇唯一的医生,因不肯救治暴动中的伤员而与小镇所有人断绝交往;17年来一直被小镇人怨恨、诅咒:“让大夫在这栋房子里腐烂发臭吧!”3年前救治了病入膏肓的上校,有了与上校的关于送葬的约定,及最后上校逆小镇所有人之意愿的践约。
这“一个下午”,既呈现了大夫越来越孤寂的人生,也呈现了在20世纪初美国投资家引起的香蕉风暴后,马孔多小镇表面的繁荣与实质上的贫瘠,“整个小镇显出一副像破烂家具一样的可怜相儿。似乎上帝已经宣判马孔多是个废物,把它撂倒了一个角落,那里堆放着所有不再能为造物服务的镇子。”
其二,他在同一时间节点“两点半”的火车汽笛声中,让三个人物的心理伸展向不同的时间方向。
(孩子)“汽笛又响了,声音越来越远。猛然间我想到:‘两点半了’。我记得每天这个时候(就是火车站最后一个弯道鸣汽笛的时候),同学们正好在校园里列队,准备上下午的第一节课。”
(母亲)“我听见火车在最后一个弯道上鸣汽笛的声音。我想:‘两点半了。’这会儿,整个马孔多都注视着我们在干些什么。我总是排遣不掉这个念头。”
(外祖父)“这时候,刚好火车拉响汽笛,随即在镇子的最后一个弯道那儿消失了。‘两点半了。’我想。一九二八年九月十二日的两点半。死者第一次坐在我们家的桌旁要青草吃的时候,大概就是一九〇三年同一天的几乎同一个时辰。当时阿黛莱达问他:‘什么草,大夫?’他带着浓重的鼻音,用反刍动物特有的那种慢吞吞的声音说道:‘普通的草,夫人。就是驴吃的青草。’”
这与《达洛维夫人》中“大本钟铿锵有力的钟声,报告半点钟”,在克拉丽莎、伊丽莎白、彼得·沃尔什三者之间引起的思维震动有点相似,却在时间指向上走得更远。当年,年轻的马尔克斯拿着《枯枝败叶》的初稿向年长的加泰罗尼亚学者堂拉蒙·宾耶斯请教,对方就如何处理时间大致说了几句:“您应该意识到,事情已经发生,人物的出现只是为了回忆。因此,您要驾驭两种时间。”
因此,在修改后的小说中,孩子、母亲伊莎贝尔与外祖父上校分别站在三个深具个性观察点上:总想离开现场的孩子向往的是与自己的小伙伴们玩耍,每次的表述都暗含着“如果此时不在这里,那么我将在做什么”,在时间上指向“将来”;母亲伊莎贝尔担心的是当下,即小镇人对自己一家人冒天下之大不韪来为引起公愤的大夫送葬的愤怒,在时间上指向“现在”;外祖父上校想的更多的是大夫在马孔多25年的孤独生活,“枯枝败叶”涌入后对大夫的影响,以及他对大夫充满着理解和同情,在时间上指向“过去”。
也就是说,这种对时间的过去、现在、未来的浓缩式处理方式,在其第一部小说《枯枝败叶》中“两点半”这个时间节点上已经崭露无疑。于是,也就不必讶异于后来《百年孤独》中首句的那次经典呈现了。
三、一个神奇的文学地理空间:“马孔多”小镇
小说《枯枝败叶》在第一节之前,有一段以“我们”为叙述者所做的类似日记或笔记的文字,末尾标注为“一九〇九年于马孔多”。
阅读马尔克斯者,对“马孔多”肯定不会陌生,它反复出现在他的《伊莎贝尔在马孔多观雨时的独白》《蒙铁尔寡妇》《格兰德大妈的葬礼》《恶时辰》等小说中。当然,最著名的还是《百年孤独》:在这场述说中,“马孔多”在布恩迪亚家族第一代带领的迁居而来的人们的努力下,由原来的一片无人的沼泽地变成繁华市镇,最后又在跨国资本的侵袭下遭到毁灭,飓风席卷了它,它在大地上消失。一场持续了4年11个月零2天的暴风雨将马孔多重新化为了洪荒和虚无,这个小镇象征整个拉丁美洲的的兴衰史,也暗示人类在不断的循环和轮回中永劫往返。
当年,关于《枯枝败叶》的写作,堂拉蒙·宾耶斯除了关于时间的提议,还曾指点马尔克斯:“小说里的城市不能叫巴兰基亚——初稿里是这样写的——否则,读者受地名所限,缺乏想象空间。……要不,您就装傻,等天上掉馅饼。反正,索福克勒斯生活过的雅典绝不是安提戈涅生活过的雅典。”马尔克斯自然没有“等天上掉馅饼”,但“馅饼”就一直在他童年在外祖父家生活的那段时光里,最终在随母亲重返故地“火车会在十一点经过马孔多种植园”时找到:
“火车停靠在一个没有镇子的车站,没过多久,又途经路线上唯一一片香蕉园,大门上写着名字:马孔多。外公最初几次带我出门旅行时,我就被这个名字吸引,长大后才发觉,我喜欢的是它诗一般悦耳的读音。我没听说过甚至也没琢磨过它的含义;等我偶然在一本百科全书上看到解释(热带植物,类似于吉贝,不开花,不结果,木质轻盈、多孔,适合做独木舟或厨房用具)时,我已经把它当作一个虚构的镇名,在三本书里用过了;后来我又在《大英百科全书》上见过,说坦嘎尼喀有一个名叫马孔多的种族,居无定所,四海为家。也许,这才是词源。不过,我没做过调查研究,也不知道马孔多树长什么样,在香蕉种植园区问过几次,谁也说不清楚。也许,这种树根本就不存在。”
《枯枝败叶》的结构方式,多少会使人联想到他的“导师”福克纳的小说《我弥留之际》,同样是一个关于葬礼及其回忆的故事。在其自传中,马尔克斯曾记录在陪母亲重回阿拉卡塔卡小镇时,他一路“重读威廉·福克纳的《八月之光》。当年,他是我最牢靠的精神导师”;为《民族报》撰稿期间,“我急切地想从逝去的时光中汲取某种好处,坐在打字机前,试图尽可能快地写出站得住脚的东西:《家》的片段,对《八月之光》所展现的可怕的福克纳……的拙劣模仿。”所以,缘于这种密切的精神吸引,很难说马尔克斯对“马孔多”的反复塑造,除了应和堂拉蒙所说的“想象空间”问题,他就没有向其“导师”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靠拢的野心。
终于,经过马尔克斯的反复勾勒,“马孔多”成了一个神奇的空间,一个独特的文学地理形象,一个“以密码形式容纳一切的世界村”。而最初在《枯枝败叶》中,马尔克斯已搭建起“马孔多”大致的历史发展与演变:
战争期间,上校一家在马孔多落脚,“那时候,这儿还是个正在形成的村落,只有几户逃难的人家。他们竭力保留传统的生活方式,恪守宗教习俗,努力饲养牲口。对我父母而来说,马孔多是应许之地,是和平之乡,是金羊毛”;
随着香蕉公司的到来,“铁路通车了,马孔多变成了一个繁华的集镇”;
当香蕉公司“压榨够了,带着当初带来的垃圾中的垃圾离开了马孔多。‘枯枝败叶’——一九一五年繁荣的马孔多留下的最后一点遗物——也随之而去,留下的是一座衰落的村庄和四家萧条破败的商店。村里人无所事事,整日里怨天尤人”;
当人们希图重建家园时,才发现“一堆由其他地方的人类渣滓和物质垃圾组成的杂乱、喧嚣的‘枯枝败叶’”,已对当地人现实生活及精神的冲击和影响,“‘枯枝败叶’经过天然发酵,终于融入到大地中默默发育的种子里去了”,重建家园几乎已成为无望的事件。
至此,我们也可看出,与最初的“应许之地,和平之乡,金羊毛”相比,随着小镇人传统的生活方式的被冲击,心灵无所寄托,“马孔多”小镇已在香蕉风暴中“枯枝败叶”化了,最终成为孤独的权力(《格兰德大妈的葬礼》)、以无名帖中伤他人(《恶时辰》)的实施地,并最终随百年孤独家族消散在飓风中(《百年孤独》)。
可以说,也正是从这部小说开始,“马孔多”这个神奇的小镇,成为了马尔克斯指称拉丁美洲历史与现实的一个投影与符号空间。
四、死亡与孤独:萦绕马尔克斯一生的小说主题
“这是我第一次瞧见死尸”,《枯枝败叶》第一句即狂暴地指向死亡。正如拉尔斯·吉伦斯坦在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词中说的那样:
“一种生命的悲剧意识体现了加西亚·马尔克斯作品的特点——一种命运至高无上和历史残酷无情破坏的意识。但是这种死亡的意识和生命的悲剧意识被叙述的无限而机智巧妙的活力冲破了,这活力代表了现实与生命本身的既使人惊恐又给人启迪的生气勃勃的力量。”
在马尔克斯的小说中,与其叙述的“活力”相伴的,总是“死亡”这个置身幕后的导演,这已成为其小说的一个恒久的主题。《礼拜二午睡时刻》述写一位母亲带着女儿乘火车远道而来,在全镇人的暗暗目光中,有尊言地为被人打死的小偷儿子扫墓;《恶时辰》始于塞萨尔·蒙特罗轻信了自家门上的匿名帖,妒火中烧中冲去巴斯托尔家,将其枪杀在鸽房;《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中,纳赛尔在镇上大部分人知情而自己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被杀害;《霍乱时期的爱情》中杰勒米雅·德萨因特·阿莫乌尔选择在60岁时自杀,为的是“我永远也不会变老”;这种对死亡的感知或生命的悲剧意识,以及企图超越终点的生命力量和激情,又使人想到《苦妓回忆录》中报社老记者幽默又张扬的想法:“活到九十岁这年,我想找个年少的处女,送自己一个充满疯狂爱欲的夜晚。”
而死亡的荒诞的、不可思议的来临,或对死亡的幽默恐惧,又总是与马尔克斯另一个重要的小说主题“孤独”如影随形。“孤独的幽灵始终追随着他”,马尔克斯曾表示“描写孤独的书”是他一生唯一的书。他曾提示:“请你注意,《枯枝败叶》中的核心人物一辈子就是在极端孤独中度过的,可谓是生于孤独,死于孤独。”
外祖父上校深刻地了解着大夫的孤独:“我感受到他生活中那间黑黝黝的、令人窒息的小屋中的苦恼。环境把他击败了,使他变得郁郁寡欢,惶惶不可终日。……我终于看透了他那迷宫般的孤独的秘密。”击败他的“环境”是什么呢?是香蕉公司带来的“枯枝败叶”,以及马孔多小镇自身的“枯枝败叶”化。
大夫在马孔多行医四年之久,终被香蕉公司开办的职工医院排挤,到了1907年,马孔多已经没有一个病人记得他了。“他分明已经开始意识到,自己在生活中吃了败仗”,然而却“找不到一个知心朋友,可以谈谈自己的憧憬或幻灭”,于是,“每到夜深人静,就能听到他像疯子一样在屋子里翻来覆去地折腾,仿佛在跟他过去的幽灵打交道。过去的他和现在的他进行着一场无声的战斗,过去的他在奋力保卫自己的性格:孤僻、坚毅不屈、说一不二;而现在的他一心一意地要摆脱过去的他。”他的孤僻与坚毅不屈,使他拒绝向香蕉公司屈服,办理一个“医生证明”,也拒绝向那些曾经抛弃和遗忘他的小镇之人再次伸出救助之手。只向曾帮助过他并从未遗弃他的上校,提出身后事的践约要求:“我只希望在我咽气的那天,您能往我身上盖一层薄土,免得兀鹫把我给吃了。”
马尔克斯曾指出:“孤独的反义词是团结。”而团结的反义词却是分裂、散乱,那是否意味着孤独是一种分裂与散乱。如此,像安提戈涅一样,一意孤行、逆全镇人意愿而为、坚持要为大夫送葬的上校,才会感到:“我似乎从漂浮在死者上方的空气中呼吸到一种苦涩的东西,那就是把马孔多引向毁灭的听天由命的气氛。”可怕的“枯枝败叶”,不仅是由外界而来的“一堆由其他地方的人类渣滓和物质垃圾组成杂乱、喧嚣的”物质,更在于小镇的人们内心中的那种随波逐流的状态,那些与优良传统相对立的观念:丧失传统道义,缺乏同情心,庸俗、势利等等。可以说,是上校,也是大夫,在自觉或不自觉中凭“至高无上的意志”在对抗人们内心的“枯枝败叶”。
而这种“枯枝败叶”的马孔多小镇或其他世界,充满危机并具有自我毁灭的能力,唯有堪与“孤独”对抗的“团结”,才能做到如其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所预言的:
“反转这个趋势,再乌托邦一次,还为时不晚。那将是一种全新的、颠覆性的生活方式:不会连如何死,都掌握在别人手里,爱真的存在,幸福真的可能,那些注定经受百年孤独的家族,也终于永远地享有了这大地上重生的机会。”
五、结语
马尔克斯曾坚称:“一般而言,一个作家只能写出一本书,不管这本书卷帙多么浩瀚,名目多么繁多。巴尔扎克、康拉德、梅尔维尔、卡夫卡都这样;自然,福克纳也不例外”,他也确实以其写作践行着这种坚持。于是,对其第一部小说的解读,便如此切实地感受到那些具有他的风格的故事。
【注释】
[1]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玛丽》(前言),王家湘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
[2]马尔克斯在自传《活着为了讲述》中写有:“二十七岁的我创作第一部小说《枯枝败叶》”,参见加西亚·马尔克斯:《活着为了讲述》,李静译,南海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40页。
[3]加西亚·马尔克斯:《活着为了讲述》,李静译,南海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339页
[4]加西亚·马尔克斯、P.A.门多萨:《番石榴飘香》,林一安译,南海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82页。
[5]同上,第103页。
[6]格非:《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归种子的道路》//邱华栋选编:《我与加西亚·马尔克斯》,,华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37页。
[7]加西亚·马尔克斯:《活着为了讲述》,李静译,南海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423页。
[8]林一安:《有感于成名之前博尔赫斯的遭遇》,《中华读书报》1999年9月2日。
[9]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的妹夫拒绝出版我的书》,朱景冬译,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MDc 5MTkwNQ%3D%3D&idx=1&mid=201715403&scene=20 &sn=251467b882f0ef49a5ba6bdb87a3bdc9,2016年8月26日。
[10]加西亚·马尔克斯、P.A.门多萨:《番石榴飘香》,林一安译,南海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69页。
[11]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黄锦炎、沈国正、陈泉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12]加西亚·马尔克斯、P.A.门多萨:《番石榴飘香》,林一安译,南海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59-60页。
[13]同上,第60页。
[14]同上,第55-56页。
[15]弗吉尼亚·伍尔夫:《现代小说》//《伍尔夫读书笔记》,黄梅、刘炳善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第118页。
[16]加西亚·马尔克斯:《枯枝败叶》,刘习良、笋季英译,南海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1页。
[17]同上,第144页。
[18]同上,第9页。
[19]同上,第72页。
[20]同上,第133页。
[21]同上,第21页。
[22]加西亚·马尔克斯:《枯枝败叶》,刘习良、笋季英译,南海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139页。
[23]同上,第10页。
[24]同上,第14页。
[25]同上,第25页。
[26]弗吉尼亚·伍尔夫:《达洛卫夫人》,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44-47页。
[27]加西亚·马尔克斯:《活着为了讲述》,李静译,南海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104页。
[28]加西亚·马尔克斯:《枯枝败叶》,刘习良、笋季英译,南海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3页。
[29]加西亚·马尔克斯:《活着为了讲述》,李静译,南海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104页。
[30]加西亚·马尔克斯:《活着为了讲述》,李静译,南海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16页。
[31]1982年,马尔克斯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的演说中称福克纳为“我的导师”(参见加西亚·马尔克斯:《拉丁美洲的孤独》//《我不是来演讲的》,李静译,南海出版公司2012年,第26页);甚至在与堂拉蒙会面时,他自称:“当时,能找到的‘迷惘的一代’作家的所有西班牙文译本我都读过,尤其是福克纳,我读得很细,好比用剃须刀一点点刮,谨防出血,就怕日后再读,发现他不过是一个敏锐的修辞学家。”(参见加西亚·马尔克斯:《活着为了讲述》,李静译,南海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102页)。
[32]加西亚·马尔克斯:《活着为了讲述》,李静译,南海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4页。
[33]同上,第391-392页。
[34]达索·萨尔迪瓦尔:《回归本源——加西亚马尔克斯传》,卞双城、胡真才译,外国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5页。
[35]加西亚·马尔克斯:《枯枝败叶》,刘习良、笋季英译,南海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36页。
[36]同上,第73页。
[37]同上,第118页。
[38]同上,第1页。
[39]同上,第3页。
[40]宋兆霖主编:《(1901-2013)诺贝尔文学奖全集》(下),北京燕山出版社2013年版,第974页。
[41]加西亚·马尔克斯:《霍乱时期的爱情》,杨玲译,南海出版公司2012年版,第16页。
[42]加西亚·马尔克斯:《苦妓回忆录》,轩乐译,南海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1页。
[43]加西亚·马尔克斯、P.A.门多萨:《番石榴飘香》,林一安译,南海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127页。
[44]同上,第68页。
[45]同上,第68页。
[46]加西亚·马尔克斯:《枯枝败叶》,刘习良、笋季英译,南海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97-98页。
[47]同上,第72页。
[48]加西亚·马尔克斯:《枯枝败叶》,刘习良、笋季英译,南海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84页。
[49]同上,第84页。
[50]同上,第137页。
[51]同上,第98页。
[52]《枯枝败叶》正文前引用了古希腊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中的一段台词,提示《枯枝败叶》对此剧的呼应:安提戈涅反抗克瑞翁王的禁令、安葬她哥哥,既是一种对亲情的尊重,也是对宗教信仰、对“神律”和道义的尊重。参见加西亚·马尔克斯:《枯枝败叶》,刘习良、笋季英译,南海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1页。
[53]加西亚·马尔克斯:《枯枝败叶》,刘习良、笋季英译,南海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132页。
[54]同上,第1页。
[55]加西亚·马尔克斯:《拉丁美洲的孤独》//《我不是来演讲的》,李静译,南海出版公司2012年,第26-27页
[56]加西亚·马尔克斯、P.A.门多萨:《番石榴飘香》,林一安译,南海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67页。
责任编辑:杨 林
(作者系云南民族大学副教授,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