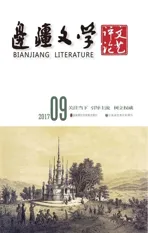没有救赎的“罪与罚”
——评夏天敏中篇小说《是谁埋了我》
2017-11-13唐诗奇
唐诗奇
新锐批评
没有救赎的“罪与罚”——评夏天敏中篇小说《是谁埋了我》
唐诗奇
·主持人语·
本期新锐批评所发三篇作品都是青年评论写作者,文章都较短,却显示出了批评的敏锐与坦诚。唐诗奇对老作家夏天敏的新作作出及时的评析,不仅看到了这一作品与这位前辈作家创作上的不同,指出其探索的意义,可见她对夏天敏过去的创作有充分的了解,有此基础才有批评深度的可能性;她还直言不讳地指出这部新作的缺憾,是平等对话的立场。一个初出茅庐者面对著名的前辈作家,有无平等对话的立场,是非常重要的。赵靖宏对居于香港的傣族作家禾素的散文作了较为全面的解读,让我们看到了远离故土的作家深厚的乡愁,牵起了香港文学与云南文学的一条红线。沈鹏对藏族作家永基卓玛小说的理解虽然写得简单了些,但不失为一个特殊的角度。对云南迪庆藏族文学的理解,我们也还处于相当初浅的程度,希望有更多的评论家参与其中。(宋家宏)
一
《是谁埋了我》是夏天敏最新的中篇小说,发表于《十月》2017年第四期卷首,引起一定的关注。该作讲述了一个被俘的解放军李水在成功逃脱之后无法释怀、不断寻求重生的故事。夏天敏把小说设定在建国之初的特殊历史背景下,把参军、剿匪、修水库这样的标志性事件杂糅在一起,又加入了被俘、造坟、驱邪等富有传奇性和神秘性的情节,使得小说既具有历史的厚重感,又富有阅读的趣味性,是夏天敏近年来不断探索、耕耘的成果。
夏天敏自80年代开始创作以来笔耕不辍,创作了大量的中短篇小说。他的小说多关注农村题材,多以昭通为背景来聚焦社会现实问题,以农民为主要描写对象,书写底层人民的苦难,有鲜明的批判精神和悲悯情怀。已出版散文集《情海放舟》,小说集《乡场上的皮匠》《乡村雕塑》《飞来的村庄》《绚丽的波斯菊》《窄窄的巷道》等。在之前的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第三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之作《好大一对羊》。《好大一对羊》为夏天敏的创作树起了一座高峰,长久以来,夏天敏的小说创作似乎与《好大一对羊》画起了等号。但夏天敏是一个有自觉艺术追求和实践的作家,长期以来对各种主义、流派的嬗变的了解与实践,让他对自己的写作有了更高的要求——回归到人和人物命运本身。《是谁埋了我》就是这样一部关注在大时代中个体命运的作品。
承接了以往的丰赡饱满的悲悯情怀和反思精神,《是谁埋了我》无论从思想深度还是艺术实践上都有了新的突破。在小说中,那种直截了当的道德批判被悬置起来,漫画式的夸张描写、符号化的人物与二元对立的叙事套路也退场了,取而代之的是历史、组织与个体的复杂关系,夏天敏把个体放置于特定的历史时期,更着重表现个体在时代和体制之下复杂、纠结的精神世界与命运浮沉。这是一个纠结且沉重的故事,如果说前期的作品还能给人“含泪的笑”的阅读体验,那么这篇小说则可以说是沉重的“罪与罚”。如同拉斯科尔尼科夫一样,李水内心也饱受着罪责的惩罚,但在信仰缺失的国度,李水始终没有得到救赎。
夏天敏曾说过,“沉重永远是我创作的一个主题。”从前,夏天敏小说的沉重感来自于对那些大山深处触目惊心的贫困的感同身受,他把所有的苦难的根源归于贫困,而对“贫困”的追问缺乏精神向度的开掘。在《是谁埋了我》中,他不再急于书写、忙于控诉,而是缓慢地讲述,仔细打磨细节,对人的精神状态与人在时代中的命运做出了自己的解读。从聚焦当下的社会问题到回归历史与人性,夏天敏的创作呈现出越来越深沉、扎实的特点。
小说的标题为《是谁埋了我》,这个“谁”在通篇小说的叙述中依旧悬而未决。“我”最先是被组织埋了,后来为了获得重生自己把自己埋了。所以小说中实际上建了三个“坟”:第一个是组织为“不在了”的李水建的“革命战士李水之墓”,第二个坟是李水自己在河边捏了个人形,为自己建了一个坟,第三个则是李水秘密地在心里建造的“坟”。在“是谁埋了我”的追问中,失落于时代的个体逐渐浮出水面。
二
新生的政权正在建立,为了巩固政权和维护人民生活的安定,李水随军进入乌蒙山,目的是剿灭乌蒙山腹地的一支强悍的土匪。然而在伏击土匪的过程中情报出了问题,反而受到土匪的袭击,解放军伤亡惨重,不得不撤退。在仓促的撤退中,无法顾及伤员。李水作为唯一活下来的人被土匪俘虏,与匪首之女桃花结下了一段孽缘,从此成为李水心中无法消除的阴影。即便他逃出匪窝,带队剿灭了这支土匪,立下大功,依然无法卸下心中的重负。与此同时,家乡人为被组织认定为“不在了”的李水建起了高高的坟墓。他的失踪被组织模糊地定义为“不在了”。这个“不在了”非常有意思,它既非生,亦非死,让人联想到同是云南作家的胡性能的小说《消失的祖父》。在历史中,人的生死与身份一样难以确认,充满着虚无和荒诞的意味。
李水活着回来了,灵魂却已经死去。为了寻求重生,李水用河滩上的泥捏造了一个自己,很庄重地把自己埋了进去,试图与过去告别。与其说是“自埋”,不如说是一种“自救”。这个极富仪式感的葬礼使得李水的重生之路显得滑稽而悲壮。然而李水的自救之路,无论是请道士作法驱邪,还是拼苦力去修水库,不但是徒劳,且反而成为他更大的包袱——正如卷首语所言,“受之有愧的荣誉,比不正当的感情,更加让人饱受折磨。”
李水一直在纠结中度过,纠结的过去使得他不断在当下陷入“疲软”状态。与桃花在一起的时候,因无法面对为救他而死去的班长而愧疚,与玲子在一起的时候,又总是被与桃花的那段阴影所纠缠。情欲是生命力的象征,李水情欲的无能为力象征着其生命力在这样的心理重压下一点点被磨耗殆尽。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是李水“自己”埋了自己,而前者的“自己”其实代表的是组织、体制或是意识形态,在这个“自己”的背后,依然是大时代在推波助澜,而后者的自己才是真正的个体。在小说中,组织一直都是以温情的面目示人,非但不追究他与桃花的过往,还对他委以重任,给予嘉奖。这就构成了一种荒诞,在个人与组织的对立中产生了微妙的张力——一方面,组织在精神上“绑架”了个体,使得个体饱受折磨和压迫;另一方面,个体隐瞒了组织,而组织却更加信任、宽恕个体。
当我们为“李水为何如此?”而感到不解时,我们必须反问一句:李水还能怎样?作为伴随着革命和政治运动出生成长的一代人,李水的潜意识里都被注入了英雄主义的革命因子,视死如归的荣誉感潜移默化形成了思想之网。忠诚与荣誉是他们最为看重的东西,虽然听起来虚无缥缈,但却实实在在地落在生活的每一处。李水的作茧自缚,其“茧”就来自这两方面。视死如归的荣誉感是支撑他们的信念和力量。“把荣誉看得比生命还重,他坚信为革命牺牲比啥都光荣,只要获得这个荣誉,他和家里会受到人们永远的敬仰和尊重。”这一点在妇女主任那里得到更实在的阐述:“人活着靠啥?就靠这脸面。”而对组织的绝对服从和绝对忠诚则是作为个体的必修课。“一听到组织这个词,李水的神经立即绷紧了。”“组织无时不在,组织无处不在,组织不是形式,组织是你的骨骼,是你的肌肉,是你的血管,更是你的灵魂。组织永远照亮你的灵魂,让你的内心藏不住任何东西。”组织无孔不入,就连李水的“私人问题”都被温暖地“照顾”到,在他吃下狗鞭的同时,他最后的隐秘空间也一并被吞下了。
所以,与桃花那段情感纠葛,让李水既失去了战死沙场的荣誉,又因隐瞒这段经历而失去了对组织的忠诚。在这双重丧失下,虽然李水活着回来了,但当“革命战士李水之墓”被刨除之时,那个英雄李水和“军属光荣”的荣誉就随之而亡,剩下的只是一个背负着秘密的“苟且”的躯壳。
三
夏天敏延续了一贯的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又加入了传奇性、神秘性和魔幻性的因素等因素,成就了自己的一套写作策略。现实与意愿的强烈反差是构成其作品艺术特色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种荒诞感使得作品形成一种内在的张力。正如《好大一只羊》中刘副专员“好心”与之造成的恶果形成反差,《左手,右手》中断指的疼痛和巨额赔偿的喜悦形成反差,《是谁埋了我》中,李水极想获得荣誉之时却被俘,使得愿望落空,然而当他不再追求荣誉而只想寻求内心的平静之时,荣誉却一再降临,让他不堪重负。这种反差让小说氤氲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无力感和荒诞感,构成了其小说的悲剧内核。
小说成功地塑造了李水这样一个极度纠结复杂的人物形象。他从一个视死如归、英勇无畏的解放军战士变成一个只有靠女人才能免遭一死的战俘,作者写出了他的挣扎、悔恨、愤怒和羞耻。从一心想寻死到向死而生,逃出匪窝,他强忍着与不爱的女人周旋,潜意识里为保护他而死去的班长血肉模糊的形象不时闪现,之后,死去的桃花怨念不甘的眼神又时常出现在李水的潜意识与梦境之中,让他内心备受煎熬,充分表现了人物内心的复杂、纠结的精神状态。小说中大篇幅的心理活动、梦境、幻想等现代性手法的尝试,对人物内心有了更深度的开掘,也营造出一种压抑、阴冷的氛围。其次,作者还善于用细节刻画人物,这也是李水这个形象之所以鲜活可感的重要因素。作者细致地捕捉到一个细节,李水为了实现逃跑哄着桃花进城,在城里遇到穿中山装和李宁装的人,他为了不暴露自己的心事,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羡慕,瞟一眼就坚决地转开脸。第二次是李水带军队剿灭了桃花所在的这股顽匪,看到躺在血泊里的桃花,李水内心很复杂,但怕被战友看到,也是只一瞥就迅速离开了。这个“瞥一眼”的细节让李水敏感、谨慎又有点小心机的性格跃然纸上,这也是李水“纠结”的个性原因所在,为李水整个精神的变化做出了充分的铺垫。
传奇性和魔幻性也是该作艺术上值得一提的地方。作为历史题材,土匪群体的传奇性书写已不是夏天敏的第一次尝试。此前,他就以土匪为主人公写过长篇小说《古镇遗梦》,刻画出朱玉婉这样一个敢爱敢恨、温柔坚毅的女性形象,显示出一种飒爽的英雄气概。从当下向历史深处的开掘似乎成为当代作家的一种集体性的转向,夏天敏近来的创作从关注当下的社会现实问题、底层和苦难转向对边地历史传奇的书写,试图用新的眼光重塑边地历史生活,《极地边城》《绚丽的波斯菊》《北方北方》和《古镇遗梦》都是如此,显示出作者对边地传奇的关注与重构历史的野心。而“驱邪”这样魔幻性的情节的加入,让小说更富有吸引力和叙述的张力。从显露魔怔到求助道士陈五先生驱鬼,再到削桃木女人烧成灰埋掉的过程,写得惊心动魄。当然,困扰李水的是心魔,并非桃花化身的“女鬼”,当李水最后全面爆发把埋葬桃木形女人的坑挫骨扬灰时,才终于在心底清除了魔障。李水那种纠结、害怕、小心翼翼的心理表现得非常丰富,氛围营造得鬼魅阴森,很见作者功力。
然而,当夏天敏放弃了得天独厚的底层叙事经验和对苦难、当下的关注之后,这种带有传奇色彩的历史演绎总感觉缺了点什么。那种从《好大一只羊》《左手,右手》《接吻长安街》等优秀之作中流露出来的切肤之痛消失了,反而陷入了一种故事化的写作之中。当我们抛开作品的立意,回望整个小说的故事情节时就会发现,这实在是一个意料之中的故事,在这样一个颇具阐释意味的标题之下,读者的期待视野随着故事的开展落空了,构思和艺术上的薄弱之处开始显露出来:俗套的土匪的女儿突然爱上“我”的戏码;一个伏击了解放军一整个小分队的穷凶极恶的匪首不敢对李水用刑,竟然是因对方是解放军,怕以后死无葬身之地;李水千方百计来到城里,在寻求部队救援时被误伤,“感到身上中了几枪”却依然活了下来,而寻求救援的岗哨刚好是他所在的部队,就如夏天敏自己在文中写道的那样,“就跟烂熟的电视剧一样”,太多的巧合显示出故事的刻意经营。在人物塑造上也落入了俗套,除了李水之外,人物均显得概念化。匪首的目光必然是“透露出阴鸷和狡黠”,土匪的女儿必然是既心狠手辣又温柔多情的,自己心上人就是羞怯温顺……这种概念化的人物,似乎仅仅是为了推动故事发展而存在,从而皆削弱了小说的艺术性,极易让读者丧失研读小说、探究小说主题意蕴的机会。与有着切肤之痛的乡村题材苦难叙事相比,夏天敏仔历史题材的把握和书写上显得有点力不从心。
虽然艺术处理上略有欠缺,但总体上来说,《是谁埋了我》仍不失为一篇值得一读的中篇小说。它是夏天敏近年来创作转向的一个窗口,我们可以从中窥探夏天敏在无论是题材、主题还是表现手法上的开拓和创新。我们期待夏天敏在历史题材的写作中,更进一步地把握人性及人在时代中的命运沉浮,写出更优秀的边地小说。当然,笔者更期待的是,在当下“三农问题”“城乡问题”“扶贫攻坚”等社会问题日渐白热的今天,有更复杂的问题、更荒诞的现象值得去关注、去书写,夏天敏依然能坚守这块阵地。毕竟,能在历史的天空中展开想象力之翅的作家很多,但能对苦难有真正体察和悲悯的作家太少,希望作者不要放弃底层与苦难写作,从历史长河中回顾当下,写出新时期的疼痛与坚守。
责任编辑:臧子逸
(作者系云南大学文学院2016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