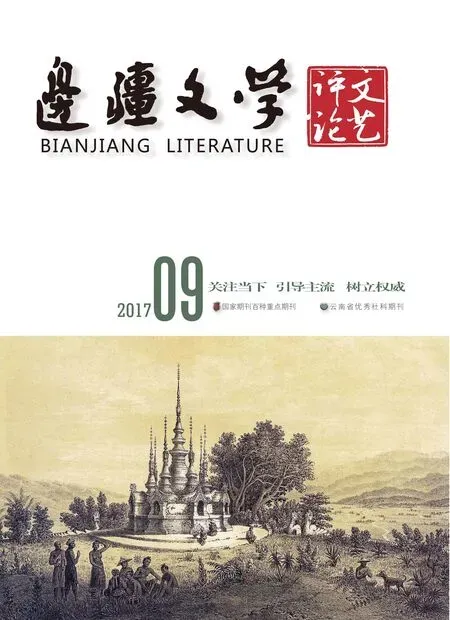小地方文学史的可能与向度
——冉隆中和《昭通文学三十年》
2017-11-13汪舒
汪 舒
小地方文学史的可能与向度——冉隆中和《昭通文学三十年》
汪 舒
我只爱我寄宿的云南,因为其他省我都不爱/我只爱云南的昭通市,因为其他市我都不爱/我只爱昭通市的土城乡,因为其他乡我都不爱/我的爱狭隘、偏执,像针尖上的蜂蜜,假如有一天我再不能继续下去,我会只爱我的亲人/——这逐渐缩小的过程,耗尽了我的青春和悲悯
某日下午,云南昭通。凤凰山麓,昭通文艺家创作中心。冉隆中作题为《地方文学史的可能和困难——以昭通为例》专题讲座,向参加云南省第二届文艺评论高级研修班学员讲述《昭通文学三十年》成书经历时,引用了诗人雷平阳诗歌《亲人》,表达自己与文学史的关系,“对文学史的关注由大到小”。冉隆中与当代地域文学史纠结了30年。首次卷入文学史写作,是参与编撰《新中国文学发展史》,冉隆中是该书主要撰稿人之一。这本后来成为若干高校使用多年的教科书,逼使冉隆中细读了众多当代文学精品。到后来写作《云南当代文学简史》(原书名《流淌过往的文学时光》)《昆明新时期文学史》(原书名《红土高原的回声》),冉隆中对文学历史和地域的关系有了越来越深入的认识把握。直到今天的《昭通文学三十年》,从地域上看,冉隆中对文学史的关注,事实上如《亲人》诗句,是一个逐渐缩小的过程。
“秉笔直书”的职业标准和“曲意迎逢”的道德问题,考量着文学史书写者的选择。
大概在十年前或者更为早些时间,冉隆中在写作《底层文学真相报告》时,选择昭通几个作家及其作品进行了分析,包括孙世祥、樊忠慰、雷平阳,朗生等,也包括了对昭通底层作者的关注。这个被命名为“田野调查式评论写作”进行到一定程度时,作为一个身体和心灵同时抵达现场的批评写作者,冉隆中开始思考:能否由点到面进行关注,解剖一个地区文学发展历史与现状——他将目光锁定了云南当代文学重镇昭通。
《昭通文学三十年》付印之时,冉隆中希望将该书作为“2013年,我对文学做了什么事”的回答,“我们的文学面对很多困难和困惑,但我们要寻找它生长的可能。”这是一名长期关注底层文学生态状况的批评家的言说方式。
地方文学史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地方建立在一种参照系中,国家由若干地方叠加而成,有文学生长的地方都可能书写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史的书写通常是史官责任之一。“秉笔直书”是一个职业标准,忠实自己的所见所思,把它真实准确地记录下来。“曲意迎逢”是一个道德问题,也是一个能力问题,没有认知的区分和能力仍然做不好。
“这考验我们的选择,怎么书写好一个地方的文学史。”冉隆中告诉记者。
回溯到1989年,昆明市文联组成“昆明作家徒步金沙江采访团”来到昭通金沙江一带,参与者仅黎泉、邹长铭、马宝康、袁佑学、徐刚几个人。这次采访的始作俑者是其中的昭通本土作家邹长铭,由他引发的昆明作家金沙江之行,被评论家冉隆中在《文艺报》发文,命名为名噪一时的“金沙江文学现象”,而写金沙江的文学作品上了《收获》等高端杂志。今天看来,这颇有行为艺术意味的作家采风,为昭通文学之火添了一把柴,因此有了今天的蔚为大观。1999年,文学刊物《大家》杂志在“文学调查”栏目发表了雷平阳的《群峰之上的夏天——云南昭通文学现象调查》一文,首次提出“昭通作家群”和“昭通文学现象”的概念,开始在文学界引起反响。
这一段历史在冉隆中进行田野式调查时引起思考:被边缘化的昭通,为什么有那么多丰富优质的文学资源?1980年代前,东川、个旧是云南文学重镇,而当时的昭通文学还是一片沉寂。但到1980年代中期,昭通文学开始萌动,呈现出后发趋势。当云南文学以边疆的奇风异俗受到关注,满足猎奇的眼光而最终被抛弃时,昭通写作者与其说不知道这一切,不如说确实不具备这些便利。他们放弃了追寻云南文学当时的主潮,放弃了边疆奇风异俗的写作题材,将目光收回到脚下这片土地,看到的是苦难现实,不需要叙述别人的故事,只需要重述自己的经历,因此,昭通文学在发轫之初,就有了一个被动的惊人转身。
通过对若干点的透视,再到面上进行田野式考察和资料汇集,对现象进行分析和整理,这种方式接近于文学史的写作。
毫无疑问,《昭通文学三十年》是云南第一本对一个非省份城市、边远地域文学现象进行全面梳理、总结的文学史书,其作用在于回顾、展示和检阅。
当年,冉隆中和他的写作团队在昭通文艺家创作中心谋划该书时,无论结构、形式和内容,都比现在的成书更为宏大而全面。
首先考虑要有什么内容,由什么作品来呈现,各自文体、各个层次的代表人物和作品有什么?参加各级作协的有哪些人?被国内主要刊物转载和评论过的有哪些?重要奖项有哪些?这些都需要尽可能全面地呈现出来。
一些调查,看似远离文学本身。比如,作家的经济收入来源及生活状况。但这些调查发现了昭通文学的一些重要元素,昭通人重精神生活,即便贫困潦倒的人依然如此,因此可以说昭通文学自有其深厚的人文基础。这种被称为田野式调查的方式还包括了对报刊亭的调查,冉隆中发现,《收获》、《十月》两本大型文学刊物,在昆明的一些报刊亭早已经看不到了,但昭通的一些报刊亭,一处就可以卖出十多本。
“有了田野式调查和样本分析的基础,再进入作家作品解读时,要考虑哪些人的作品能进入。”冉隆中介绍。
首先是主流社会的评价标准,比如获得重大奖项,或具有重大影响力,但这不是唯一。昭通文学一言难尽,有的没有获奖,但有存在的意义,我们要有这样的预测和前瞻。比如孙世祥的《神史》摆在重要位置——论述昭通长篇小说的第一篇章,就是基于这样的考量。《神史》是昭通的,云南的,可能将来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有一席之地。还有樊忠慰,虽然只是主要获得过云南民间的王中文化奖,但他身上体现出来的诗人的高贵品质,让他完全活在自己的诗歌氛围中,那些充满杂质的人间烟火与他毫无联系,他的诗作非常干净纯粹天真,在今天的社会已属凤毛麟角。
“既要有一把主要的尺子,也要有多把修正的尺子,才能体现昭通文学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作为主编,冉隆中把握着编辑工作的方向。《昭通文学三十年》有关夏天敏和雷平阳的部分,以专门的“作家论”、用几万字篇幅来进行专章描述,一个以中篇小说为代表,一个以诗歌为代表,分别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中篇小说奖和诗歌奖,他们同时具有各自领域的代表性。
昭通在经济版图上是后发地区,较长时期以来,因贫穷匮乏而导致的各种社会矛盾尖锐突出。作家可以绕开这一现实,但昭通作家敢于直面“淋漓的鲜血和惨淡的人生”,这与昭通作家敢于突破自身的困厄和时代某些禁忌有关。冉隆中认为,这种突破的最大受益者,其实就是昭通作家中最突出的代表者夏天敏和雷平阳。
“云南文坛非常热闹的时候,昭通却很寂寞。但昭通呈现出的独立性、多样性,比较早切入文学规律,可以这样说,昭通二三流的作家放在某些其他地方都是一流的,这与昭通作家较早回归文学本质有关。”冉隆中这样理解昭通文学。
实际上,《昭通文学三十年》编撰还是传统的断代、分类。按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影视)、文艺评论等进行了分类,还适当加入带有时代特性的非虚构文体。
2011年,《云南文艺评论》刊发了《昭通文学三十年》研究提纲,就引起其他州市对编写地方文学史的兴趣。
出版该书的云南人民出版社也看好《昭通文学三十年》。他们将在即将到来的新一年北京图书订货会,重点推出该书。
《昭通文学三十年》未交付印刷前,冉隆中总是经常将样书带在身上随时修改。一次参加省委领导联系专家考察,该团中昭通有两位专家,一个是农学方面的,一个是医学方面的,他们在冉隆中手中看见了这本书,对冉隆中说:“我们都有一段文学青年的梦,但昭通文学是什么,我们很想知道。”
即便对于文学局外人,也不难看出,《昭通文学三十年》的写作团队,通过对若干点的透视,再到面上进行田野式考察以及资料汇集,最后对现象进行分析和整理,呈现在他们眼前的,已经是一部比较完整全面的昭通文学史。
一本书的容量是有限的,犹如国画一样,需要适当留白。这些留白的部分,就交给后来的人吧。
“我主编的《昭通文学三十年》,并非都由我来写,我只是提供一种思路,不是个人的东西,而是一个团队的价值取向。”冉隆中对自己的角色定位并不妨碍他对一个地方文学史的深层次思考。
其实地域文学经验也可以上升到国家层面去分析研判。昭通文学经验就有若干侧面具有这样的品相和价值。比如昭通文学呈现出的经济和文学发展不平衡规律比较突出,经济发展与文学发展在很长时期里是不对称的,这是为什么?对变化过程和轨迹进行描述,可能会更真切地发现和把握昭通作家的精神向度。冉隆中发现,昭通作家在总体上对文学的追求变得非常纯粹,除了自己坚持的美学标准之外,并无更多别的价值诉求。第二次出样书时,他真切体会到,昭通文学确实已经上升到一个品牌高度,因此,他果断地拿掉了已经成书的数万字内容。
在冉隆中看来,任何品牌都是日积月累的打造,不是广告,是心血的凝结,品牌形成后,品牌的维护到了一个严苛的程度,对品牌背后存在的瑕疵,不适宜在一部以展示和检阅为主的史书中去大声议论。
2012年,《文学报》刊发《昭通作家群的困境与局限》一文,提出昭通文学的发展需要挤去“数量”泡沫,而不是进一步去发酵这个“数量”泡沫,建议昭通作家群必须形成一股中坚力量,“以一当十”,甚至“以一当百”“以一当千”。该文同时提出昭通作家群缺少批评风气,容不下正常的批评火药味。
这其实是原计划出现在《昭通文学三十年》中的一小部分,刊发后引起轩然大波,不同的声音导致这一章节撤稿,并不得不对《昭通文学三十年》做了重大调整,凡是涉及作家作品缺陷的批评,到成书时,都放弃了。
这本是一种完美主义的表达,有好说好,有坏说坏,但出于对品牌维护的考量和设身处地的换位思考,冉隆中最终作出这种选择。冉隆中认为,文学史需要传递正价值,“我们不是没有看见缺陷,而是我们放弃了在这本书里的表达。我想,也许在别的时候,用别的方式,来探讨这个问题会更恰当。”当向世人推荐昭通文学这个品牌时,冉隆中现在总是选择那些最具亮色的点和片段,使用最具热情的词汇。“我在内心里接受了这个理解和想法。其次,我们团队中其他几个是昭通本土人,他们要面对被书写者。即使这样,也有可能出现批评和质疑的声音。我不希望他们在这样的生态圈子里变得复杂和艰难,我们要做的是对地域文学促进性的工作,所作出的调整,是每个人都说服了自己的缘故。”
其实,早在《昭通文学三十年》最初的构想里,包括了对存在的问题和困境作反思追问,并将给出适当的判断。也想通过同题材作品的比较研究,在多向度的比较中,看出昭通文学艺术价值,将其上升成中国乡土文学经验的一个矢量。但冉隆中的团队在调查过程中,发现有些地方力不从心,有的地方又显得好高骛远。“团队工作是妥协和谅解的产物,《昭通文学三十年》最后呈现的就是这样的结果。”
对昭通文学上升到一个品牌的理解和认知,冉隆中做了个比喻,这好比为一部书写序,会发现若干破绽,但不会一一点破,通常是去找亮点和优点,归纳后推荐给读者。如果一开始就批评得体无完肤,这并非是序的写法。
显然,昭通文学成为一个品牌,写作文学史就成了这个品牌的推广者和维护者,文学史这种文体和写作对象成就和限定了这种选择,其中有苦衷,有选择,有坚持,有妥协,有换位思考。“一本书的容量是有限的,犹如传统国画一样,需要适当留白。这些留白的部分,就交给后来的人吧。”冉隆中说。
责任编辑:臧子逸
(作者系昭通日报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