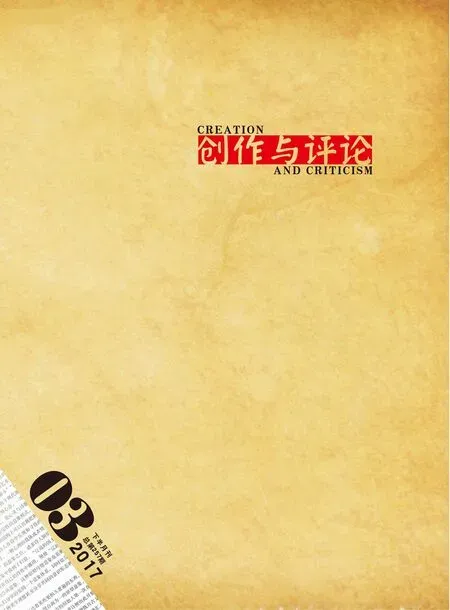伶俐的自然与无言的身体
——评电影《老井》
2017-11-13章文哲
○章文哲
伶俐的自然与无言的身体——评电影《老井》
○章文哲
影片《老井》改编自郑义的同名小说,围绕孙旺泉、赵巧英和段喜凤三人的情感纠葛,讲述了老井村村民祖祖辈辈寻井、挖井和求水的故事。该片荣获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最佳男演员等诸多荣誉。影片的成功,奠定了吴天明导演在海内外的声誉;片中所流露出来的古典主义审美倾向,为导演在创作风格上的创新与观念上的破格提供了新的出路和策略。“古典主义” (Classicism)多指西方艺术史中17世纪欧洲艺术对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艺术范式之模仿与复兴,强调对古希腊艺术中的节制、理性、和谐、尊崇自然等元素的复兴。其后的“新古典主义”风格发生在18世纪,其宗旨也是复兴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艺术精神。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更多的是针对洛可可艺术中滋生出来的封建皇权,指责并嘲弄浮华、堕落的艺术范式。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古典主义”创作风格在二十世纪一度被马克思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浪潮所遮蔽。这一趋势也可从电影的发展史中窥探一二。八十年代是中国激情燃烧的岁月,电影界同仁们从十年沉睡中苏醒,如饥似渴的吸取西方电影理论,特别是巴赞的现实主义理论之甘露。在“电影与戏剧离婚”“电影语言现代化”的浪潮下,中国电影理论建设迈出了影像本体层面探讨的坚定步伐;创作方面,西有“中国西部片”,东有“谢晋模式大讨论”,蔚为壮观。曾经被误判的前辈们得以平反,钟惦棐先生重新执笔,再论“票房价值”,又敲“电影锣鼓”。我们常用“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来概括那个年代的电影主潮,而较少关注文本创作的审美观念。
吴天明曾任西影厂厂长,拍出了《没有航标的河流》《人生》《变脸》《首席执行官》和《百鸟朝凤》等影片。天明导演也是一位伯乐,他大胆提携当时的年轻人(第五代),给予他们自由的创作空间;他重视电影理论工作,对理论界的声音兼容并蓄。在《老井》筹备过程中,还曾在钟惦棐先生家中组织理论会谈,树剧本创作之初,先向理论请教之先例。并且,在创作过程中注重合作、尊重人才。影片用老井村打井石碑的方式作为结局,便是吴天明在百般犹豫之下,采纳了张艺谋的建议。用节制、隐忍和静默的方式,在影片的情节高涨处“硬”收尾。影片的成功与天明导演创作观念中的古典审美倾向不无关系。
“古典主义”之核心为崇尚自然、敬畏理性和效仿古典。电影艺术的多元性给予了它超越自身历史的可能性。有趣的是,将公元后至今两千余年的艺术发展史与百余年的电影发展史做一个数学上的类比,会发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世界电影与西方十六、七世纪古典主义艺术时期对应各自发展史时间轴的比例是相似的,即五分之四处。而八十年代的中国电影同样也处于新老交替、推陈出新之历史时期。天明导演的《老井》便是当时光彩夺目的一颗启明星。影片通过编织一幅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之西部风貌作为其叙事时空;故事结构极其讲究规范,情节点的设置、情节线的安排以及人物性格刻画都遵循节制、理性和均衡的古典美学风格;影片主题不仅折射出导演自身的集体无意识,同时,也承载着具有普遍性的大众价值认知。上述特征,皆可看作是中国电影中“古典主义”审美之闪耀。
一、伶俐的自然:古典主义叙事与主题
梁实秋先生曾提到:“一部小说必定要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必要是合乎人情的,必要有起有讫,有变化有结果,有艺术的安排,有单纯的效力。”古典主义的叙事风格,讲究在“真实”的基础上追求整体情节的“排兵布阵”。与好莱坞的三段式叙事范式不同,古典风格的叙事策略讲究适宜、节制、充满韵律且情理交融。中国的民族电影大都延续着“戏”的内核,这是中西叙事类影片在叙事策略上的一大差异,也是学院派影片常用的叙事风格。如果说类型片对故事建置、冲突、高潮等环节有着严苛的追求是一种现代工业生产的范本;那古典风格的电影叙事系统则如同百年老字号的手工坊,精雕细琢,温柔敦厚。两种风格并无高下之分,只是后者对中国传统古典主义审美的承载能力更胜一筹。
小说《老井》提供了一个好故事,影片在此基础上理出了两条情节线,贯之以线性叙事结构。旺泉、巧英和喜凤之间的情感纠葛与老井村千百年来的打井史互为交织,很自然的将人的命运与人所生活其中的广袤土地联系起来。在故事的安排上,便奠定了全片的磅礴气势。这是定基调的一笔,吴天明导演在此前的《人生》和之后的《变脸》和《百鸟朝凤》中都延续着这一模式。人物的命运离不开自然的束缚,在情节上表现为人物纠葛情节线的推进多用自然大背景中的冲突来蓄力。片头旺泉和巧英给村中打井队送水,这是巧英在片中第一次和旺泉的父亲富贵叔见面。看似不经意的一场戏,实则暗藏着旺泉和巧英两人情感危机的种子。富贵叔精疲力尽靠在井边,他并非对旺泉和巧英的懵懂情愫不知情,而是打井的艰苦生活让他无心多想。紧接着一场戏则是旺泉的父辈在讨论入赘事宜,而两场戏之间的衔接是一个俯拍的大远景,旺泉和巧英两人挑着空扁担,走向远方。这是影片中少有的远景镜头,用在开场仅十分半钟之处,早早的为他们两人的爱情悲剧埋下伏笔。其后旺泉和巧英感情虽遭遇“入赘危机”,但他们也用私奔予以回应。然而,情感纠葛并非本片主线,二十三分处富贵挖井遇难,彻底打消了旺泉内心残存的浪漫主义,他(同时也是观众)开始意识到,爱情的绊脚石并非是“第三者”喜凤的一厢情愿,而是压在老井村村民心中几百年来的氏族责任。
影片的两条叙事线皆有强大的思想力量和戏剧动力,且都可独立成篇。但是导演却用克制、温婉的审美思想将其黏合起来,构成了影片叙事风格上的古典主义特征。为了遵循父亲生前的遗愿,旺泉无奈之下入赘到喜凤家。影片的两条叙事线此时的主要矛盾转变为,巧英对旺泉背叛爱情的无声指责与老井村打井计划的搁置。当旺泉和喜凤第一次真正同房行夫妻之实后,旺泉主动起床端尿盆。叠印在窗户上的喜字似乎告诉观众,旺泉在爱情和生活中做出了妥协。观众此刻最关心的是巧英和旺泉将何去何从。导演的冷峻和克制则体现在用看似被动回避,实则主动出击的情节布局,化解观众对人物爱情纠葛的观影欲望。老井村村民得知邻村的老乡们非但独占了原本属于他们的一口古井,还出于私欲恶意填井。一场械斗随之发生。这样一来,小情小爱在家族荣誉面前便显得微不足道了。因此,在观影过程中,观众的期待总是先于影片的情节进展,无形之中便实现了好莱坞类型片所追求的大密度、高强度的叙事节奏。《老井》的这一叙事模式并不逊色于后者的紧张激烈;反而,它能在讲好一个故事的基础上,承载起比类型片更多的民族元素。
梁漱溟曾指出中国是伦理本位之社会,“家”的观念优于其他;而西方则是权利与义务之世界,“人”之间的关系最为重要。仅从开场便能明显看出《老井》的叙事策略与好莱坞类型片建置阶段的差异,即前者强调用历史的视角来写人物命运,人很难超出时代而存活;后者着力于人与人之对抗,因此凸显人物的核心动机和因利益、信仰、情感冲突而存在的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人类对故事的需求是亘古不变的,因此也造就了好莱坞的全球霸权局面。然而,艺术对人类命运的探索则困难很多。《老井》温柔敦厚、中和谐美的叙事范式恰恰与西北大地的冷峻干裂、朴实诚毅互为映照,叙事节奏上的跌宕也如水滴激起的涟漪带动着全片的气氛。旺泉从学习班学成返乡后,影片的叙事节奏发生了变调。原本紧张、规律的叙事范式不复存在,转而变为侧重描绘自然的抒情段落。村支书在旺泉和巧英面前掏心窝子,立誓要为全村人打出一眼井来。旺泉和巧英在找水定井为的途中,互表衷肠,延绵起伏的山脉就如同两人心中荡漾的情愫。影片中旺泉和巧英独处的段落大多在室外,不论是试验电视机失败的归途面朝山底的呐喊、挑着扁担行走在碎石小路和私奔前夕休憩的破屋残垣,还是勘探井位时穿行其间的悬崖断壁,大景别通常对应较长的镜头时间。形式上的改变,自然带来了情绪上的放缓。导演依托外景、自然风光,将旺泉和巧英的情感纠葛置于更广袤的时空中,表面上看,延续了全片冷静、节制和大音希声之叙事美学;其内里则是导演自觉或不自觉的古典主义叙事风格的体现。朱光潜先生曾指出“古典作品之所以得到普遍的赞赏,也就因为它们抓住了普遍的东西;而我们应向古人学习怎样观察自然和处理自然。”在《老井》的影像风格上,天明导演延续了其在叙事策略中的古典美学探索。
二、无言的身体:人物造型与观念范式
西方艺术中的很多雕塑作品也是通过表现人体肌肉、骨骼的和谐美、力量美和健康美来承载艺术家的主观表意。藏于德国慕尼黑州立文物博物馆古雕塑馆的“希腊埃伊纳岛爱法伊娥神庙东山墙的倒伏武士”(约公元前500至前480年)以及藏于希腊雅典国立考古博物馆的“阿提卡的啊纳维索斯”雕塑(约公元前530年)是古希腊早期古典美学风格的代表。两座雕像皆注重人体骨骼和肌肉比例的塑造,并且线条简洁有力、躯干挺拔、刻画精细。相较之下,文艺复兴盛期米开朗琪罗的“摩西”雕塑(藏于罗马戴锁链的圣彼得堡教堂,儒略二世教皇墓)则更为圆润、华彩四溢。该作品想表达的是摩西对自己的人民祭拜金牛犊时的忿怒之情。而雕塑中摩西的卷发、胡须和腿上的服饰遮盖了其健壮的肢体,他微微侧目,右前臂夹着《摩西五经》,光滑的衣角和逸动的胡须让其看起来肃穆而威严。对比前文提及的旺泉造型风格,不禁赞叹天明导演在选角时的独到与精准。张艺谋身体的地缘亲近性,让他从导演跨界到演员并饰演男一号时游刃有余。
电影的人物造型和人像雕塑在某些地方是类似的。《老井》中旺泉数次赤裸上身,开篇高光比、强反差之中的男性臂膀,在铿锵有力的打击声中流露出鲜明的古典美学风格。崇尚力量、朴素健康、坚毅粗糙,既是旺泉敲击铁钉的外在形象美;同时也是一种情节上的隐喻,和片尾老井村打井英雄史诗相呼应。旺泉的赤裸上身造型还承担着人物心理造型的功能。在旺泉和巧英给打井队挑水的途中,旺泉率真的脱下上衣擦拭身体,这是两个年轻人的亲热期,也是旺泉赤裸的身体第一次正面出现在荧幕上。随后两次旺泉赤裸上身的镜头,则是在和喜凤同眠共枕之时。第一次,是茫然无措的,他还没从“被入赘”和失恋的忧愁中走出来,面对以泪洗面的喜凤,他手足无措,只能用被子裹紧身体,刻意和她保持距离;第二次则是不忍心喜凤再被自己冷落,侧身挤进喜凤的被褥;第三次,是在他经历了坠井事件和“婆媳矛盾”后,终于接纳了喜凤。但遗憾的是,他与喜凤依然是侧面相对,留给喜凤(同时也是展现在观众面前)的依旧是不完整的身体。旺泉最后一次在银幕上赤裸上身是在塌方的井下,他和巧英相互依偎。厚黑健硕的肌体上占满了岩灰和泥浆的混合物,在危难之中,他们的情感终于爆发。憋闷的井底构成了暂时性的封闭空间,而旺泉的身体再一次正面出现在巧英和观众面前。有趣的是,旺泉和巧英在井底忘情拥吻所对应的叠印镜头是延绵不绝的山脉,并配以恢弘的人声合奏;而更早之前,旺泉勉强与喜凤云雨之时,所出现的叠印画面是双喜红窗花,配音也是更为幽转回绕的笛声。前者是情到深处的自然流露,后者则是礼仪教化的规训。天明导演并未就孰好孰坏给予提示和评价,而是通过展现人物的肢体美,由此实现一种“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古典审美。
在影片的观念设计上,《老井》较之《人生》更能体现出理性、平和、节制与适度的古典审美意味。《人生》侧重于赞美巧珍的善良淳朴,歌颂她对爱情的忠贞,却忽略了对她身上的封建局限。《老井》的立意更客观,高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范式。真实感已不是影片的终极目标,尊重自然、推崇理性则是它的特点。尊重自然之处体现为,将每一个人物的命运置于历史生活中思考,时空上的局限性将每一个人串联起来,牵一发而动全身。旺泉私奔未果,却经历丧父之痛;喜凤终获泉子“芳心”,岂料发生塌方,丈夫和情敌同时禁锢井底。而推崇“理性”则体现在影片的美术造型上。隐喻和象征性的段落借现实主义的外衣,不露声色的将导演的批判思想缝合于故事文本中。中国民间习俗中,一般是在给年过八旬无疾而终的老人喜丧中才能使用红棺材。影片中的富贵显然不符合要求,硕大的棺材摆在旺泉家中,后人们跪拜逝者,镜头叠化出一轮红日。红棺材和井绳上的红花结、角色的红衣服、家中的红衣柜都是看似写实,实则写意。旺泉去喜凤家帮忙打石槽,目的是让女方家更好的了解他。这一段落既是当地民俗的真实体现,也具备西西弗斯神话般的象征意味。另一处类似的象征段落是片尾,村支书组织全村人集会,为了继续打井而募捐。年轻后生们言辞轻薄,质疑这次募捐打井又将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就写咱流血牺牲、弃粮捐款、艰苦奋斗。给咱村,又杵了个机械化的黑窟窿”。他们把反复劳作改变命运视为笑谈,只有旺泉神情严肃。因此,也只有在他身上能折射出西西弗斯式的悲壮。
时至当下,中国电影正处于风云际会之时。票房成绩屡破记录、电影新人纷纷亮相、行业模式逐渐规范,新世纪的中国电影热闹纷繁;但同时,中国电影也危机四伏,资本乱象、创作断层、媒介革新,林林种种皆为双刃剑,迫使国产片在新世纪不断转型。如何在错综复杂的市场环境中找到中国电影的位置,是当下青年电影人亟需思考的问题。毕赣的《路边野餐》之所以能打动金马奖评委,除了叙事时空上的藻饰和影像语言上的新鲜感外,导演自身的乡土性、地缘性和由此折射出来的民族根系恰恰是其更为动人之处。而像宁浩的“疯狂三部曲”,杨庆的《夜店》与《火锅英雄》等作者化的类型片道路,则是目前青年导演普遍采取的创作策略。随着中国电影工业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老生常谈的二元悖论又重新成为了热点话题,艺术与商业、质量与数量、票房与口碑再度困扰新世纪的中国电影。然而,电影工业真正的成熟并非是资本牵着创作的鼻子走,抑或资本与创作绝缘,而是各司其职。我们似乎可以将目光转移到人物命运与时代变革、审美观念与消费元素、作者风格与类型破格等创作领域,重新思考并定位独属于自身的创作观念。在可预见的未来,“艺术中的人”和“人的艺术”依旧会是艺术所关注的主要对象。《老井》的屹立不倒颇为重要,它是中国电影拓荒征程中的一眼清泉,潺潺流动,滋养着无数晚辈;也是一把标尺,明晰且温柔的立下诸多民族电影范式;其如岩壁画般的影像,隐秘而敦厚,传唱着西北大地上数千年的民族史诗。
注释:
①梁实秋:《人生几度秋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7页。
②朱光潜:《法国新古典主义的美学思想》,《北京大学学报》1962年第1期。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