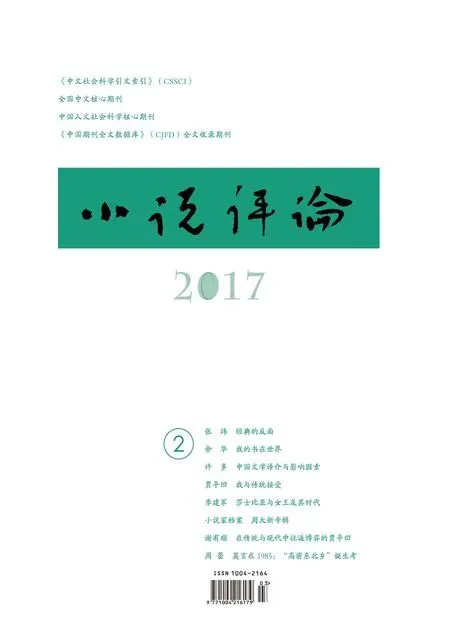贾平凹近期小说的空间转向
2017-11-13乔艳
乔 艳
贾平凹近期小说的空间转向
乔 艳
在《极花》“后记”中,贾平凹将自己的写作与水墨画作比,“我一直以为我的写作与水墨画有关,以水墨而文学,文学是水墨的。”这似乎涉及了一个古老的话题,即“诗与画”的关系。作为我国当代文学的重要代表,贾平凹的写作始终关注现实,尤其是农村的社会问题和巨大变革,同时他也在考虑文学的现代意识,思考如何为世界文学带来“特殊的声响和色彩”。在小说形式上,从明清文字的轻灵秀丽,到西汉品格的海风山骨,他一直在不断地尝试。然而,相较小说的现实题材,贾平凹在写法上的探索和文体形式的革新却很少得到关注。在他近年来的作品——《带灯》(2013)《老生》(2014)以及最新的《极花》(2016)中,作者有意识地加强了对小说形式的探索,表现为打破线性叙事逻辑,淡化故事时间,以及多种文体的杂糅等,从而使上述作品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叙事特征。
一
时间与空间是文学发展的两个重要维度,而“任何一种维度的获得是与在其他维度上的失去相称的”,贾平凹近期作品的空间转向,首先表现在对时间的处理上,通过淡化故事时间,打断事件发展的自然进程,并以多种形式“扭曲”时间,从而实现了小说形式的空间化。
在较早的作品如《古炉》中,已经可以见出时间的停滞,空间感初步呈现。在随后写作的《带灯》中,对时间的模糊和淡化进一步加强。小说始终未介绍故事时间,仅在开头点出“开发的年代”,其它部分则付阙如。带灯从初来樱镇的小干事,到综治办主任,再到最后被撤职,时间一直在流逝,但读者并不知道她的真实年龄,她在樱镇的工作时间,以及整个故事的时间跨度。在小说中,情节发展主要不是依靠时间推动,而代之以空间的不断转换。作为镇政府综治办主任,带灯的主要工作是处理各类上访事件以及各村寨矛盾纠纷,因此,她需要不断来往于镇政府和各村寨之间,空间的不断转换成为推动小说前进的主要叙事动力。《极花》以对时间的记录开始,“那个傍晚,在窑壁上刻下第一百七十八条道儿,乌鸦叽哩咵嚓往下拉屎,顺子爹死了,我就认识了老老爷。”此后,小说中反复出现“在窑壁上刻下新的道儿”“指甲在窑壁上的刻道儿还在继续”等内容,被拐卖并囚禁的胡蝶失去了对时间的感知,只能以空间的形式来记录时间,而时间也无法成为推动叙事的力量,《极花》的叙述更多遵循了胡蝶的心理逻辑,其中的时间则是模糊和混乱的。由此,通过对时间的淡化处理,使空间成为时间的标志,以空间变化推动时间进程,贾平凹近期小说表现出鲜明的空间叙事特征。
除了对时间背景的淡化、虚化之外,贾平凹近期创作有意打断情节发展,使叙述的时间流减慢,也使空间性进一步得到凸显。《带灯》分为“山野”“星空”“幽灵”三部,每部内还贯穿着各类小标题,将作品划分为长短不一的各部分,短则一两句,长则数段。小标题所辖的部分自成一体,或讲述事件,或介绍人物,也有一些标题成为区分不同空间的标志。《老生》摒弃了小标题的使用,在“开头”和“结尾”之外,讲述四个故事,用“⋆⋆”将叙事分为或长或短的若干小节。《极花》进一步简化,在小说题为“夜空”“村子”“招魂”“走山”“空空树”“彩花绳”的各部中,叙事并不连贯,而总是被空行打断,并由此分为多个叙事单元。通过这类手法的使用,贾平凹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现代小说家的叙事困境,即如何克服时间的单向度发展,展现多样化的可能性。发生在不同时空的叙述被重新组织起来,小说的空间效果由此产生。
多种文体的插入也是小说产生空间效果的重要原因。文体混杂是现代小说的叙事特征之一,在《尤利西斯》等西方现代小说中都曾经出现,而在贾平凹笔下,自上世纪末的写作中,作者就开始尝试不同文体的杂糅,如《高老庄》中不断出现的碑文,《秦腔》中的各种唱词等,在近年来的创作中,这一特征更加明显。在《带灯》的叙事过程中,多次出现会议记录、文件摘录、旧年县志等内容,这些内容在措辞上完全保留了实用文体的特点,简洁、客观、不动感情,与上下文所描写的社会生活的鲜活、生动、烟火气形成了鲜明对比。如果说,《带灯》中多种文体形式的存在展示了生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老生》则借助《山海经》讲述的山与海,极大增强了小说在空间表现上的力度,使得小说对百年中国的讲述不仅局限于线性发展的历史,也突出了每个时代的历史纵深感。多种文体的插入减慢了故事时间,甚至在一些时间点上出现了凝滞,叙述时间仍在继续,但情节没有发展,故事时间出现了停顿,而“时间的定格,就像一幅照片凝固的是一个瞬间一样,一种空间感被表现了出来”。
对细节的关注和情节的并置同样造成了时间性的减弱和空间性的加强。贾平凹曾总结《秦腔》《古炉》等小说写法,称其“不倚重故事和情节”,“靠细节推进”,近期小说仍然延续了这一特点。《带灯》中没有一以贯之的情节和首尾相贯的故事,相反,在以主人公为核心的叙事过程中,以人物行动为线索,穿插了大量的细节,带灯的工作和生活如书中所说的——“琐碎泼烦”,在人物被琐事牵绊,读者被细节吸引的同时,小说的时间性相应减弱。如果说细节描写吸引读者兴趣,使其埋头于细节而忽视时间,那么情节并置则进一步造成了时间凝滞。《极花》在叙事上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情节并置,如“村子”中连续八次出现的“黑亮说”,“招魂”中接连五次出现的“我在想”。“走山”中六次出现的“比如”,以及“空空树”中出现了六次的“如今我学会了”。情节并置突破了叙事的时间顺序,形成在空间中并置叠加的效果,而读者也无法再根据时间的线性发展进行阅读,必须在反复阅读中建立一定的空间秩序,并将各类片段重新联系起来理解,由此,小说的空间形式在读者意识中建立起来。
二
在凸显空间性的同时,贾平凹近期小说建构出多重文学空间,包括由自然景观构成的地理空间、由人物心理构成的想象空间以及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空间,通过不同空间的并置、对立、交叉,作品传达了更加立体、复杂的现实图景。
自然地理空间是人物活动的背景,也是故事展开的基础,《带灯》中的樱镇是秦岭山中的小盆地,有灵动的山水自然和淳朴民风,同时它也曾是秦岭中著名的驿站,修建大工厂挖出的崖壁上刻有“樱阳驿里玉井莲,花开十丈藕如船”的诗句。《老生》以“秦岭里有一条倒流着的河”开篇,在不知年龄的唱师的讲述中,秦岭里的驿站栈道、飞禽走兽、树木花草尽数呈现,并在空间的变化中显示着时代变迁。《极花》中的自然空间是黄土原上的村子,被拐卖的胡蝶无法得知它的地理位置,也正由此,这个衰败没落、没有生气的村子反而具有了更广泛的象征意义。在上述作品中,自然地理都表现为乡村景观,它或美好或丑陋,既构成人物活动的背景,由人物描摹和感受,也是作品描述的对象,代表了作者认识现实的态度和方式。作者一方面以文学空间再现并帮助塑造了昔日的乡村景观,另一方面也以空间的变化展现了乡村在当下时代的必然变革。
近期作品的另一重空间表现为人物心理空间的建构,在小说对现实的关注之外,心理和想象空间的建构成为塑造人物、揭示主题、反映现实的重要方式。《带灯》的主人公将精神寄托于远方,通过不断给元天亮写信,抒发苦闷、表达情绪,为自己建构起一个与世隔绝的心理空间。在工作中终日为琐事奔忙,处理各类事务不失精明、果断与泼辣的带灯主任,在信中温柔、善感而多情,想象空间使她有机会转向自己的内心,表现出不同的自我认知,工作的苦闷都化作了秦岭的山风露水,而她似乎也变成了山中的野物,有了灵性与温柔。《极花》中被囚禁的胡蝶也拥有一个想象空间,突出表现在两个部分,一是“村子”中频繁出现的“我在想……”,由此读者了解了胡蝶的身世,做城里人的梦想和不成功的爱恋;一是作品结尾处胡蝶在梦中经历了惊险的解救,最终又选择回到被拐卖的地方,是梦?非梦?梦醒之后的胡蝶难以抉择。不同空间形式对人物的多样性塑造起到了重要作用,想象空间是带灯和胡蝶的精神避难所,也是面对现实的支撑和动力,同时想象和现实的并置也预示着人物心理空间的内在矛盾和分裂,在《带灯》下部“幽灵”中,“给元天亮的信”再未出现,当想象空间最终坍塌、消失,与现实混为一体,人物的精神危机也随之出现。《极花》结尾处的梦境也深刻揭示了胡蝶的困境,身处两个空间的分裂中,胡蝶“没有了重量,没有了身子,越走越成了纸,风把我吹着呼地贴在这边的窑的墙上了,又呼地吹着贴在了那边的窑的墙”。
除了自然地理空间和人物心理空间,近期小说还致力于建构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空间。一般来说,现代化是一个时间概念,遵循线性发展的时间逻辑,但如巴赫金所说,“时间的标志要展现在空间里”,同时,“现代性既是一种历史规划,又是一种地理和空间的规划,是对我们栖居于其中的环境持续的分解和重组。”在现代化进程中,空间不是静止不变的容器,而是充满了矛盾、冲突,是各种力量交汇对抗的场所。因此,《老生》在讲述中国近代的百年历史时,并没有将时间作为叙事的主要动力,而是建构出不同时代的四个社会空间,对空间的强调并没有降低小说的历史性,相反,通过将时间与空间结合,小说更真实揭示了不同时期的社会存在,显示了中国农村由近代向现代的艰难历程。《带灯》开头提出“这是开发的年代”,“开发”表现为一系列的空间变化,大工厂引进,道路拓宽改建,梅李园被毁,房子拆迁,坟墓迁移;空间的意义也发生变化,镇街的老房子被改造成商业街,原本的居住空间变成消费空间;空间重构也导致了人们的争夺,为了多得拆迁款,人们发了疯地多栽树;小说结尾处造成严重后果的斗殴,其起因也是元、薛两家对河滩沙地的争夺。在现代化过程中,空间不再是与人们依存共生的场所,而被按照利益关系重新分配,并进而成为争夺的对象。
三
通过空间形式的建构,贾平凹近期小说呈现出开放性的结构特征。一方面,近期作品中没有首尾连贯的完整故事,也缺乏传统意义上的开端和结局。《带灯》以“高速路修进秦岭”开头,以“镇政府还有着故事”结束,《老生》始自倒流河,也终于倒流河,开端既没有明确的起因,结局也是开放式的,这既体现了作者面对现实“我不知道”的诚实体会,也喻示着生活的进程,不会因为故事的结束而终止。另一方面,在叙述过程中,空行、小标题打断了情节发展,各种事件、人物、生活细节不断涌入,造成了情节的片段化和并置,也使叙述指向暧昧不明,生活的不同横截面得到突出展示。不同空间的并置、交叉,以及由此产生的开放性的结构特征,既展示了生活的本来面貌,尤其是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农村社会的真实面貌,同时也增强了作品对现实的表现力度。
在打破线性逻辑的同时,小说的空间形式也将读者的注意力转向自身,增强了作品本身的表现力。贾平凹写作一向不倚重故事情节,这一特点在《秦腔》《古炉》等小说中均有体现,在近期作品中,他更加注重形式的创新,并建构出更典型的空间形式。“空间形式的发展代表着空间作为一种结构因素,在小说的主题建构上建立的一种连续性”,由此促使读者放弃追随情节发展的传统阅读方式,而关注作品结构本身。贾平凹在近期创作中,通过一系列方式降低时间性,突出空间效果,并使读者在这一过程中更加关注作品的结构,从而增强了作品本身的表现力。
如果说,贾平凹近期小说在题材上,仍然延续了贾氏以往对农村变革的关注,没有大的突破,而他在形式上的探索却格外引人注目,这种探索不仅体现了个人风格,代表着作家对写作方法的不断探求和革新,同时,“这种形式创造的自觉以及作家在形式上对独特风格的追求,即所谓‘形式感’,也是现实主义衍进的必要条件之一。”
本文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经费资助项目(310833154003;2014G6331009)的阶段性成果。
乔 艳 长安大学
注释:
①贾平凹:《极花·后记》,《人民文学》,2016年第1期,第92-93页。
②[美]戴维·米切尔森:《叙述中的空间结构类型》,约瑟夫·弗兰克等著,《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秦林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66页。
③⑥贾平凹:《极花》,《人民文学》,2016年第1期,第4页、90页。
④邓颖玲:《诺斯托罗莫的空间解读》,《外国文学评论》,2005年第1期。
⑤贾平凹:《带灯·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361页。
⑦[苏]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三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74页。
⑧[美]菲利普·韦格纳:《空间批评:批评的地理、空间、场所与文本性》,《文学理论精粹读本》,阎嘉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37页。
⑨王欣、石坚:《时间主题的空间形式》,《外国文学研究》,2007年第5期。
⑩温儒敏:《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