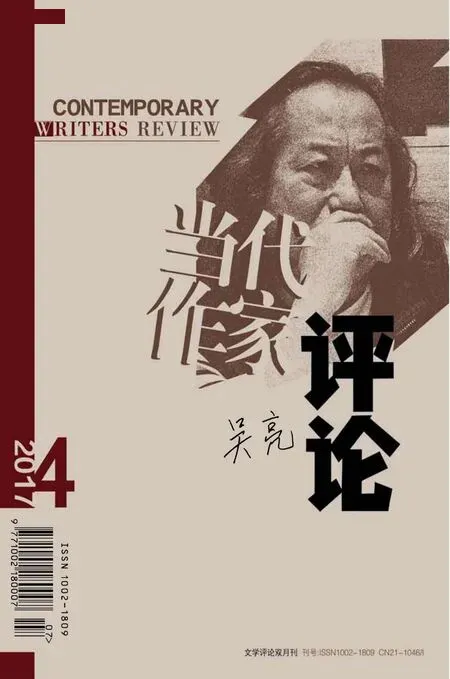以理想、思想、梦想建构的儿童文学世界
——常星儿创作面面观
2017-11-13陈晖
陈 晖

以理想
、思想
、梦想建构的儿童文学世界
——常星儿创作面面观
陈 晖
上世纪80年代开始儿童文学创作的常星儿,从现已发表的400余篇中短篇小说童话及30余部长篇小说童话文本看,这位笔耕不辍、成果丰硕的作家已形成自己与众不同的创作特色与成熟的个人风格。纵观常星儿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我们能看到一以贯之的理想的光芒、思想的力量和梦想的色彩,他以理想、思想、梦想建构起自己的儿童文学世界。
一、社会与自然环境中的少年成长书写
成长小说一直作为少年儿童小说最具代表性的一个类别,能够归纳出其固有的叙事模式,但从广义上来说,以少年儿童为预设读者的儿童文学,本质上都是成长的文学,成长主题是儿童文学也是少年儿童小说的永恒主题。儿童文学作家都会从自己的儿童观、儿童教育观、儿童文学观出发,从自己的成长记忆与成长经历中获取或提取主观经验,结合对当代少年儿童的体察、感受与思考,展开自己的成长书写。
常星儿的众多短篇小说,像具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黑泥小屋》《回望沙原》《苦艾甸》《白鹭别墅》《河过沙原》等,还有他的长篇小说《谁在草垛上唱歌》《男孩的河》《枝上小鸟》等,都是将少年的成长作为主题及主要的表现内容。正如常星儿在《谁在草垛上唱歌》后记《牵挂一个远行的少年》一文中指出的,他书写成长的初衷是因为少年们在匆匆行走的路上且是最脆弱的时期,“太需要我们的关爱与呵护”,从这一点出发他告诫自己“故事要浪漫,更要现实,要触及生活的实质,其中包括对社会变革、道德观念、人生价值的思考”。
常星儿的作品直面中国当下的现实,尤其关注到中国近二三十年来城市经济高速发展引发的乡村社会的剧烈变化,他将这其中种种的矛盾与问题投射到他所描写的少年儿童生活中,通过少年主人公的生活遭际与心理感受,将资本、商业及市场化经济带来的冲击,将人们思想道德观念的裂变,聚合成一些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事件与场景加以着重的表现。他的小说敏锐捕捉着社会各个角落发生着的震荡,像乡村经济及生活方式的改变、自然资源的耗损与生态环境的破坏、社会各阶层贫富差异加剧等等,以及在此背景下留守乡村的少年儿童因社会发展不均衡、家庭变故、生活窘迫而面临种种的困难与艰苦;他深入少年们的内心,代他们传递心声,表达那些依傍祖父母的孩子对远在他乡父母铭心刻骨的想念,表达他们热爱乡土同时向往外面世界的心绪,表达他们对时代对社会对成人世界的肯定与否定、评价与判断,表达他们因身心发育与同伴相处与异性交往的困惑、感伤与迷惘。常星儿对新时代少年的外在现实与内心现实的真实而深切的描画,让他的成长书写有了厚重的质感,更彰显出儿童文学作家的情怀及责任担当。
正如文学评论家李敬泽曾指出的,在我们所处的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青春期的焦虑和困惑、成长的孤独和困难也在加剧,他们的精神需求非常复杂迫切……恰恰特别需要我们用人类积累下来的经验、知识和智慧去帮助他们,失语、沉默,任由孩子自己去摸索,这是失职,是没有尽到文化上的责任”。我们当下的儿童文学创作,应尽可能反映中国不同地区不同社会阶层青少年的客观生存状况,关注广大少年儿童生活现实与内心诉求,体察时代脉动社会变化带给少年儿童成长的方方面面影响,让创作更扎根于底层,让作品闪耀理想的光芒传递温暖的关怀,我们的儿童文学也就更能够走进少年儿童的心灵深处,更能实现儿童文学的思想价值与情感力量。
与社会及人文环境互为支撑,常星儿的少年成长书写还纳入了自然的力量,着意强化兼具勃发生机和残酷恶劣两面性的大自然对少年心性及品格的锻造。
“苦艾甸”和“沙原”是常星儿集合了自己童年记忆中的家乡地貌创造出来的两个具有代表性的场域,作为了他少年小说系列主人公共有的成长环境。蛮荒苍凉、连绵起伏的沙坨子,蒿草繁茂、树木葱茏、野花盛开的草甸,考验着也滋养着成长中的少年,承载着他们的衣食住行与喜怒哀乐,唤起他们对自然界的感恩与敬畏、对各个生命体生命形态的尊重与爱护。在作品中,八百里瀚海、那木斯莱湿地、红柳滩、北牧河谷、野麦岭山谷等地,既是故事生发的场所,起背景的作用,还经常是情节的要素,成为触发儿童心理活动或活动的关键点。作家曾经明确说明自己相关的创作理念,他要连接自然生态与少年们的心理生态,要用作品传递“对自然的热爱和对生命的赞美”,传递“自然对少年成长及人类生存的影响和作用”,他把这些作为了创作重要的“主旨和指向”。这样的创作思想让他的成长文学在具备乡土及地域文化特质的同时,具有了大自然生态文学的色彩。
二、“爱”与“美”:理想和信念的坚守及诗意表达
无论是写实性的小说还是幻想性的童话,常星儿都看成是对自己“内心世界的一次净化与洗礼”。他塑造正直勇敢的阳刚少年、纯真聪慧的阳光少女,他“用清澈的目光看着他们,用饱含深情的笔勾画着他们,用纯净的心灵之声表达对他们的赞美和敬意”。理想和信念的坚守,让作家将“爱”与“美”当成了自己作品的精神内核,常星儿的创作也由此彰显出积极向上的情感基调与感染力。
常星儿认为少年儿童文学作品应该以亮丽为底色,让读者更多地从作品中看到我们这个世界的纯洁、美好和善良,看到爱与美的价值和意义及未来的希望,从中汲取成长的力量。《草滩秋夜》一篇中,空旷苍茫的碱草滩的夜色下,失去父亲的少年远明不得不独自辛勤劳作,他最终因为罕山叔点燃的篝火及陪伴他走上回家路的歌声而敞开心扉;《谁在草垛上唱歌》一篇中,北衫跟丛生两个男孩在竞争及矛盾冲突中、在各自经历生活的考验中结伴前行,相互了解最后建立起深厚的友情;在《枝上小鸟》中,跟爷爷相依为命的男孩李多多即使备受挫折与伤害,依然坚强勇敢热诚友善,让自己的心灵自由飞翔与歌唱……
常星儿作品对“爱”与“美”的诗意表达主要借助人物与景物、物象与意象、情境与意境的艺术构建实现和完成。
在常星儿的小说和童话中有很多历经磨难依然正直坚韧的成年人形象,作者将他们塑造成为少年成长的引路人。有如忽浪爷、麻爷、实如爷等长者,他们以自己的生活阅历及经验、以睿智而亲切的教诲,温暖照亮孩子们的世界。还有一众少年主人公的父亲和母亲(包括继父继母),他们在尚待改变的贫穷落后中依然坚守着温厚善良、简朴勤劳的道德及行为方式。少年们的祖辈和父辈都在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示范着乡间民众间最朴素的为人之道,让少年们懂得,在遭遇苦难困厄、不公正及社会丑恶时,在生离死别、游驻聚散不可避免时,人们艰难中的相扶、困境中的相助、孤独中的理解、冷漠中的脉脉温情和殷殷守望,是人世间应该永远遵从及信奉的法则,是人性光辉之所在。
写作灵感及创作源泉植根于东北大地的常星儿,景观景物、风物风土的描写具有着浓重的北方的地域色彩。地处辽宁西北部的彰武是常星儿的故乡,他魂牵梦绕的回想与回归化作了众多富有地标特征的物象与意象:草甸上阳光中光芒四射的金色草垛、成峰似浪的沙坨子及沙陀间缠来绕去的小路、白色的盐碱滩在晚风中起伏的一棵棵稀疏的碱草、在夕阳中摇曳的红柳及美丽的青杨树、草滩上火烧云似的晚霞中缓缓升起的红月亮……在自然风物的映衬下,具有人文色彩的风景描画也次第展开:雾霭中隐约可见的村庄上空袅袅升起的炊烟、傍晚各家村民招呼猪牛羊进圈此起彼伏的吆喝声、草滩守夜人及乡间小屋的独居者孤独苍凉的歌声……借助作家深情饱满的对乡土的热爱还有与生俱来的熟悉亲近感,借助作家富于才情的如诗如歌的笔触,作品创设出多维多向、多姿多彩的审美空间,集聚起动人心弦的艺术感染力。
作者创作中对诗性的追求是全方位的,其中既有古诗传统诗歌意境的化入,也有现代诗歌意象的撷取,还有自然物象及景象的提取与升华。在《谁在草垛上唱歌》《想念那木斯莱》《找回那片金色百合》等作品中,无论是那饱含忽浪爷深情爱意的草垛,还是那丰饶润泽生生不息的那木斯莱草甸,还是那片极富梦幻色彩的金色百合,它们或蕴含人物的精神气韵,或承载大地的博大恩泽,或象征人们的美好心愿与梦想,依靠物象与意象、画面与画境的描绘,“爱”与“美”的表达具有了优美的情致与风致。
在常星儿笔下,“一切景语皆情语”,哪怕是一个人名一个地名及至一个建筑物的称谓,都有着特定的诗情画意的寄寓与点染。作品沿用了一些具有历史典故或诗意内涵的真实地名,比如“那木斯莱”,其蒙语意是“开莲花的泡子”;比如章古台、阿尔乡、申金花、谢林塔拉等蒙语意思分别是长满苍耳的地方、温泉或者“神水”、长满小根蒜的坨子、开遍黄花的甸子;那些主人公栖身的小屋,都有着让人回味的名称,比如白鹭别墅、丁香别墅等,还有那些少男少女的名字,有亮、远明、望秋、改草、天馨、婉雪,映现着作家对纯美典雅文风的追求,让人过目不忘。
在童话及幻想性突出的文本中,常星儿更将唯美的意象借助灵动的想象沉潜到幻想的各个层面。比如在《想念那木斯莱》中,阳光、月光、露水、晚霞都是可供采摘取用的,阳光可以放进火炉、月光可以做成纱巾、晚霞可以涂到兔子们的脸上当成胭脂、露水和阳光可以装入草梗编成的背篓……在《找回那片金色百合》中,那朵会微笑舞蹈歌唱的金色百合,瞬间变出了如潮似云的百合花田,身穿红色连衣裙脚踩红舞鞋的兔妮儿和老兔子在花田中梦想成真回到童年;老兔子吹响苇笛,翅膀折断嗓子嘶哑百灵鸟恢复了信心和勇气,重新渴望着蓝天和歌唱……
向儿童传递思想与美是儿童文学最重要的使命与责任,也是儿童文学意义及价值之所在,常星儿作品正是充分重视并把握了儿童文学这一重心与方向,他的创作在儿童文学的本质与本体上具有了品质与高度,进而支撑起他所创建的儿童的文学世界。
三、以借喻和象征折射现实的幻想模式
常星儿近年来转而重视幻想文学创作,不仅有《枝上小鸟》这样以写实为主带有幻想性的小说文本,更有《找回那片金色百合》《想念那木斯莱》《瓦罐公》等介于童话和幻想小说之间的多部作品问世。与众多作家的儿童幻想文学不同,常星儿不再侧重于用夸张拟人的手法描绘儿童稚趣的想象、生成天真烂漫的童真童趣,也不着重于在幻想人物的人性与物性的粘合,更不拘泥于幻想故事情境及情节的逻辑性发展,他的幻想人物及故事更多的具有借喻和象征的意义,是对现实的折射和曲折反映,借此表达对社会的思考、讽喻及批判。
常星儿作品中的幻想角色通常带有鲜明而确切的象征性,直接指涉某一类人物或某一种思想意念,它们以主观突入的方式进入到作品的环境及事件中,承担作家作品赋予它们的角色使命。这些拟人化角色的特质及功能定位偏重于“人性”而非其从属的某类动物的自然“物性”,围绕它们也没有生成因物性与人性的交互融合而具有的特定趣味。随着作品逻辑假定的成立,随着这些幻想人物展开行动,读者往往会发现这些人物具有了某种典型性或代表性。比如作者着力塑造的几个动物主人公角色,像《瓦罐公》中的老麻雀、《找回那片金色百合》的老兔子等,没有夸张、也不变形,还不易辨别或记忆,但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多面性,难以一言蔽之,它们很大程度上成为了福斯特小说理论中提到的的圆形人物——“既简单、又平庸,仍有其一定深度”。
这样的幻想模式并非完全属于常星儿个人的艺术探索及实验性创造,罗大里《洋葱头历险记》《假话国历险记》等经典文本,早就开启了以借喻和象征影射现实的幻想文学的内容及表现的一脉传承。冲破儿童幻想文学的既定美学标准与固化形态,包括幻想逻辑性与幻想趣味的生成模式,塑造有厚度与深度的幻想人物形象,恰恰是我们当代儿童幻想文学需要开拓和创新的领域。
2013年创作出版的《枝上小鸟》是常星儿作品中最别具一格的文本。作品的主题及主体故事内容是写实的,深刻甚至是痛切地反映了中国广大乡村及社会底层孩子的生存困境。故事较多依托主人公九岁男孩李多多的心理活动及内心世界展开,自然而然纳入了幻想的因子。李多多在祖父的照顾下生活,母亲早已离去,父亲远走他乡务工,祖孙俩艰难度日,还成为了乡村恶霸盘剥与欺凌的对象,爷爷的日夜劳作也不能为多多换来其他孩子都有的六彩魔方、五色铅笔、电子手枪,他朝夕相伴的小狗二毛还死在了恶人的脚下。李多多对父亲的思念、对安全感的渴望、对自由与快乐童年的向往,最终化作了变成一只小鸟的心愿与幻想,他这幻想中包含的是这个孩子渴望挣脱现实困境的心声。李多多的小鸟幻梦贯穿作品始终,成为他在幻想与现实中穿梭出入的情节推动力,聚合成作品的高潮,更收束成有情感张力的结尾,成为了整部小说震撼人心的“文眼”。
作者在《枝上小鸟》的引子中这样写到:
变成一只小鸟的李多多有时会躲在爷爷干活的丁香树丛里为爷爷歌唱;有时会盘旋在苦艾甸的上空看金花鼠、狗獾和刺猬做游戏;有时会给慧秀衔来一朵野百合让她高兴……甚至,他会飞到任何一个需要帮助的人身旁,为那个人做他所能做的事情……变成一只小鸟的李多多依然坚强勇敢和善良诚恳。啾啾的鸣声是他在为这个世界歌唱。告诉你,已经变成一只小鸟的李多多还是那样快乐,所以,当我们身旁缺少了那样一个小男孩,请你千万不要难过……
行走是艰难的,而有一双翅膀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所以,李多多要变成一只小鸟。
在作品的结尾则是以下的文字:
变成一只小鸟是李多多的愿望。然而,我们要说,李多多,你变不成小鸟,永远也不能变成小鸟;你变不成小鸟,我们任何人都不能变成小鸟。这是事实。不过,我们感谢你。我们需要这样的想象,真的很需要。你的这个想象足以让我们眼前一亮,足以让这个世界充满光明和温暖。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东西吗?
南方有很多很多城市,每座城市都是那样美丽。那里四季都是春天,因而,你再不会在雪地上行走。李多多,那座城市里的高楼与园地草坪之间任你来往,每个广场、车站、图书馆、影剧院、足球场……都对你敞开着,并且,有一群群花朵一样的小鸟伴你飞舞。当然,学校也由你自己选择。那座城市欢迎你,真诚地欢迎你,所有的人都会对你微笑。李多多,这是我们的欣慰。
作者直抒胸臆的文字令人动容,他表达的是他个人深挚的情感,也传递了我们基于良知与公平正义的对李多多这样孩子获得关爱与呵护的强烈期待与企盼。正如著名儿童文学理论家浦漫汀先生曾经赞誉的“常星儿是在用文字,更是用信念,为我们守望一片纯净与美丽”。
或者我们会以严苛的目光注意到常星儿作品表征上可能存在的“主题思想先行”、“概念化主导人物设计与呈现”、相对明显的成人化视角与表现方式,以及幻想切近现实带来的拟人化故事内容及趣味的弱化,但我们恰恰最不能忽视这些可能同样是作者个人的创作特质及个性化艺术追求,而常星儿基于理想、思想、梦想的儿童文学创作理念与实践成果,有待于我们持续给予关注和重视、研究与讨论。
(责任编辑
周
荣
)陈晖,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图画书创作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