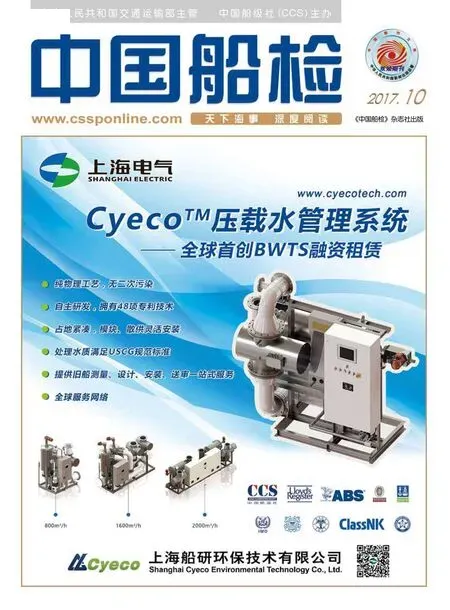《1979年国际海上搜寻救助公约》的诞生
2017-11-03沈肇圻
沈肇圻
《1979年国际海上搜寻救助公约》的诞生
沈肇圻
为开展国际合作搜寻营救海上遇险人员,“海协”于1979年4月9日~27日在汉堡召开国际海上搜寻救助会议,讨论并制定了《1979年国际海上搜寻救助公约》。公约强调发扬人道主义,规定缔约国在本国的法律、规章制度许可的情况下,应批准其他缔约国的救助单位为了搜寻发生海难的地点和营救遇险人员立即进入或越过其领海或领土。公约的附则对搜寻救助的组织、国家间的合作、搜寻救助的准备措施、工作程序和船舶报告制度等作了规定。公约自1985年6月22日起生效。中国于1985年6月24日核准了公约。
其实,制定这样一部公约的想法最早要追溯到20世纪初。
长久以来,人们千方百计避免和防止海难,但事故仍时有发生,为挽救遇险人员的生命,搜寻和救助是重要的措施。“海上皆兄弟”,船长在海上接收到求救信息,要做出相应回应,这是古老的海上传统,人道主义的表现。
1910年9月23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的第三次海洋法会议把这个传统写入了1910年统一海难援助和救助某些法律规定的公约,此公约在规定“无效果,无报酬”原则的同时,将这个传统,用国际法固定下来。它的第11条规定:“船长在海上发现遭遇生命危险的每一个人,即使是敌人,都必须援助,只要这样做,对其船舶、船员和旅客没有严重危险。船舶所有人不因上述规定的违反而承担责任”。
“泰坦尼克”号惨案后,第一次国际海上安全会议签订的1914年安全公约,也作出了类似规定。公约第Ⅴ章无线电报第37条规定:“接到遇难船舶求救的船长有责任向遇难船舶提供援助”。
1929年安全公约也有类似规定。第五章航行安全第四十五条:“遭难电信执行职务程序 第一款,船长于本船收到遭难之无线电信,应即开足速力(当时习惯用词,相当于现在的‘马力’),驶往援助,但船长委实无能为力,或按当时特定情形无理由或无必要为之执行或依本条第三款、第四款之规定,应免执行者不在此限(注:第三款指已知其他船已应征前往,第四款指已知其他船已抵遇险现场)。”
1948年安全公约作了进一步规定,第五章第一条遇难通信、程序规定:“海上船舶之船长,不论由任何方面接到有船、飞机或艇筏在遇难中之信号时,须以全速度前往援助遇险之人,如属可能,必须通知他们正在前往援助中,若此船不能前往援助或因情况特殊认为前往援助为不合理或不必要时,该船长必须将未能前往援助遇难人之理由载入航海日志中。”
这样的规定,一直沿用到1960年和1974年安全公约中。
第四次国际海上安全会议通过1960年安全公约的同时,还用决议形式对海上搜寻救助工作提出了建议:缔约国政府应设立海岸无线电台,以保证在无线电报、无线电话频率及救生艇所用频率上的连续守听;“海协“应与国际民航组织(ICAO)、国际电讯联盟(ITU)和世界气象组织(WMO)合作研究搜寻救助设施计划;“海协”、国际民航组织、国际电讯联盟和世界气象组织抓紧研究以最好的方式建立飞机与遇难船舶之间的通信联系;缔约国政府应鼓励本国所有船舶参加商船船位报告系统,该系统应免费提供有关船舶所使用,政府应鼓励船舶适时配备应急示位标,以利搜寻救助。
1969年“海协”起草了“商船搜救行动手册”,作为海上遇难求救人员或救助人员的行动指南,并由1971年“海协”第七届全体大会通过,推荐给各国使用。手册共八章。它们的题目是:搜救协调、遇难船的行动、救助船的行动、飞机的救助、搜寻计划及指导,搜救结束、通信及海上飞机事故。1978年“海协”修订了这个手册,改名为“海协搜寻救助手册”,共两部分,第一部分:搜救机构,主要介绍现有各国搜救机构,现有服务和设施等。第二部分:包括对所有参加搜救行动人员,特别是船长有帮助的资料。手册还有一个附录,“海上搜救识别规则”供搜救人员和被搜救人员----遇险人员的相互通讯联络之用。
1970年10月美国举办的搜寻救助座谈会建议,“海协”应在海上安全委员会下设立一个搜寻救助专家组,着手起草国际搜寻救助公约。
往事拾遗之三十四
座谈会认为手册对海上搜寻救助业务流程作了详细规定,对救助操作很有帮助,但海难事故的特点是偶然性、突发性,时间和地点都难以预料。因此不可能像岸上消防队那样,可以常设,这就需要国际间合作。同时海难救助,时间极为紧迫,可以说争分夺秒,需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联系网络,更好地协调行动。更主要的是搜寻救助可能要进入一国领海领空,又涉及国家主权,只有通过国际公约才能协调好这方面的关系。
海难救助是偶然需要,即使西方海运发达国家,也不保持一个长时间专门职业队伍,而是依靠社会力量,作为公益事业,组织志愿人员来进行。例如英国救生艇协会,总部设在英国普尔(Poole),在一些海港有分部。总部设执行局长和秘书二人。分部也只有一到二个专职或兼职人员。会员均为志愿人员。因必要时要放下工作执行救助任务,所以均须所在单位同意,经体检合格,登记在册。协会组织培训和操练,提供救助用设备和服装,无报酬,只有年度评奖等精神奖励。协会经费来自社会捐助,其中包括获救人员和家属亲人的捐助。它成立于1824年。在荷兰、前西德和加拿大等44个国家有类似机构。但他们是民间机构,相互间保持联系,并组成联盟。作为非政府性国际组织,“海协”还给予这个联盟咨询地位,可应邀参加“海协”会议,但涉及跨国搜寻和救助,涉及国家主权,他们就没有决策权,因此有必要通过国际公约来建立政府间的救助合作渠道。
应前西德政府邀请,这次会议有51个国家派代表出席,2个国家和联系会员香港派观察员列席。此外,还有4个国际组织派出观察员。5个非政府性国际组织也派了观察员。总计245人。西德杰·布鲁尔博士当选大会主席,中国等十个国家代表被选为副主席。
中国代表团由交通部救助打捞局吴英诚局长任团长,通知我从伦敦去汉堡,任副团长。图1会议现场。大会选举主席、副主席前,秘书长找我拟选中国代表团为副主席。经与吴英诚局长商量,他表示,语言上有难处。我说这是国家荣誉,可以在旁协助。选举结果,他当选大会第一副主席。
这次会议是发扬人道主义精神的会议,对海上遇险人员伸出援助之手,挽救他们的生命。因此要强调争分夺秒。但是海难事故不一定发生在本国海域,需要邻国之间的合作。当援救来自邻国时,就涉及入境问题。经过协商,中国代表团提出,援助和尊重主权必须兼顾,得到多数代表的认同。在缔约国的本国法律许可情况下,应批准其他缔约国的救助单位,只是为了搜寻发生海难的地点和救助海难中遇险人员的目的,立即进入或越过其领海和领土,写入了公约。
人们都不希望发生海难。但还是时有发生。为做好充分准备,就需要将海域划分成搜救责任区,由负责国家来承担搜救主要责任,也不排除邻近国家的协助。如何划区,就需要相邻各国来协商。这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本来相邻国家之间就有领海,还有大陆架,专属经济区的争议。我们国家,按公约建议在第七区,周边国家有澳大利亚、日本、朝鲜、韩国、越南、菲律宾、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等。在讨论中,我们表示了搜救责任区的划分不应与国家领海主权相混淆。最后在公约中写明,并强调:搜寻救助区域的划分不涉及,并不得损害国家之间边界的划分。
会议讨论通过了1979年国际海上搜寻救助公约。其主要目的是:为国际海上搜寻救助方案确立法律和技术基础,以推动搜救组织之间和参加海上搜救作业的各个单位之间进行合作。公约有8个程序性条款和1个附件。附件共6章,开展搜救工作指导原则;名词和定义;搜寻救助的组织机构;国家间搜救合作;搜寻救助的准备措施;工作程序和船舶报告制度。公约规定各缔约国应尽快完善搜救机构,建立救助协调中心和救助分中心、划定搜救区域、制订搜救行动程序和通信联络程序,并建议在负责的搜救区域建立船舶报告制度,要加强各缔约国之间的合作以及海、空搜救部门之间的合作,以便对海上遇险人员提供搜救服务。另外,会议还通过了8个决议,以推动进一步改善海上搜救作业。会议期间,在汉堡港内组织了救助表演。见图2和图3,还参观了汉堡港用的救助船,见图4和图5。
因会后要应前西德一家救捞公司之邀,进行参观访问,国内来专业人员六人,译员三人,加我共有十人之多,原拟住外贸部驻汉堡商务处,但它在郊区,无公共交通。我们在附近散步,竟有西德人停车,好心地问,要不搭他车进城。于是决定搬去会场——汉堡国际会议中心附近。所住旅馆房内,只有一个小台灯,三周会议文件众多,只能夜间阅读,准备意见。会后回到伦敦,竟有一个小黑点在左眼内不停地转动,英国皇家医院称,要住院手术。经大使特准,有生以来第一次住院。第二天,轮椅推进手术室,半小时完成手术,用冷冻方法把破裂视网膜补起来。怕爱人沈福妹担心,未告诉她。1990年工作调动到中国船舶工业集团,被派去汉堡任西欧代表处首席代表,爱人同去常驻。一次去汉堡国际会议中心参观,因时间已过去近二十年,才告诉她眼睛出过事,在她建议下照了张照片留念(见图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