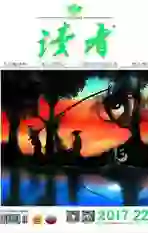医生也许都想错了
2017-10-28阿图·葛文德彭小华
〔美〕阿图·葛文德++彭小华 译
一
约瑟夫·拉扎罗夫是市政府的一位行政官,几年前,他的妻子死于癌症。此时,60多岁的他也患了无法治愈的癌症——一种转移性的前列腺癌。他瘦了近25公斤,腹部、阴囊和双腿都积满了液体。有一天,他一觉醒来,发觉右腿无法动弹,大便失禁,于是住进了医院。那时候,我是医院神经外科组的实习生。我们发现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他的胸椎,对脊椎造成压迫。很显然,癌症已无法彻底治愈,但是,我们仍然希望进行干预。然而,应急放疗没能缩小癌症病灶。于是,神经外科医生给了他两个选项:一是安宁缓和医疗;二是实施手术,切除脊椎处生长的肿瘤包块。拉扎罗夫选择了手术。作为神经外科组的一名实习生,我的任务是履行知情同意手续,并取得他的签字,确认他理解了手术风险并希望施行手术。
我站在他的病房外,汗津津的手里拿着他的知情同意书,竭力思考该如何开口跟他把这个话题谈明白。我们都希望手术能够阻止脊椎损伤继续发展,但是手术治不好他的病,也不能纠正瘫痪,更谈不上使他恢复正常的生活。无论我们做什么,他都只能存活几个月,而且,手术本身也有危险。要进入脊椎,需要打开他的胸腔,切除一根肋骨,拿掉一片肺叶,手术中失血量会很大,以他虚弱的状态,身体恢复起来会很困难。而且,术后发生各种并发症、导致重要器官衰竭的风险相当高。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手术可能会使病情恶化,缩短他的寿命。但是神经外科医生已经仔细斟酌过这些风险,拉扎罗夫自己也确定选择做手术。此刻,我需要做的只是敲门进去,完善术前的各项手续。
拉扎罗夫躺在床上,脸色苍白,形容枯槁。我说我是实习生,需要获得他同意手术的签字,确认他了解手术的风险。我说手术可以切除肿瘤,但是可能会留下严重的后遗症,比如瘫痪或者中风,也有可能导致死亡。我尽量用委婉的语气把情况说清楚,但是,他还是一下子坐了起来。当他的儿子质疑选择做手术是否明智时,拉扎罗夫很不高兴。
“别放弃我,”他说,“只要我还有任何机会,你们一定要让我尝试。”他签完字后,我出了病房。他儿子跟出来,把我拉到一边对我说,他的母亲死在监护室里,死的时候全身插满了管子,戴着呼吸机。当时,他父亲说,他绝不想这样的情形发生在他身上。但是,时至今日,他却坚决要求采取“一切措施”。可见一个理智的人在死亡降临的时候还是无法舍弃求生的欲望。
那時,我觉得拉扎罗夫的选择很糟糕,现在的我仍然这么认为。他的选择之所以糟糕,不是因为手术有很高的风险,而是因为,手术根本不可能给予他真正想要的东西:排便节制能力、体力,以及过去的生活方式。他冒着经受漫长而可怕的死亡的风险(这正是他最后的结局),追求的不过是一种幻想。
从技术的角度讲,他的手术很成功。经过8个半小时的努力,手术团队切除了侵蚀他脊椎的肿块,用丙烯酸黏合剂重建了椎体。手术解除了脊椎的压力,但是他一直没能从手术中恢复过来。他住在监护室,并发了呼吸衰竭、系统性感染,卧床不动导致了血栓,治疗血栓的血液稀释剂又引起了内出血。病情每天都在恶化,他在向死亡的深渊坠落。第十四天,他的儿子告诉医疗组,我们应该停止“治疗”了。
我的任务是去除维持拉扎罗夫生命的呼吸机。我进行了检查,调高了吗啡静脉滴注,以免他缺氧。我想他也许能听见我说话,于是俯身告诉他,我要取出他嘴里的呼吸管。我取管子期间,他咳了几声,眼睛睁开了一小会儿,然后又闭上了。他的呼吸变得越来越吃力,然后终止了。我把听诊器放在他的胸口,听着他的心跳声逐渐消失。
10多年以后,我第一次讲起拉扎罗夫先生的故事时,对我内心冲击最大的不是他的决定有多糟糕,而是我们所有人都刻意去回避诚实地讨论他的选择。我们不难解释各种治疗方案的特定风险,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真正触及疾病的真相。他的肿瘤医生、放疗医生、外科医生,以及其他医生给他做了几个月的治疗,而他们都知道,这些治疗根本医不好他的病。关于他的情况的基本真相,以及我们的能力的最终局限,我们都未曾讨论过,更遑论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什么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了。如果说他是在追求一种幻觉,那么,我们也同样如此。他住进了医院,扩散到全身的癌细胞导致他的身体部分瘫痪,连恢复到几个星期前的生活状态的机会都完全不存在。但是,我们似乎没有能力承认这一点并帮助他去坦然面对。我们没有承认,没有给予安慰,也没有给予引导。我们提供给他另外一种治疗,告诉他也许会有某种非常好的效果。
二
现代科学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生命的进程。跟历史上任何时代的人比起来,我们活得更长、生命质量更好。但是,科学进步已经把生命进程中的老化和垂死变成医学的干预科目,融入医疗专业人士“永不言弃”的技术追求。而事实上,我们并没有做好去阻止老弱病死的准备,这种情况令人担忧。
其实,患者死亡并不代表医生的失败,死亡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死亡可能是我们的敌人,但是,死亡也符合事物的自然规律。在抽象的意义上,我知道这些真理,但是,我缺乏具体的认知——它们不仅对于每个人是真理,而且,对于我面前的这个人,这个由我负责治疗的人,也是真理。
我的同行舍温·努兰大夫在他的著作《死亡的脸》中写道:“我们之前的历代先人预期并接受了自然最终获胜的必要性。那时的医生远比我们更愿意承认失败的征兆,他们也远不像我们这么傲慢,所以不会予以否认。”但是,当我行进在21世纪的医学跑道上,学习使用令人生畏的技术武器时,我恰恰不懂“不那么傲慢”的真正含义。
作为一名医生,你想象自己会获得工作的满足感,结果工作的满足感却变成能力的满足感。这种深刻的满足感类似于一个木匠因为修复一只破损的古董柜子而获得的那种满足感。这种满足感部分是因为自己有助于他人,但同时也来自于技术娴熟,能够解决复杂的问题。你的能力给你一种安全的身份感。所以,对一名临床医生来说,对于自我认识的威胁,最严重的莫过于解决不了病人的问题。
无人可以逃脱生命的悲剧——从出生的那一天开始,每个人都在不断老去。一个人可以理解并接受这一事实,那些已故和垂死的病人不再萦绕于我的梦境,但这与知道怎样对付回天无力的病例是两码事。我身处这个充满英雄主义的行业,因修复生命的能力而取得成功和荣耀。如果你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我们就知道技术上该怎么办。但如果病情严重到无法治愈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没有明确的答案。这个事实令人困扰,并导致了麻木不仁、不人道,以及某种特别的痛苦。
把死亡作为医学的技术极限和伦理选择问题来思考,不过是近几十年的事。医学还很年轻。事实证明,救治失败并不是医学的无能,而是对生命进程的尊重。
三
我做了10年的外科医生,如今人到中年,我发现不论是我还是我的病人,都觉得当前的状态难以忍受。但我也感到困惑,答案应该是什么,甚至是否可能有任何充分的答案,这些都还不清楚。然而,作家和科学家的双重体验让我相信,只要揭开面纱,抵近观察,就可以把这团“乱麻”厘清。
无须同临终老人或处于生命末期的患者相处太长时间,你就可以本能地意识到,医学经常辜负其本应帮助的人们。我们把生命的余日交给治疗,结果为了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好处,让这些治疗搅乱了我们的头脑、削弱了我们的身体。我们在各种机构,比如疗养院或监护室度过最后的时光,刻板的、无形的惯例使我们同生活中真正要紧的东西相隔绝。我们一直犹犹豫豫,不肯诚实地面对衰老和垂死的窘境,本应获得的安宁缓和医疗与许多人擦肩而过,过度的技术干预反而增加了患者及其亲属的痛苦,剥夺了患者最需要的临终关怀。人们无法回避一个问题:应该如何优雅地跨越生命的终点?对此,大多数人缺少清晰的观念,而只是把命运交由医学、技术和陌生人来掌控。
作为医生,我深知生命是一条单行道,一步一步走向衰弱和死亡,生老病死的进程不可逆,但对大众来说,有人会感到惊骇。无论怎样小心翼翼地措辞,仍有很多人觉得这个话题太残酷,可能会让人们联想到这个社会准备舍弃病人和老人。其实,恰恰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拒绝接受生命周期的限定性,以及衰老与死亡的不可避免性,我们的末期病人和老人才会成为无效治疗和精神照顾缺失的牺牲品。好在我们的社会已经意识到这一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正在为生命的末期关怀开辟安宁缓和医疗(临终关怀)的新路径。到那一天,生的愉悦与死的坦然都将成为生命圆满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