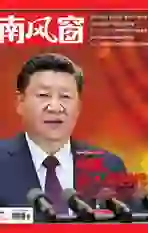欧洲宗教改革为何在德意志引爆?
2017-10-25高凌
高凌
2017年是马丁·路德发起“宗教改革运动”的500周年。在德国中部的哈勒及维滕堡等地都将有大型的庆典活动,纪念这位改变西方历史的基督教新教“路德宗”的创始人—1517年10月31日,当过神父和圣经教授的马丁·路德在维滕堡教堂的大门上张贴了他的论纲,表示反对教皇向信徒兜售“赎罪券”,从而打响了从内部反抗罗马天主教会的第一枪。
欧洲宗教改革为何最先在德意志引爆?如果我们不是基于明确的历史划分,而是把此后一个多世纪里的历史事件视作一个整体,就不难发现,德意志宗教改革和信仰斗争的特殊性,与其相对松散、彼此制衡的帝国权力架构是分不开的。教皇、皇帝和德意志诸侯之间的复杂博弈,屡屡导致了意想不到的结果。
譬如,在欧洲普遍存在宗教压迫的17世纪末,法国禁绝新教的《枫丹白露敕令》替代了倡导宗教容忍的《南特敕令》,英国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的长期斗争促成了王位跨国继承;而此时,最早掀起宗教改革、且宗教斗争最为持久的德意志,却出现了“多元文化”和“宗教宽容”的反常局面。
德意志“教会诸侯”的崛起
宗教改革就其本意而言,无疑来自普通民众革新教会和追求信仰的需求,但是在欧洲各国,它都不得不与16、17世纪的历史现实相结合。在这两个世纪里,德意志有着和欧洲其他各国迥然不同的自身特色。
当时的英格兰和法兰西,君权方兴未艾。法国的天主教会因为和罗马教会一样是罗马帝国西部教会的遗存,试图背靠一个统一的法兰西大君主国,而与罗马教会分庭抗礼;英格兰的天主教会原本就是罗马派遣的传教士建立的,所以它从传统上就亲罗马,而提防本地君主。在宗教改革过程中,法国天主教会利用它和国王之间传统的同盟关系,在路易十四时期取消了对新教徒的一切宽容;而英国几经反复后,天主教的国王被推翻,天主教徒饱受压制,仅仅因其人数众多才没有被禁绝。
德意志的教会和英法两国完全不同。德意志地区在9到10世纪仍属蛮荒之地,德意志人只要有机会就会回到多神教信仰,并且拿起武器反抗皈依基督教的加洛林王朝君主。所以,指望像法国那样,依靠信徒缴纳的什一税和捐献来维持德意志新建的主教管区是不可能的,只能依靠土地的地租和产出来维持教会。而授予教会大片土地的结果,是教会走上了成为大地主,进而成为大领主、甚至诸侯的道路。
加洛林王朝在德意志统治的崩溃,并没有改变教会的这个趋势;相反,公元911年诞生的德意志国家是由4个部族结合而成,国王由选举产生,很难越过4个部族的公爵去直接统治,只能依赖恭顺的教会来加强王权,结果就是越来越多的主教成为诸侯。
在广授权力和土地给教会后,德意志君主通过进军罗马,接受教皇的加冕,使自己在名义上获得统治教会的权力,同时在现实中把罗马教皇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于是在德意志皇权的全盛时期,理论上享有基督教世界尊崇地位的罗马教皇,却被德意志皇帝们贬低为自己的首席宫廷神父。
教皇很快就站出来反抗德意志皇帝,反对皇帝把持主教任命权。随着萨利安王朝的绝嗣,皇帝自由选举的传统恢复,皇权受到重大打击。已经在诸侯等级占据多数的“教会诸侯”,对皇帝的恭顺态度也发生变化了。
在教权与皇权之争的第二个阶段,即斯陶芬王朝时期,教皇反过来试图独霸帝国,把曾经控制自己的皇帝贬低到自己封臣的地位上。在漫长的斗争中,斯陶芬王朝最终灭亡,德意志陷入十几年没有皇帝的大空位期。而教皇也遭到报应,先是被劫持到阿维尼翁,后来又分裂为罗马的教皇和阿维尼翁的教皇。当“大公会议”除了选举出自己的教皇之外无所作为时,欧洲出现3个教皇同时在位并彼此诅咒的窘况。
在教皇和皇帝“两败俱伤”之后,德意志诸侯这个等级试图独霸帝国。他们中的首领,由七个诸侯组成的“选侯”或者“选帝侯”等级,通过查理四世于1356年颁布的《黄金诏书》独霸了皇帝选举权。
在“选侯”等级中,三个莱茵大主教占据了七选侯里的三席,而其中的美因茨大主教作为德意志“大宰相”,成为选侯会议的主席和召集者。通过与诸侯们团结一致,以选侯为首的德意志诸侯们,又于1495年成功地让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皇帝接受了“帝国等级会议”的约束。
于是到15世纪末,诸侯们把持了德意志的权力,他们当中多数是教会诸侯。几个世纪里,皇室的不断赏赐和教会自身的经营,还有世俗诸侯贵族所捐献给修道院的财产和土地,让德意志的教会掌握了惊人的财富,并在实际上不受约束。也正是在“无为”的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统治末期,1517年10月31日,一个奥古斯丁会修士张贴了自己的《九十五条论纲》,宗教改革的风暴来临了。
宗教改革的“天时地利”
在德意志领土上,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几乎无所作为。他的成就首先表现在哈布斯堡王朝在德意志之外的领土扩张,其次是作为德意志东南部的领主所取得的功绩。由于此后哈布斯堡王朝君主连续登上帝国皇位,这两点实际上也决定了在此后德意志宗教改革和信仰斗争中皇帝的立場和政策。
哈布斯堡王朝的海外扩张,始自马克西米利安和勃艮第公爵“大胆查理”的女儿玛丽的订婚。当统治尼德兰(今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一带)的“大胆查理”意外战死后,马克西米利安只身前往尼德兰和玛丽结婚,并率领尼德兰的军队战胜了试图夺取尼德兰的法国国王。再后来,马克西米利安的儿子、美男子菲利普,娶了西班牙公主胡安娜,这桩婚姻为哈布斯堡带来了对西班牙、那不勒斯、西西里、撒丁和西属美洲的继承权。

1516年,菲利普与胡安娜的长子查理,继承了来自勃艮第公爵家族和西班牙王室的全部财产。3年后,当马克西米利安皇帝逝世时,选帝侯们在查理和法国的弗朗索瓦国王之间犹豫不决,但最终选择了查理(作为皇帝他被称为查理五世)。不过,查理也被迫签署《选举誓约》,保证绝不破坏帝国已经存在的制度,不把自己的外国军队带到德意志—以此保证不破坏德意志诸侯的势力。endprint
1521年查理五世第一次来到德意志,在沃尔姆斯帝国会议上召见了马丁·路德。作为一个讲法语的勃艮第贵族,查理五世对只能讲拉丁语和德语的路德的宗教观和神学论点既没能理解,也没有兴趣。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首先是哈布斯堡与法国君主的传统矛盾,这个矛盾把他深深卷入在尼德兰和意大利与法国国王的战争里。另一个重要事务是奥斯曼帝国的威胁。1521年,也就是查理五世在沃尔姆斯宣布路德不受法律保护的那一年,奥斯曼帝国攻陷贝尔格莱德;1526年莫哈齐战役后,包括维也纳在内的哈布斯堡世袭领地,陷入奥斯曼人的陆上威胁。
此外,作为南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君主,查理五世身不由己地陷入了传统上皇帝和教皇围绕南意大利的领主之争。现实的矛盾抵消了教皇通过查理五世重振德意志人信仰的意图;出于对德意志皇权在意大利重现的恐惧,德意志因宗教改革陷入混乱,反而更符合教皇的利益。
皇帝无暇顾及,教皇态度暧昧,决定了沃尔姆斯帝国会议以后如日中天的德意志诸侯阶层纷纷投入宗教改革。宗教改革不仅仅意味着诸侯可以夺取和掠夺自己领地上的修道院,还意味着世俗诸侯可以通过宗教改革夺取教会诸侯的领地,甚至教会诸侯可以借机把不能世袭的教会诸侯领地变成自家世袭的世俗领地。比如最特殊的教会诸侯“条顿骑士团”,就被骑士团大首领通过宗教改革直接变成了由大首领自己担任公爵的世俗的普鲁士公国。
在这风起云涌的20多年间,皇帝虽然一再重申对马丁·路德和新教教义的谴责,却始终力有未逮。他被五花八门的领地和敌人拖进大大小小的战争。1529年当他终于战胜法国时,奥斯曼军队又向维也纳大举进攻。
在这个过程中,随着皇帝势力的不断扩张,德意志的新教诸侯开始对皇帝象征性的谴责感到不安,于是结成“施马尔卡尔登同盟”。而法国虽然是一个天主教王国而且正在迫害本国新教徒,也还是加入了这个同盟。
即便如此,查理五世依然隐忍不发,直到1544年最后一次战胜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并用条约禁止法国干预德意志宗教改革之后,他才终于决心用武力解决德意志的宗教纷争,以重振德意志的皇权。然而,曾经追随他的天主教诸侯却秘密地和幸存的新教諸侯结成联盟,在法国新国王亨利二世的支持下,于1552年发动了诸侯革命,把皇帝打翻在地。查理五世3年后退位,其毕生追求的普世皇权梦想至此破灭。
“三十年战争”后的宗教宽容
1555年查理五世退位,退位之前他把哈布斯堡王朝德意志世袭领地,留给了此时已经登上波西米亚和匈牙利王位的兄弟斐迪南;后者登上皇位之后,称为斐迪南一世。剩余的广阔领土,查理五世都留给了自己的儿子菲利普;菲利普作为西班牙国王,称为菲利普二世。
哈布斯堡“德意志”和“西班牙”两系分立后,斐迪南皇帝手中的力量,完全无法和查理五世相比,因此他放弃了查理五世对重振帝国的想法,转而承认德意志诸侯的地位,并促使德意志诸侯和解。
1555年斐迪南一世促使德意志的诸侯签署了《奥格斯堡和约》。和约首先放弃了德意志信仰统一的要求,承认了新教路德宗和天主教的平等地位,同时承认了诸侯对领地之内信仰状况的支配权,也就是“教随国定”的原则。
从1555年到1618年之间的半个世纪里,哈布斯堡王朝垄断着“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但并不明确介入德意志的信仰斗争。这一阶段德意志信仰斗争的主角,终于由德意志各邦诸侯扮演。
1618年波西米亚起义后,西南德意志最大的新教诸侯—莱茵行宫伯爵,于次年被起义者选为波西米亚国王。皇帝因为手中最大的世袭领地和唯一的选侯票被夺去,不得不发动战争;而新教和天主教同盟,以及他们所能争取到的外国同盟者也纷纷投入战争,“三十年战争”随之而来。
当战争最终告一段落时,《威斯特伐利亚和约》重申了“教随国定”的原则。在漫长宗教战争的废墟上,和平同等地降临在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头上。在南德城市奥格斯堡,一切权力都由两大教派的人共同行使;而在主教兼任邦君的主教管区奥斯纳布吕克,邦君则由不同教派轮流产生。在天主教的南德意志,新教的孤岛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而在新教的北德意志,幸免于难的天主教修道院也重新焕发了生机。
从1517年到1648年,德意志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信仰斗争和宗教战争,见证了诸侯阶层崛起、而皇权瓦解的独特进程。随着战争的加剧、杀戮的扩大,普通民众对信仰的追求渐渐淡漠,最终被迫切的恢复和平与秩序的需求取代。原本为了让诸侯成为宗教的保护者而提出的“教随国定”或者“谁的领地信谁的教”,反而成了和解的途径。
战争本身是诸侯领地走向“帝国之内的独立王国”的途径,而战争结束时的和解手段又进一步推动了这个过程。民众不再追求信仰的统一,皇帝也不再追求振兴皇权,诸侯再一次取得了胜利。结果就是在曾经宗教最深入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德意志,在信仰热忱最高,对不同信仰也最缺乏容忍的德意志,宗教宽容反而借助国家本身的破碎而最先降临。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