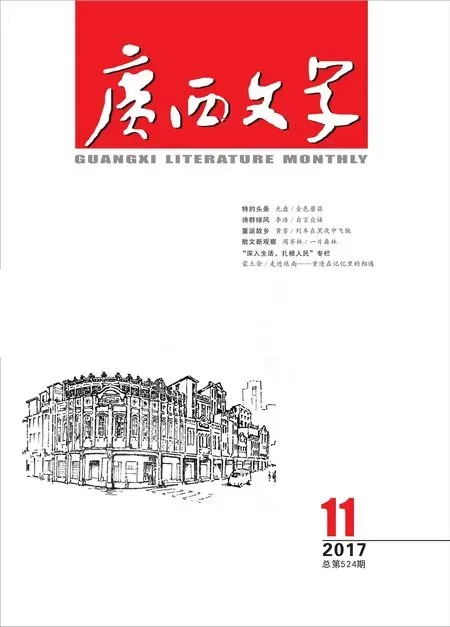刘永飞小小说二题
2017-10-22刘永飞
刘永飞/著

老 王
老王因为当兵留在这个城市。后来成家立业,结婚生子;后来因为儿子结婚,居住不便,分开另过;再后来因为儿子有了儿子,儿子的儿子缺人照料,在儿子的要求下,老王又跟儿子住在一起。
这时的老王刚刚退休,家务和孩子多由老伴照看,老王闲得无聊,就买了把弦子,在家里咿咿呀呀地拉起来。年轻时的老王也算个文艺青年,尤其在部队时经常参加演出。后来转到地方工作,一忙,这个爱好就丢了,一丢几十年,再捡起来,才发现不是一般的生疏,简直就是回到了原点。于是,老王空闲下来就咿咿呀呀地拉,他相信拉熟练了就好了。
老王是河南人,妻子却不是,后来生了儿子,儿子娶了媳妇,媳妇又生了孙子,这一家五口人,能听懂家乡戏的只有他自己,所以,他一把弦子拉得全家人心慌意乱,差点就鸡飞狗跳。有一天,他在客厅里拉着拉着儿子回来了。儿子说,爸,你去小房间拉吧。老王愣了一下,就去了小房间。刚拉了几分钟,儿子砰的一声帮他带上了门。
晚上睡觉的时候,老王和老伴说起这事儿,他说儿子挺理解人的,知道拉弦子需要清静。老伴说,算了吧你,他哪是关心你呀?他是不想让你打扰他看电视。老伴并没有看老王的反应,而是看着墙壁说,老王,咱们能不能不拉了?你不觉得拉得太难听了吗?我也就算了,可是儿子和媳妇听着心烦呀!老伴一席话说得老王半天没言语。其实他们并不知道,老王拉的并不是简单的弦子,他拉的是乡愁,或是寂寞。
其实老王从小就喜欢听家乡戏,也喜欢唱,后来年纪轻轻离开家乡,听戏的机会少了,眼见人老了,对家乡戏着魔起来。现在,每当他拉弦子的时候,他都会想到故乡,想到童年,想到母亲。可惜几十年过去了,亲人都离他远去,他也只能在弦音中回到故乡,回到童年,回到母亲的怀抱。
接下来的几天,吃完饭,搞好家里的卫生,老王就拎个包,来到小区对面的公园,在一个最偏僻的角落,打开便携式V C D,他就跟着人家的伴奏拉。于是,来小区的人常会听到《花木兰》《朝阳沟》《三哭殿》等一些经典的豫剧唱段。
再后来,老王通过老乡认识了一大帮票友。票友们大多都是像他一样从故乡来到这个城市,或定居,或工作,或求学,他们有的喜欢拉,有的喜欢唱,大家一拍即合,成立了 “戏迷会”,他们约定每个周日在一个公园里聚会。这时候,老王的弦子拉得仍不好,但他可以跟在“头把弦子”后面“滥竽充数”似的学习。不论弦子拉得好坏,也不论嗓子唱得如何,大家玩得都很尽兴。于是,每到周日,老王骑车半个城市去聚会,成了雷打不动的日程。
这些都被老婆、儿子、媳妇看在眼里,老伴还没说啥,儿子先说话了,让她管管父亲,说什么这么大年纪了,骑车转悠大半个城市,万一出点事咋办?这不是给孩子找麻烦吗?我也是纳了闷了,就爸那水平,别人还能让他加入乐队?
于是,儿子总找这样那样的理由不让老王出去。无奈,老王只能隔三岔五地去。后来,儿子经营的饭店遇到困难,每天的脾气阴晴不定,老王索性就不出去了。
一天,一大帮票友突然来到他家里,还拎着大包小包的礼物。老王的儿子看他们一个个打扮得“三教九流”似的,心里老大不痛快,虽不好意思赶人家走,但是脸色十分难看。
票友们问老王为啥不来了,老王不好意思说儿子不让,就说儿子的生意遇到些困难,想在家帮帮他。他们又问遇到什么困难。他就实话实说了。原来,老王的儿子在镇政府的对门开了一家饭店,生意挺好,后来就成了镇政府的“招待点”,但是要记账,不知不觉一盘账,政府竟欠他一百多万元,眼看着资金困难开不下去了,就去要账,可是人家推来推去的根本没有还钱的意思,你说咋办?
这时,头把弦子老秦说话了,问他哪个镇,老王就说了。老秦当即走上阳台打了个电话,也不知是对谁发了一通火。老秦挂上电话不一会儿,老王的儿子就接到了镇领导的电话,对方让他周一去镇政府办手续结账,还说了一些有眼不识泰山的话。
事后,老王儿子的生意又活了,而且越来越红火。现在,儿子不能看到老王在家待着,也不管是什么时候,这小子都会冷不丁地冒出来一句:“爸,你咋不跟秦叔去拉弦子呢?”
看着儿子那觍着的脸,老王哭笑不得,他知道,儿子接纳了他的爱好是假,让他巴结秦副书记才是真。老王这一辈子最怕巴结人。于是,他以身体不适为由,再也不去“戏迷会”了。
但他仍旧拉弦子,多是在小区后面的公园,偶尔也边拉边唱:
自从你两眼一闭,
撒手而去,
这个家弄得我措手不及。
白天当爹爹,
拉弦去卖艺,
夜里又当娘,
缝补儿的衣。
孩儿想他娘我想俺的妻,
搂着我那两个儿哭哭啼啼
……
王 叔
自从和老王相识后,我开始喊他王叔。
那是个星期天,我带孩子到小区后面的公园里玩。远远地,从公园的一角传来一阵阵悲悲切切的拉唱声,唱的是现代豫剧《倒霉大叔的婚事》里的“哭坟”片段。
不知为何,年过四十的我突然对家乡戏迷恋起来,一个人独自做家务事或散步时,都会哼唱两句。还记得年前的一天傍晚,在我居住的前一排的房子里,忽然响起一阵板胡的声音。他拉的是河南豫剧,我料定他一定是家乡人。虽然他(她)拉得断断续续不太流畅,但这丝毫不影响我跟着这旋律哼唱。只可惜半年后,这声音就再没有响起过。
此时的我为能在异地他乡听到如此纯正的家乡戏欣喜不已。于是,我“强迫”着两岁半的儿子离开沙坑,循着板胡声找去。“……自从你两眼一闭,撒手而去,这个家弄得我措手不及。白天当爹爹,拉弦去卖艺,夜里又当娘,缝补儿的衣。孩儿想他娘我想俺的妻,搂着我那两个儿哭哭啼啼……”
绕过一行一人高的绿化带,我看到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老人双目紧闭,满脸悲切,拉唱到动容处身体止不住地颤抖,一头花白的乱发迎风起舞。
我被老人动情的演唱感染了,听得如痴如醉,听到动情处,我的眼底跟着潮湿起来。一定是我入戏太深了,一定是悲切的表情出卖了我。当琴声戛然而止时,老人笑了,他说:“你也是河南哩?!”
就这样,我和老人坐到一起聊起来。一聊才知道,他的老家距我的老家只有百十里的路程,也知道了他是因为当兵才留在这座城市。我们接着聊起了《花木兰》《穆桂英挂帅》《朝阳沟》等戏曲,聊起了常香玉、马金凤、牛得草等豫剧名家。
我们犹如他乡遇故知般,聊得热火朝天,聊得我的儿子跑得无影无踪也没有发觉。我跟他说,我小时候喜欢家乡戏就是图个热闹,生旦净末丑,脸上涂得花花绿绿,有的翻滚跳跃,有的楚楚动人,仅此而已。
我还想说下去,老人却接过话茬,他说:“不瞒你,现在我拉弦子的时候,都会想到老家,想到小时候,想到老母亲,可惜啊,亲人们都走了,故乡也回不去了!”老人说到这里声音有些哽咽。很快,他就发现了自己的失态,然后抹了一把眼睛说:“白闲着,咱弄两句呗!”老人说着话,手里弓弦一动,弦音缭绕,勾得我嗓子直发痒,可惜我仅仅是喜欢而已,若真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开嗓,我还真是抹不开面子。
随后我向老人说起大约半年前的事情,说我住的小区也有个河南人,每次他一拉弦子,我的骨头都要酥了,几次产生要去拜访的念头,但怕打扰人家的生活,后来我再也没有听他(她)拉过,大概是搬走了吧。
老人问我住在哪个小区,我说就前面的这个。老人又问我住在几号。我答了,老人笑了,他说,那就是我拉的。我说,不对呀,那时候拉得可不好,断断续续的,估计是弦子不好。老人说,不是弦子不好,是拉得生疏。我问他这段时间咋不在家里拉了,他说老婆孩子都不喜欢,说太难听。难听?我说是他们根本不懂豫剧,也不喜欢,在家里怕打扰他们,所以就在公园里拉拉,他们现在是上海人,不是河南人喽。
临走时,老人说他姓王,让我喊他老王,但我离去时,喊了他王叔。王叔说,没事时来家坐坐,如果想听家乡戏就来公园,他每天基本上都在。
我和王叔就这样认识了,每个双休日,我都会来公园走走,听他拉弦子。每次他都鼓励我唱几句。尽管有些段子在家里练过无数遍,可是王叔的弦子一响,我就像被人掐住了喉咙似的发不出声音。王叔就笑,他说多听听就好了。
对我来说这是一段美好的日子,可是这样的美好突然有了变化,因为之后的日子我再也没有看到过王叔。刚开始以为他忙走不开,但后来一直碰不到人,我就产生了去拜访老人的念头。
那一天,我鼓足勇气摁响了王叔家的门铃。门开了,开门的不是王叔,但可以断定这人就是王叔的儿子。我说明来意,年轻人哦了一声,把我让进屋里。刚进屋,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了,因为我看到王叔被镶进了黑框摆放在桌子上,这才知道老人出了车祸。
坐下去许久,我没言语,脑子里满满的都是老人的弦音和音容笑貌,最后心乱如麻地说了些安慰的话。我要告辞,年轻人把我送到门外。我转身正要离去,他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叫住我,他回到里屋,抱出一个长长的盒子,盒子很熟——这是王叔的板胡。
经过风吹日晒的盒子已经很破了,多处地方出现龟裂。年轻人说,我父亲让我把这个给您。我吃惊得说不出话来,我问老人是怎么说的,他说他父亲从出车祸到去世,就说了一句话:
“把板胡给一个小老乡!”
年轻人在递给我板胡的时候,神情凝重,他的一只手在不停地抚摸着这个斑驳的盒子,像是在抚摸一只粗糙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