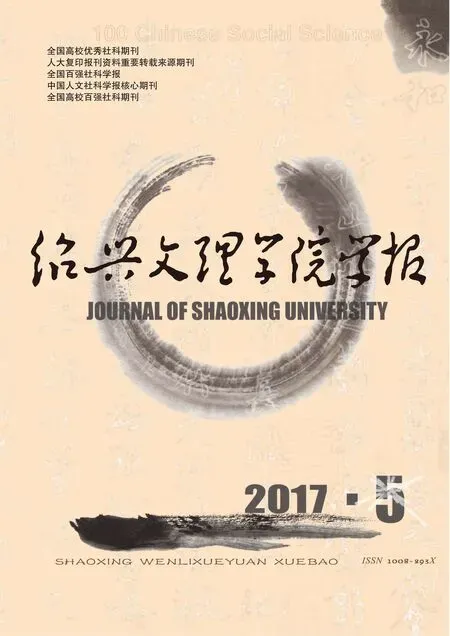“肉薄”再证
2017-10-20呼叙利
呼叙利
(绍兴文理学院 人文学院,浙江 绍兴312000)
“肉薄”再证
呼叙利
(绍兴文理学院 人文学院,浙江 绍兴312000)
“肉薄”与“蚁傅(附)”实质上均是“人攻”。“蚁傅(附)”之“傅(附)”即“傅(附)城”之“傅(附)”,为“攀附”义;而“肉薄”之“薄”即“薄城”之“薄”,为“攻击”义。“肉薄”与“蚁傅(附)”都是名状类型的状中结构。攻城战“肉薄”只做状语,而清末民国之初出现的非攻城战“肉薄”只做谓语,是攻城战“肉薄”实现其做谓语的潜能、打破与“械攻”的矛盾关系演变而来的。
肉薄;蚁傅;蚁附;薄城;傅城;附城;肉攻;人攻
《“肉薄” 补证》(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一文主要采用逻辑学方法,并结合语言学方法,从“肉薄”与“蚁傅(附)”的关系:“攻城具”等方面,对笔者《“肉薄”补释》(古汉语研究,2010年第1期)一文进行了补证。本文则主要采用语言学方法,对“薄城”与“傅(附)城”的关系、“肉薄”之“薄”与“薄城”之“薄”的关系、攻城战“肉薄”与非攻城战“肉薄”的关系等进行再证,对材料与用例的鉴别问题进行探讨,对相关问题进行进一步研究。
一、“薄城”与“傅(附)城”
拙文《“肉薄”补释》主要依据普通逻辑学概念原理,采用逻辑学方法为主、语言学方法为辅的研究策略,这样可以更容易解决“肉薄”释义问题。即使主要采用语言学方法,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问题。“肉薄”释义的难点就在于对语素“薄”义项的确定,下面通过对“肉薄”出现之前典籍中“薄”用例的梳理,找出客观依据判定“肉薄”之“薄”的意义。因为一个词语的语素和构成方式都只能来源于同时代或前时代已经存在的语素和构成方式,而不会凭空产生,更绝对不会来源于一千六七百年后的现代汉语中许文所谓的“深层结构”。当然“肉薄”出现之后典籍中的“薄”与“肉薄”处于共存的使用状态,对其进行研究也可进一步印证。同时,由于“肉薄”与“蚁傅(附)”有着密切的内在关系,将两者进行比较,将“薄”与“傅(附)”进行比较,对准确解释“肉薄”也有重要价值。
方一新先生在《东汉魏晋南北朝史书词语笺释》中确证“薄”有“攻击,冲击”义[1],又说:“‘薄’有迫近义……也有搏击义,《易·说卦》:‘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攻击、冲击义当即由此演变而来。《淮南子·兵略》:‘击之若雷,薄之若风。’是此义之早见者。”[1]由此可知,方先生认为“薄”的“攻击,冲击”义是由“搏击”义演变而来的。其实“雷风相薄”例中的“薄”亦为“攻击”义,而非“搏击”义。“攻击”为动作方对另一方主动实施的行为,而“搏击”为动作方对另一方的攻击实施抵御并反击的行为,二者的语义特征有明显区别。“雷”冲击“风”,“风”冲击“雷”,无抵御并反击的特征。又如《宋史·李邈传刘翊附传》:“金人攻广信、保州不克,遂越中山而攻真定。翊率众昼夜搏战城上。金兵初攻北壁,翊拒之,乃伪徙攻东城,宣抚使李邈复趣翊往应;越再宿,潜移攻具还薄北城,众攀堞而上,城遂陷。”(13179页)此例中“搏战”绝非“薄战”,是由防守方对金人“攻真定”的抵御并反击,下句“薄北城”之“薄”具有实施主动攻击的特征。《淮南子·兵略》中“薄”与“击”对文同义,均指军队对敌人的主动攻击,“薄之若风”义为“像风一样攻击敌人”。《汉语大词典》“薄”义项“搏击;拍击”所引用例除《韩非子·解老》外均为“攻击,冲击”义。(卷9-573页)(案:《韩非子·解老》例“物有理不可以相薄”之“薄”实为“迫近,靠近”义,“相薄”具体义为“相近,相混”。)“攻击,冲击”义为“靠近”义的引申。许剑宇先生亦认为“‘薄’的‘进攻’义本来就是由‘靠近’义引申而来”[2],显示出与方一新的说法有明显差异。
目前对“肉薄”的释义,主要有方先生“体近”说、《汉语大词典》“徒手搏或短兵搏”说[3]、李丽先生“近战”说[3]、笔者“人攻”说[4]等,主要体现了对“薄”看法的差异,即“靠近”义、“搏击、搏斗”义、“攻击”义,其中方先生的“靠近”是士兵身体与身体靠近,而李先生的“靠近”却是士兵肉体与敌人或敌城的靠近,所以对“薄”意义的判定是正确解释“肉薄”的基础。判定某个词语或语素的义项,除了首先要确定这个词语或语素的义项系统中“有某义”外,还必须利用语言环境中的某些客观因素无可置疑地判定其“是某义”,也就是“内外结合,以外定内”。“有某义”提供了一个可供选择的义项范围,这是判定“是某义”的前提。然后在此基础上,利用语言环境中多种客观因素无可置疑地判定其“是某义”,这就充分利用语言环境对义项的选择和明确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根据“有某义”原则,可以否定“徒手搏或短兵搏”说,因为“搏斗”义不是“薄”的义项,这可以通过对上古、中古与近代典籍中“薄”用例的梳理进行判定。确立“有某义”必须有无可置疑的客观依据,不能以“两解”“亦通”等这些带有主观性的东西为依据来确立义项。另外,词典上“有某义”和客观语言事实上“有某义”是不同的概念,利用词典释义、名家成说等进行学术研究必须与客观语言事实进行参照。而“靠近”义、“攻击”义均为“薄”的义项,所以就需要进一步根据“是某义”原则在语境中找出一些合理因素进行判定。存在一定数量的用例能够无可置疑地确定“肉薄”为“身体挨着(身体)”义或者“肉体靠近(敌人或敌城)”义吗?许文用其所谓的现代汉语中的“深层结构”证“薄”为“靠近”义,陶文用“林薄”“榛薄”证“薄”为“靠近”义,这些“论证”能够无可置疑地证明“肉薄”之“薄”是“靠近”义吗?“近战”说的依据又是什么?拙文《“肉薄”补释》依据逻辑学概念原理,通过对典籍用例的梳理和分析,确定“肉薄”与“车攻”等攻城方式存在反对关系,进而判定其与“械攻”攻城方式存在同属种概念关系的“人攻”攻城方式,从而在“薄”的合理义项范围内确定其为“攻击”义。从许文“但呼文随后提出‘薄’有‘林薄’‘迫’‘靠近’‘攻’等多种意义,因而‘肉薄’的‘薄’就可以解释为‘攻’,这一点尚不能令人信服”[2]的表述来看,许先生对拙文判定“薄”“有某义”的论述还是清楚的。
在历代史书、兵书等典籍中,“薄”的“攻击,冲击”义用例大量存在;毋庸讳言,在某些具体用例中,“攻击,冲击”义与“迫近,靠近”义的确难辨别,但无论如何都与“搏击、搏斗”义毫无关涉。同时“攻击,冲击”义与“迫近,靠近”义虽然在有些具体用例中难辨别,但也并非不能区别,关键要通过对其句法特征、语义特征、语用特征等研究从而确立一些标准。

(1)子上欲涉,大孙伯曰:“不可。晋人无信,半涉而薄我,悔败何及,不如纾之。”乃退舍。
(《左传·僖公三十三年》,1834页)
(2)使者目动而言肆,惧我也,将遁矣。薄诸河,必败之。
(《左传·文公十二年》,1852页)
(3)敌近而薄我,欲去无路;我众甚惧,为之奈何?
(《吴子·应变》,9页)
(4)军至瓦官寺,与义军游逻相逢,游逻退走,贼遂薄垒。
(《宋书·柳元景传》,1987页)
(5)军次巴陵,营顿未立,纳潜军夜至,薄营大噪,营中将士皆惊扰,毅独与左右数十人,当营门力战。
(《陈书·樊毅传》,415页)
(6)艺兵频胜而骄,进袭其营,建德列阵于营中,填堑而出,击艺败之。建德薄其城,不克,遂归洺州。
(《旧唐书·窦建德传》,2240页)
(7)自是贼一意长围,以持久困官军,不复薄城。
(《宋史·李全传下》,13846页)
(8)复造云梯及旱船,昼夜薄城,城中亦以炮石击毁之。
(《明史·永宁宣抚司传》,8055页)
(9)同治元年,从克青阳,乘胜攻石埭,云庆率士卒负板薄城,蚁附而登,克之。
(《清史稿·鲍超传娄云庆附传》,11987页)
例(1)中“悔败何及”可证“半涉而薄我”之“薄”为“攻击”义,如果是“靠近”,不会导致“败”的结果。例(2)中“必败之”可证“薄诸河”之“薄”亦为“攻击”义。此例杜预注:“薄,迫也。”(1852页)应不确。“靠近”并不会导致“败”的结果。例(3)中“敌近而薄我”之“近”可证“薄”为“攻击”义。
由此可知,例(1)“半涉而薄我”、例(2)“薄诸河”、例(3)“敌近而薄我”等均属于“薄人”类用例,加上方先生所选取的大量中古文献用例,均证明“薄人”类用例在古籍中习见。而例(4)“贼遂薄垒”、例(5)“薄营大噪”、例(6)“建德薄其城”、例(7)“不复薄城”、例(8)“昼夜薄城”、例(9)“云庆率士卒负板薄城”等均属“薄城”类用例,这也证明“薄城”类用例习见。“薄人”类用例与“薄城”类用例中,“薄”有一个明显的语义特征,那就是进攻方士兵主动对敌人或敌方军事目标实施攻击行为。
同时,在古代文献中还存在大量的“傅城”类用例,在战国时期的文献《墨子》中已见,在近代文献中更是习用。如:
(10)敢问适人强弱,遂以傅城,后上先断,以为(法)程。
(《墨子·备蛾傅》,565页)
(11)环卒,吴少诚寇许州,元阳城守;外无救兵,攻围甚急,而终不能傅其城,贼乃罢兵。
(《旧唐书·孟元阳传》,4062页)
(12)兵机事,以速为神。今士始集,铣不及知,若乘水傅垒,是震霆不及塞耳,有能仓卒召兵,无以御我,此必禽也。
(《新唐书·李靖传》,3812页)
(13)建德怒曰:“我傅其城,犹不下,劳费士旅,何可赦?”
(《新唐书·窦建德传》,3700页)
(14)已而金兵攻城东隅,薄南门北角,再兴与宗政、刘世兴各当一面,大战数十合,大败金兵。金帅完颜讹可拥步骑数万傅城,再兴与宗政纵之涉濠,半渡击之。
(《宋史·扈再兴传》,12210页)
(15)十一月辛丑,大兵以攻具傅城,有司尽籍民丁防守,不足则括妇女壮健者,假男子衣冠使运木石。
(《金史·完颜仲德传》,2609-2610页)
(16)令都督黄中等将死士,人持炬火铜角,夜四鼓,越重濠,云梯傅其城。都指挥蔡福先登,士蚁附而上,角鸣,万炬齐举,城下兵鼓噪继进,遂入城。
(《明史·张辅传》,4220页)
在典籍中,“傅城”也作“附城”,如:
(17)从木华黎攻通州,献计,一夕造砲三十、云梯数十,附城,州将惧,出宝货以降。
(《元史·攸哈剌拔都传》,4380页)
(18)贼障革裹竹牌钩梯附城,垒土山,上架蓬荜,伏弩射城中。燮元用火器击却之。
(《明史·朱燮元传》,6441页)
以上用例可以确证“蚁傅(附)”之“傅(附)”即“傅(附)城”之“傅(附)”,为“攀附”义,在攻城战中“攀附”敌城实质上属于作战行为。
但是在古代典籍中,“傅(附)城”确实也有“近城”义的少数用例,如:
(19)漠谷险隘,必为贼所邀,不若取乾陵北过,附柏城而行,便取城东北鸡子堆下营,与城中掎角相应。
(《旧唐书·浑瑊传》,3705页)
(20)宗权素壁上蔡以扼险要,全忠拔其壁,遂围蔡州,傅城而垒,以羸兵诱贼。
(《新唐书·秦宗权传》,6465-6466页)
(21)贺德伦闭城不出,李嗣昭日以铁骑环其城,捕刍牧者,附城三十里禾黍皆刈之。(《资治通鉴·唐纪七七·昭宗圣穆景文孝皇帝中之上》,8527页)
(22)至铜州,高丽将康肇分兵为三以抗我军:一营于州西,据三水之会,肇居其中;一营近州之山;一附城而营。
(《辽史·耶律盆奴传》,1340-1341页)
那么,怎么区别“傅(附)城”的“攀城”与“近城”义呢?“攀附”义和“靠近”义均为“傅(附)”义项,能够“以内定内”吗?只有“以外定内”,即研究词语之间的外部关系,找出两者在语义特征、句法特征、语用特征等方面的差别,确立判定标准,才能够进行有效辨别。“攀附”的对象为敌方军事目标即城、营、垒等凸出于地面的防御工事,“攀附”是从下往上的靠近,而“靠近”义可以是进攻方对敌人、敌方城墙的靠近,也可以是对自己某些人或事物的靠近,或者是某物对某些人、事物的靠近;“傅(附)城”之“攀附”具有实施作战行为的特征,而“靠近”义不具备实施作战行为的特征。根据这些区别特征,也并不难对“傅(附)城”之“攀附城墙”义与“靠近城墙”义的用例进行辨别,虽然“攀附”义也是“靠近”义从一般到特殊的引申。如果在一些具体用例中确实不能够找到足够的客观证据证明是“攀城”义还是“近城”义,那么可以用语境标准进行辨别:如果在攀附敌城的语境中出现的用例,除非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其不是“攀城”义,那么就判定其为“攀城”义;如果在非攀附敌城的语境中出现的用例,除非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其不是“近城”义,那么就判定为“近城”义。
更有趣的是,在古代典籍中,“薄城”除了有“攻城”义的大量用例外,也有“近城”义的个别用例。如:
(23)行密薄城而屯,用之以兵属之。彦以骑兵背城战,行密卧帐中,令曰:“贼近,报我。”
(《新唐书·杨行密传》,5452页)
类似的表达方式还有“薄我城下”“以薄城下”,如:
(24)敌人分为三四,或战而侵掠我地,或止而收我牛马,其大军未尽至,而使寇薄我城下,致吾三军恐惧,为之奈何?
(《六韬·豹韬》,8册-1026页)
(25)是时,北风正急,贼乃随风推桥以薄城下,贼三千余人相继而登。
(《旧唐书·浑瑊传》,3706页)
例(24)中“致吾三军恐惧”可证“薄我城下”之“薄”为“靠近”义,尚未实施作战行为,例(25)中“随风推桥以薄城下”指“桥”靠近城下。
“肉薄”在攻城战语境中的句法功能均为做状语,而“蚁傅(附)”除做状语之外,还有做谓语、介词宾语、动词宾语等用例。如:
(26)客冯面而蛾傅之,主人则先之知,主人利。
(《墨子·备城门》,530页)
(27)备蛾傅为县脾(陴),以木板厚二寸,前后二尺,旁广五尺,高五尺。
(《墨子·备蛾傅》,565页)
(28)于是段齐城、高唐为两,直将蚁傅平陵。
(《孙膑兵法·擒庞涓》,册1-85页)
(29)虏贪而少虑,必悉力攻小城,图破此堰。见堑狭城小,谓一往可克,当以蚁附攻之。
(《南齐书·垣崇祖传》,462页)
例(26)中“蛾傅”做谓语,例(27)中“蛾傅”做动词“备”的宾语,例(29)中“蚁附”做介词“以”的宾语。做状语是“蚁傅(附)”的最基本句法功能,用例也最多。而将“傅(附)”与“蚁傅(附)”后修饰的动词性词语、“薄”与“肉薄”后修饰的动词性词语之关系进行探究,也发现一些有意思的现象。如:
(30)赵兵四面蚁附缘城,慕舆根等昼夜力战;凡十余日,赵兵不能克,壬辰,引退。(《资治通鉴·晋纪一八·显宗成皇帝中之下》,3020页)
(31)魏人果蚁附攻小城,崇祖著白纱帽,肩舆上城,晡时,决堰下水;魏攻城之众漂坠堑中,人马溺死以千数。(《资治通鉴·齐纪一·太祖高皇帝》,4236页)
(32)除夕,大兵登城,战少却,旋蚁附而登,衡守尹谷及其家人自焚,芾命酒酹之。
(《宋史·李芾传》,13255-13256页)
(33)诸军缘木攀萝,蚁附而上,四面夹攻,连日鏖战,贼不能支。
(《明史·浔州传》,8221页)
从以上用例可以看出,“蚁附”做状语,修饰的多为动词性词语如“缘城”“登”“上”,与“附”有密切关系。如例(30)“蚁附缘城”之“蚁附”修饰“缘城”,“附”为“攀附”义,“缘”亦为“攀附,攀缘”义,可见在具体的用例中并不避忌许文所谓的“语义重复之病”。同时,在古代典籍中极难找到“蚁傅(附)傅(附)城”类的用例,这说明古人在表达上有倾向于避忌“词语重复”却不避忌“语义重复”的特点。少数用例如例(31)“蚁附攻小城”之“蚁附”修饰“攻小城”,“攻”更明确体现出“蚁附”属于作战行为的性质。“蚁附”所修饰的中心语中动词的受事均为“城”“营”“垒”等,这与“附”的受事是相同的;施事与“附”的施事也是相同的,均为攻城方士兵。
而“肉薄”与“蚁傅(附)”大致具有相同的句法特征、语义特征,但也表现出一些个性,如:
(34)虏肉薄攻城,死者甚众,宪将士死伤亦过半。
(《宋书·索虏传》,2344页)
(35)既至,柴栅已坚,仓猝无攻具,便使肉薄攻之。
(《宋书·柳元景传》,1987页)
(36)宝结营拒战,广之等肉薄攻营,自晡至日没,大败之,杀伤千余人,遂退,烧其运车。
(《南齐书·王广之传》,547页)
(37)魏军乃肉薄登城,坠而复升,莫有退者。杀伤万计,死者与城平。
(《南史·臧焘传臧质附传》,515页)
(38)景帅船舰并集北寺,又分入港中,登岸治道,广设毡屋,耀军城东陇上,芟除草芿,开八道向城,遣五千兔头肉薄苦攻。城内同时鼓譟,矢石雨下,杀贼既多,贼乃引退,世祖又命平北将军胡僧祐率兵下援僧辩。是日,贼复攻巴陵,水步十处,鸣鼓吹唇,肉薄斫上。
(《梁书·王僧辩传》,625-626页)
(39)发地雷,裂城百丈,挥军肉薄而登,忽中枪贯脑,踣而复起,部将刘士奇继之,遂克嘉兴。
(《清史稿·程学启传》,12076页)
在少量用例中“肉薄”修饰的动词性词语为“登城”“斫上”“登”等,揭示出“肉薄”攻城是通过从下而上攀附敌城的具体动作来实施的;而大量用例中“肉薄”修饰的却为“攻城”“攻之”“攻营”“苦攻”等,动词与“薄”同义,则揭示出其属于作战行为的本质属性。“肉薄”所修饰的中心语中动词的受事均为“城”“营”“垒”等,这与“薄”的受事是相同的;动词的施事与“薄”的施事也是相同的,均为攻城方士兵。而在古代典籍中,也极难找到“肉薄薄城”之类的用例,这也证明“肉薄”构词为什么选用“薄”而不选用“攻”,实质上“肉薄”就是“肉攻”,古人在表达上一般倾向于避忌“词语重复”,在可能出现“词语重复”时往往尽可能选用同义或近义的词语。
由此可知,“蚁傅(附)”修饰的动词性词语多为攻城方从下而上攀附敌城的具体动作,少量为攻击动作;而“肉薄”修饰的动词性词语少量为攻城方从下而上攀附敌城的具体动作,而大量的却是攻击动作。“人攻”攻城是通过由下而上攀附敌城的具体动作来实施,而这种由下而上攀附敌城的具体动作本质上属于作战行为。两者相比,“肉薄”体现出来的属于作战行为的本质特征更为明显,这也证明了在早已存在表达“人攻”攻城方式的“蚁傅(附)”这一词语的条件下,又产生了同样表达“人攻”攻城方式的“肉薄”一词的必要性,“蚁傅(附)”与“肉薄”在表达上具有不同价值,因此在中古近代文献中并行不替。
在语义结构中,义为“攻城方士兵像蚂蚁一样攀附敌城”的“蚁傅(附)”,施事为攻城方士兵,而受事为敌城,攻城方士兵以一个整体做施事,具有单方的语义特征;义为“像蚂蚁一样依附”的“蚁附”,依附方也是以一个整体做施事,具有单方的语义特征;而义为“像蚂蚁一样聚附”的“蚁附”,施事与受事共存于同一个表述对象中即施事与受事同体,并且具有两方或两方以上的语义特征。在语义结构中,“肉薄”的施事也是攻城方士兵,受事也是敌城,攻城方士兵以一个整体做施事,具有单方的语义特征。典型的“肉薄”用例只出现于攻城战中,近代文献中出现于非攻城战中的“肉薄”已经不是此“肉薄”了。持“体近”说学者所主张的字面义为“身体挨着身体”的“肉薄”,倒不如说是“肉与肉相互挨着”或“体与体相互挨着”,表述对象必须具备两方或两方以上、施事与受事同体等语义特征,这与义为“像蚂蚁一样聚附”的“蚁附”非常相似;而持“近战”说学者认为“‘肉’指‘肉身’,‘薄’指‘迫近’,同‘日薄西山’之‘薄’”,那么“肉薄”字面义应为“肉体靠近(敌人或敌城)”,这与义为“像蚂蚁一样依附”的“蚁附”也非常相似,只是这两种所谓的“意义”与攻城战都毫无关涉,且找不到存在的客观证据。这大概是由于两个词语中的构成成分的语义特征差异造成的:“蚁”有生命且具有自主行为能力,而“肉”却无生命不具有自主行为能力。
义为“攻城方士兵像蚂蚁一样攀附敌城”的“蚁傅(附)”成词于攻城战语境,构词成分和构词方式均为成词时代所习用。典型的“肉薄”在非攻城战语境中未见用例,这说明其亦成词于攻城战语境。而“薄”之“攻击”义亦习用于战争语境特别是攻城战语境,通过对“薄人”类用例、“薄城”类用例的梳理,可以得出这个结论。如果要证明“肉薄”成词于非攻城战语境或非战争语境,是成词之后渗透进入攻城战语境中,要提供无可置疑的客观证据和用例,恐怕难于登天。
《说文·肉部》:“肌,肉也。”(87页)《说文解字注·肉部》:“人曰肌,鸟兽曰肉,此其分别也。”(167页)王力先生说:“可见‘肌’虽然绝对不能用于鸟兽,‘肉’却不是绝对不能用于人,只是这种应用是有条件的而已。”[5]1如果对“肉薄”成词前后“肉”的使用和构词情况进行深入探究,把这些限制条件归纳出来,恐怕可以找到更多证据。从《墨子·备蛾傅》《孙子·谋攻》等的记载和典籍用例来看,古人对“蚁傅(附)”“肉薄”攻城持明显的贬斥态度。
二、材料与用例的鉴别问题及其他
拙文《“肉薄”补释》主要选用宋代以前典籍用例;对“肉薄”的释义,笔者也曾用宋代以前用例一一进行验证,并没发现矛盾之处。进行语言研究,经常遇到材料和用例的鉴别问题,因为古今任何学者的研究成果本质上都是第二性的,存在正误、优劣,只有客观语言事实才是第一性的;词语也在不断被运用,后代的用例很可能发生变化,存在正例、变例甚至错例。依据错误的材料和用例,不能得出正确结论。宋代以前的“肉薄”用例,可以作为判断后代用例是否正确、是否发生变化的客观参照。
《敬斋古今黈》卷三:“肉薄攻城,或以肉薄为裸袒,或以肉薄为逼之使若鱼肉,然皆非是。肉薄,大抵谓士卒身相匝,如肉相迫也。”(43页)此文献资料的最大价值在于记录了当时对“肉薄”的不同释义,说明至迟在元代,对“肉薄”的理解已经出现分歧。用宋代以前用例对上述三种释义分别进行验证,并不能找到支持任何一种释义的有力证据。
许先生在论证“肉薄”的语法属性时,使用了“肉薄骨并”,此例出自《元史·郝经传》:“且鄂与汉阳分据大别,中挟巨浸,号为活城,肉薄骨并而拔之,则彼委破壁孤城而去。”(3706页)许文据此孤证,用“骨并”定“肉薄”。(案:这实质上也是许文所反对的“以‘外’制约‘内’”的方法,许文中自相矛盾之处往往而有。)许文依据错例,必然导致错误结论。鉴别此例是否正确,方法非常简单,只要检索一下“骨并”在攻城战中是否使用,是否会出现“骨并攻城”“骨并登城”之类的用例,便可做出判断。这类用例在宋代以前及以后的典籍中均极难找到。此例与“士卒身相匝,如肉相迫也”的释义大致相符,从而也印证了李治释义的错误,因为元代存在的三种释义可能会影响到当时或后代对词语的运用;并且无论从时代早晚看还是从注释者背景看,李治的释义也远不及《孙子·谋攻》曹公注、李筌注以及《资治通鉴》胡三省注等材料的证明力。
再看下面用例:
(40)我师从城上以蔺石击缘城者,而引满者辄一发若射隼于高墉中,则我师不无少衄,而城下之虏觱栗齐鸣,呼声动地,遂蚁附肉薄而登,而城陷矣。
(《夷俗记》,636-637页)
(41)洪章愤,愿一人为前驱,从烟焰中跃上缺口,以矛援所部,肉薄蚁附而登,诸将从之入,城遂复。
(《春冰室野乘·朱提督洪章遗事》,714页)
例(40)中的“蚁附肉薄”与例(41)中的“肉薄蚁附”也是后代典籍中的变例,在宋代以前一般是不会出现这两个词语连用的情况,因为“蚁附”和“肉薄”反映的客观对象相同,在同一个具体攻城战行为中,使用“蚁附”就没有必要使用“肉薄”,使用“肉薄”也就没有必要使用“蚁附”。但这两个用例都是正确的,因为“蚁附”和“肉薄”在古代攻城战语境中大量出现,“而登”既是“蚁附”也是“肉薄”经常出现的语言环境。这两个用例亦有力地证明“肉薄骨并”为错例。“肉薄”与“蚁附”连用,进一步证明“肉薄”为名状类型的状中结构,而非许文所谓的“主谓结构”。
“蚁附肉薄而登”用例,也进一步证明许文“‘肉薄’句中进攻方的‘进攻’行为可以分解为肉薄即士卒们身体挨着身体地趋集在一起、蚁附登城、攻打城内敌人等三个步骤,依次进行”观点的错误。许文通过“骨并”一例,使“肉薄”与现代汉语中的“肩迫”“比肩”“拉手”“背靠背”等词语建立联系,以此证明“肉薄”为“士卒们身体挨着身体地趋集在一起”义的观点也就不攻自破。
许文:“以上讨论了‘肉薄’里面的主语,‘肉薄’的‘薄’有没有宾语呢?从字面上看是没有。但根据方一新先生对‘肉薄’意义的解释(身体挨着身体)来看,‘薄’应该隐含有宾语,即‘(士兵的)身体’。”[2]许文“摘要”:“本文以方一新先生所作释义为基础……”[2]许文的目的是证明方先生观点,却又引用方先生的观点做论据,竟然不知道违反了“论据必须已知为真”论证规则!如果按照方先生的释义,应该表述为“肉与肉相互挨着”或“身体与身体相互挨着”,“肉”为复数概念,且“肉薄”的行为主体必须具有两方或两方以上、施事与受事同体等语义特征,何有所谓“隐含有宾语”之说!又如“自尊”意思等同“自己尊重自己”,但“自尊”句法结构为“主语+动词”,语义结构为“施事与受事同体+动作”;而“自己尊重自己”句法结构为“主语+动词+宾语”,语义结构为“施事+动作+受事”。不能依据“自己尊重自己”判定“自尊”“省略”或“隐含”了宾语。“根据方一新先生对‘肉薄’意义的解释”,许先生到处寻找的所谓“宾语”,其实就在“肉薄”中的那块“肉”里,并非“从字面上看是没有”[2]的。许文多处表述与方先生的观点相矛盾,可见许先生并没有准确把握方一新师说。
许文“‘肉薄1’的例句仍可以采用《大词典》义项①下的四例”[2]的表述证明许先生对其所谓的“肉薄1”句法特征、语义特征、语用特征等缺乏相应的认知。《汉语大词典》“肉薄”条第一义项所引第四个书证:“梁启超《论请愿国会当与请愿政府并行》:‘今也吾侪处此无政府之国,为无政府之民……如师陷重围,敌军肉薄而无其旗鼓。’”(卷8-1065页)此例与其他三例明显不同,因为典型的“肉薄”用例只出现在攻城战语境中,且只做状语,是与“械攻”攻城方式具有矛盾关系的“人攻”攻城方式。此例中“肉薄”做谓语,并且已脱离了攻城战语境,与“械攻”攻城方式的矛盾关系被打破。此例其实与“肉薄”条第二义项所引用例“鲁迅《野草·希望》:‘我只得由我来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了’”大致相同,也与许文所引例(6)“有遥相攻击之战,有两军肉薄之战。(清《皇朝经世文·兵政下》)”、例(7)“只一味地和他垓心肉薄,短兵相接。(清《九尾龟》)”大致相同。此类变化后的“肉薄”仍延续了原有的字面义,已经与“血战”非常相似,仍为状中结构关系。“薄”是“攻击”义,“搏”是“搏击”义,“攻击”是主动发起的进攻行为,而“搏击”多为受到进攻后实施的抵御并反击行为,两者具有明显区别。正如“薄战”是“薄战”“搏战”是“搏战”一样,“肉薄”是“肉薄”“肉搏”是“肉搏”!“薄战”“肉薄”“薄”等陈述对象具有主动实施攻击行为的语义特征,非遭受攻击后而进行抵御和反击;而“搏战”“肉搏”“搏”等陈述对象却大多具有实施抵御并反击行为的语义特征,行为的实施必须以受到进攻、冲击或某种外力影响为条件。攻城战“肉薄”无有与“肉搏”相混者,而在某些具体用例中非攻城战“肉薄”可能由于理解或表达的原因出现与“肉搏”相混的迹象。确立义项必须找到无可置疑的客观证据,必须具备惟一性、排他性,不能依据“两解”“亦通”这些带有浓重主观色彩的东西;在确立了义项的前提下,对具体用例的分析如果缺少充分证据可以采用“两解”“亦通”暂时存疑的处理办法。“肉薄”之“薄”与“博”“搏”“膊”等无涉,拙文《“肉薄”补释》中“‘薄’与‘博’‘搏’‘膊’是借用关系”[4]的表述是错误的,因为并不能找到能够证明“肉薄”之“薄”为“博”“搏”“膊”的用例和无可置疑的证据。
许文:“那么《大词典》义项①的解释又该怎么处置呢?它是‘肉薄1’的假借义,可记为‘肉薄2’我们知道,词语假借的用法从本质上讲就是一种误用,就像方一新先生所说的那样……”[2]什么是“词语假借”?笔者孤陋寡闻,只听老师讲过“文字假借”和文字的“假借义”。《汉语大词典》“两军迫近,以徒手或短兵器搏斗”的释义亦不当,释义者到底把“肉薄”看成什么结构关系的词语?能够找到证明“徒手”或“短兵器”的充分证据吗?能够找到证明“薄”为“搏斗”义的充分证据吗?《汉语大词典》“亦指拼搏、搏斗”的释义亦不当,释义者把“肉”藏哪里了?
非攻城战“肉薄”来源于攻城战“肉薄”,从目前收集到的用例来看,这种变化发生在清末民国时期,变化的痕迹在下例中表现得很清楚:
(42)七年元旦,进攻,部将黄元果先登,诸将肉薄垒下,一日平十八砦,克荆竹园,擒斩匪首萧桂盛、何瑞堂,其旁三十六砦相继攻下。
(《清史稿·席宝田传》,12146页)
此例为攻城战语境中的非攻城战“肉薄”用例,“肉薄”的陈述对象“诸将”仍为进攻方,但“肉薄”做谓语,已不再表达“人攻”攻城方式了,与“械攻”攻城方式的矛盾关系已经被打破;“薄”仍为“攻击”义,非“搏击”义。
许文:“‘肉薄’(实际上就是‘肉薄1’)是主谓结构,入句后多充当状语。它的使用背景是两军交战,描写的是‘进攻一方人数多,攻势猛’,它最具代表性的也是使用频率最高的组合搭配形式是‘肉薄攻城’。这样用久了,也就会出现省略其后充当谓语的动词性成分的情况,此时的‘肉薄’就被活用成了动词,并且沾染上了‘进攻、拼搏’的词义,甚至带上了对象宾语,如《大词典》举鲁迅《野草·希望》中的例子就是。”[2]“肉薄”本来就是一个状中结构的动词性词语,何有“被活用成了动词”之说?“攻击”义本来就是“薄”的义项,大量用例以及方先生的研究均已证实,何有“沾染上了‘进攻、拼搏’的词义”之说?“肉薄”修饰的动词多为“攻”“上”“登”等而无一“搏”字,如何能“沾染”上“进攻、拼搏”的词义?既然许先生认为“肉薄”为“主谓结构”,那么“肉薄”在“甚至带上了对象宾语”之后,这个之前所谓的主语、义为“身体”的“肉”现在做什么成分?之前所谓的“‘薄’应该隐含有宾语,即‘(士兵的)身体’”又哪里去了?该不会也是“这样用久了”“也就会出现省略”了吧?清末民国时期存在的非攻城战“肉薄”用例,进一步印证了“体近”说的错误,这两类“肉薄”之间的关系,“体近”说是无法解释的。
在攻城战语境中,“蚁傅(附)”可以做状语,也能做谓语;而“肉薄”只做状语,但它是一个状中结构的动词性词语,仍然具备做谓语的能力,非攻城战语境中的“肉薄”将原来能够做谓语的潜能变为现实。这类非攻城战“肉薄”仍然具备攻城战“肉薄”的字面义、部分语义特征与句法特征等,两类“肉薄”在语义结构中的施事仍然具有“单方”的特征,而释为“体近”的“肉薄”施事必须具备“复数、双方或双方以上、施事与受事同体”的特征;两类“肉薄”的“薄”仍为“攻击”义,为二价动词,只是非攻城战“肉薄”之“薄”的攻击对象(语义结构中的受事)由原来的敌城转移到其他对象了。非攻城战“肉薄”其实是由攻城战“肉薄”脱离了攻城战语境、打破了与“械攻”的矛盾关系、实现了原有的能够做谓语的潜能等演变而来的,是随着古代攻城战这种战争形态的消失而不再被用于表达与“械攻”攻城方式具有矛盾关系的“人攻”攻城方式了。
攻城战“肉薄”是否具有“人数多,攻势猛”或“徒手或短兵器”等特征?这类“肉薄”是攻城方以士兵自身的力量进行攻城,“人数多,攻势猛”或“徒手或短兵器”不是这种“人攻”攻城方式的特有属性,相对于“械攻”攻城方式,这种“人攻”攻城方式士兵人数可多可少,攻势可猛可不猛,士兵可徒手也可不徒手,可携带短兵器也可携带长兵器,都是根据攻城方与守城方的具体条件、作战的具体需要、士兵的个人习惯等决定的。如果“肉薄”攻城“人数多,攻势猛”,难道与之具有矛盾关系的“械攻”攻城就“人数少,攻势弱”了?它仅仅是一种攻城方式而已。“械攻”攻城同样人数可多可少,器械可多可少,攻势可猛可不猛,士兵可徒手可不徒手,可携带短兵器也可携带长兵器等。一般来说,相对于“械攻”攻城,“肉薄”攻城由于缺少专用攻城器械,需要克服敌方高城深濠等防御工事的阻碍,需要投入大量士兵以损害肉体为代价消耗敌方各种守城器械,伤亡必然非常大,下面材料可以准确揭示出这一特征:
(43)古之用兵者,于敌无欲多杀也,两军相击,追奔俘馘者无几也,于敌且有靳焉,而况其人乎!战国交争,驱步卒以併命,杀敌以万计,而兵乃为天下毒,然犹自爱其民,而不以其死尝试也。尉缭之徒至不仁,而始为自杀其人之说,于是杨素之流,力行其说以驱民于死而取胜。突围陷阵者有赏,肉薄攻城者前殒而后进,则嗜杀者,非嗜杀敌,而实嗜杀其人矣。
(《读通鉴论》卷一三,969-970页)
结语
学术论文的作者应该具备充分论证自己观点的能力,同时也应该具备判定所读论文的观点是否充分论证的能力。呼叙利:“论证是学术论文的有机组成部分,论证的充分与否直接关系到结论的可靠与否。”[6]其实,拙文《“肉薄”补释》已经对“肉薄”与“攻城战”的关系、“肉薄”与“攻具”的关系、“肉薄”与“蚁附”的关系、“肉薄”之“薄”与“薄垒”“薄其营”之“薄”的关系、“有专门攻具的攻城方式”与“无专门攻具的‘肉薄’攻城”[4]的划分等问题都有所涉及,许剑宇先生与陶双先生完全应该以客观语言事实为基础,依据论证的充分性原则有针对性地驳斥笔者的观点并阐明和论证自己的观点。呼叙利:“如果一个观点不符合客观事实,无论如何都是无法证实的;同样,如果一个观点符合客观事实,无论如何都是无法证伪的。”[6]
拙文《“肉薄”补释》中,《宋书·柳元景传》“仓猝无攻具,便使肉薄攻之”(1987页)和《资治通鉴·隋纪八·恭皇帝下》“时无攻具,将士肉薄而登”(1225页)等用例,以及《孙子·谋攻》曹公注“将忿不待攻城器,而使士卒缘城而上,如蚁之所附墙”和李筌注“将怒而不待攻城(器),而使士卒肉薄登城,如蚁之所附墙”等材料[4],都可以从客观事实上证明“肉薄”攻城具有“无攻具”的特征。依据“肉薄”与“攻具”的关系,做一简单推导,便能得出结论。
第一,在“无攻具”的条件下,采用“肉薄”攻城。那么,在“有攻具”的条件下如何攻城?对《宋书·臧质传》《宋书·索虏传》《梁书·王僧辩传》等用例进行研究,便能得出在“有攻具”的条件下用攻具攻城的结论。
第二,“无攻具”与“有攻具”为矛盾关系,在“有攻具”的条件下用攻具攻城,那么便可得出在“无攻具”的条件下不能用攻具攻城的结论。所以“‘肉薄’是在没有专门用于攻城的便利器械情况下所采用的一种攻城(包括攻营、攻垒、攻栅等)方式”[4]。
第三,既然“肉薄”是“无攻具”攻城方式,那么采用这种方式的时候士兵到底用什么来攻打敌城?依据社会常识和“肉薄”的语素“肉”的提示,便可以得出“肉薄”攻城实质上依靠士兵自身的力量。像刀枪剑戟之类个人武器,无论“械攻”还是“人攻”都是必须携带或使用的。
第四,在以上所得结论的基础上,采用“列举所有可能性逐一进行证实或证伪”的方法,在“薄”之“近”义和“攻”义的可选择范围内,在“肉薄”可能为主谓关系或状中关系的可选择范围内,便能够得出“肉薄”为名词做状语的状中结构以及“肉薄”之“薄”为“攻击”义的结论。
拙文《“肉薄”补释》撰写于2005年9月,该文的写作和刊发自始至终都得到了方一新先生和业师王云路先生的精心指导和巨大帮助,借此机会再次表达笔者深深的敬意。如果许剑宇先生能够将其文请两位先生斧正,《古汉语研究》编辑部能够将此文与两位先生沟通,或者能够与拙文《“肉薄”补释》的编辑先生与审稿专家沟通,恐怕许文就会大为改观了。正如方一新、刘哲先生所说:“加强审稿,进一步提高刊收文章的质量。”[7]
[1]方一新.东汉魏晋南北朝史书词语笺释[M].合肥:黄山书社,1997.
[2]许剑宇.“肉薄”的释义及其语法属性[J].古汉语研究,2013(1).
[3]呼叙利.“肉薄”补证[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17(1).
[4]呼叙利.“肉薄”补释[J].古汉语研究,2010(1).
[5]王力.汉语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80.
[6]呼叙利.“款蹙”补证[J].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6(1).
MoreProofontheMeaningof“Roubo”
Hu Xuli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oxing University, Shaoxing, Zhejiang 312000)
In essence, both “roubo” and “rengong” mean the way of attacking ramparts without using any high technology in ancient times. “Fu” in “yifu” means “climb”, ant “bo” in “roubo” is equivalent to “bo” in “bocheng”, meaning “attack”. Both “roubo” and “yifu” are adverbial modifier-centre word structures. “Roubo” in ramparts-attacking war is only used as an adverbial while “roubo” in war without attacking ramparts is only used as a predicate; it evolves from “roubo” in ramparts-attacking war so as to realize its function of predicate and break the contradiction with “xiegong”.
“roubo”; “yifu”; “yifu”; “bocheng”; “fucheng”; “fucheng”; “rougong”; “rengong”
10.16169/j.issn.1008-293x.s.2017.05.008
H134
A
1008-293X(2017)05-0048-11
2016-11-30
呼叙利(1970- ),男,山东高密人,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责任编辑吕晓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