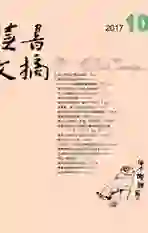汪曾祺,这个老头儿有点狂
2017-10-16许晓迪
许晓迪
人物简介:
汪曾祺 (1920年—1997年),江苏高邮人。曾就读于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师从沈从文等。在短篇小说和散文创作上颇有成就,作品有 《异秉》 《受戒》 《蒲桥集》 《晚饭花集》 等。
汪朗:汪曾祺长子。1951年生于北京。散文作家、美食家、资深媒体人。作品有 《刁嘴》 《衣食大义》 《食之白话》 等。与两个妹妹汪明、汪朝合写 《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
5月16日,是“老头儿”汪曾祺逝世20周年的日子。
彼时的汪朗,人在高邮。汪曾祺文学馆准备扩建,汪朗和两个妹妹商量,准备把“老头儿”在北京的书房原样搬过来。
“老头儿”,是汪曾祺在家中的“别号”,三个儿女这样叫,就连小孫女也这样叫。在汪朗看来,这是老头儿“自找”的。汪曾祺写过一篇 《多年父子成兄弟》,里面写道:我觉得一个现代化的、充满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须做到“没大没小”。父母叫人敬畏,儿女“笔管条直”,最没有意思。
“人们说汪曾祺是‘最后一个士大夫,家里应该藏书甚丰。其实全然不是这么一回事。他最推崇的作家是鲁迅、沈从文和废名,可家里的 《鲁迅全集》只有第一卷,沈从文作品只有1957年的一本小说选,废名的一本没有。他是个特别懒的人,看书没有系统,就和他那口牙似的,残缺不全。”汪朗对 《环球人物》 记者说起父亲,把头一歪,慢悠悠地笑起来。
在汪家人眼中,这个60岁后大放异彩的“老作家”,始终只是个平平常常、随随便便的“好老头儿”。
西南联大的散淡人
汪家这种“没大没小”的家风,沿袭自汪曾祺的父亲。他是一位眼科大夫,年轻时是运动员,而且能诗能画,会摆弄各种乐器,经常给孩子们做灯笼、扎风筝。汪曾祺十几岁就学会了抽烟喝酒,父亲喝酒,也给他倒上一杯;抽烟时一次抽出两根,老子给儿子先点上火。汪曾祺17岁初恋,在家里写情书,父亲就在一旁瞎出主意。
这种怪异而活泼的父子关系,使汪曾祺养成了自由散漫的个性。1939年,他考入西南联大中文系,有兴趣的课便上,听不下去的课就逃。教体育的马约翰教授,要求学生列队时必须站直:“Boys! you must keep your body straight.(孩子们,站直了!)”汪曾祺年轻时就有些驼背,始终未能straight起来,上了几次课就逃之夭夭了。
中文系有许多名教授,但有些汪曾祺就不敢接近,比如朱自清,上课时带着一沓卡片,一张张地讲,小考大考不断,从来不记笔记的汪曾祺就有点吃不消。闻一多则很随意,上课时激情四射,板书里有画有诗,走进教室就点上烟斗,下面抽烟的学生也跟着吞云吐雾,这其中就有汪曾祺。
对汪曾祺影响最大的老师,是沈从文。在西南联大,沈从文是个特殊的教员,一没有大学文凭,二缺乏学术专著,同在中文系的刘文典就十分看不起他。有一次警报响起,学生教授一道跑出校园,快到郊外时,他看到人群里也有沈从文,便上前呵斥:“陈先生 (陈寅恪) 跑是为了保存国粹,我跑是为了保存 《庄子》,学生跑是为了保留下一代的希望。可是你什么用都没有,跑什么跑啊!”
沈从文的课程没有系统,不是学问家的那一套,这一点很投汪曾祺的胃口。一次,他写了篇小说,里面的对话都经过精心设计。沈从文看后批评他:“你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脑壳打架。”
作为沈从文的嫡传弟子,汪曾祺的文风受其影响极深。他晚年写 《受戒》 时,脑子常常想的正是沈从文笔下的那些女性:三三、翠翠、夭夭。
沈从文对这个学生也格外赏识。汪曾祺在昆明写的稿子,无一篇不是他寄出去帮忙发表的。1946年,汪曾祺来到上海,找不到工作,情绪很坏,甚至想自杀。沈从文写信把他大骂一顿,说他这样哭哭啼啼的,真是没出息。“你手中有一支笔,怕什么!”
西南联大时期的汪曾祺,读了不少西方现代派的作品,追求新奇和抽象,比较“朦胧”,被班里的同学戏称为“写那种别人不懂,他自己也不懂的诗的人”。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有人给他看那时的新潮小说,他看后淡淡的,挺不以为意——“意识流”之类的写法,他几十年前就用过了。
随遇而安的右派
1948年,解放战争战事正酣。28岁的汪曾祺在沈从文的帮助下,进入午门的历史博物馆,当了一年的办事员,白天检查仓库,下班后到筒子河边看人算卦、叉鱼,晚上就在宿舍里看书。几十年后,他在 《午门忆旧》 里写到了紫禁城的夜晚:“站在午门前的石头坪场上,仰看满天星斗,觉得全世界都是凉的,就我这里一点是热的。”
命运弄人。汪曾祺前脚离开午门,沈从文后脚也来到了这里,他也喜欢站在午门城头上,看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心境却苍凉、孤单得多。
上世纪50年代,是火热的建设时代,沈从文和汪曾祺,却都坐上了冷板凳。一个被斥为“反动文人”,从此割舍了文学,在库房里与各种文物打交道;一个收敛起小说家的锋芒,做着安分规矩的文学编辑,不前不后,不高不低,随着大流走。
1958年夏天,一直随着大流走的汪曾祺,突然发现单位过道里贴满了围攻他的大字报。没完没了的批判会后,结论下来了:定为一般右派,下放农村劳动。
汪朗说,对于当右派,汪曾祺后来说起,居然很得意。他写过一篇 《随遇而安》,第一句话便是:“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
汪曾祺下放的地方是张家口沙岭子的一个农业科研所。这个地名汪朗记得很牢,那时他刚学会汉语拼音,不知天高地厚地给爸爸写了封信,逼得汪曾祺连忙现学拼音,好写回信。
在沙岭子,汪曾祺扎扎实实地劳动了两年。白天插秧、锄地、割稻子,给果树喷波尔多液,晚上就和农业工人被窝挨着被窝,睡在一铺大炕上,听他们说心里话。
劳动之外,业余生活也很丰富。所里演戏,汪曾祺就去给他们化妆,用戏剧油彩,勾出来的脸谱比专业剧团的还讲究;有时也亲自上阵,演演汉奸特务一类的角色。
他还负责所里的美术工作,画过一套 《中国马铃薯图谱》。他每天蹚着露水到地里掐一把花,插在玻璃瓶里,照着画。等到花一落,就开始画薯块,画完就随手扔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
“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这么多品种马铃薯的,全国盖无第二人。”许多右派回忆流放的日子都是凄风苦雨,汪曾祺笔下却是诗情画意。每次回京探亲,他总是兴奋地说个不停,或是乐此不疲地鼓捣从沙岭子带回的野兔子和甜菜。
“爸爸的脑子,似乎特别不愿意记忆那些悲啊苦啊的东西,更不愿意将它们诉诸文字。”这是汪曾祺的哲学,风来草倒,雨泄泥下,不退缩,也不偏执,从逆境里发现人生的快乐和亮色。
“生活,是很好玩的。”这个老头儿如是说。
“样板团”里的书生
1962年,汪曾祺调回了北京,在北京京剧团当专职编剧。一年后,北京京剧团开始接受京剧现代戏的演出任务,汪曾祺参与了《芦荡火种》 的编剧工作,也就是后来著名的 《沙家浜》,从此进入了样板戏的创作班子。
当时,江青的意见是整個剧团的生死簿,大到砍掉一场戏,小到改写一句对白,都必须照办。尽管写得战战兢兢,但汪曾祺还是给自己留下了一点空间。《沙家浜》 里 《智斗》 那一场,写得婉转有趣,阿庆嫂的一段唱词更是生动:
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凉……
血与火的场景,到了汪曾祺笔下,却充满了人间烟火气。这段唱词当时差点被江青“枪毙”,理由是“江湖口太多”,后来竟瞒天过海地保留下来,成为传唱至今的经典。
在政治的大潮里,汪曾祺总想隐藏点非同寻常的东西,骨子里是一腔坚守底线的傲气。后来,于会泳接替江青,负责 《杜鹃山》 的改编。有一次,他说汪曾祺写的一句词“谨防隔山烟尘涨”不通。汪曾祺二话没说,回家从 《杜工部诗集》 中翻出了杜甫的诗,在于会泳面前一放,说:“你看看!”
身为“样板团”的战士,汪曾祺的待遇不错。夏天、春秋天各一套样板服,银灰色的确良,冬天还发一身军大衣,式样、料子都是江青亲自定的。但他自认是个无名书生,不去凑热闹,有时为了交差难免胡编乱造,精神上饱受折磨。
1975年秋天,汪曾祺奉命去了一趟西藏,写一个反映高原测绘队先进事迹的戏。在拉萨,他有点高原反应,鼓着肿得老高的腮帮子在街上乱转。在一家卖藏药的铺子里,他买回了一只拇指大的、金红色的小螃蟹。多年后,他把这只螃蟹写进了一篇短文中,里面有这样几句:
螃蟹为什么要横着走呢?
螃蟹的样子很凶恶,很奇怪,也很滑稽。
凶恶和滑稽往往近似。
“爸爸当时买这个小螃蟹,是有一些感慨的。”汪朗说。
一年后,“四人帮”倒台,大乱十年成一梦。那段时间,汪曾祺十分活跃,写大字报,写标语。他觉得自己憋屈太久了,终于可以痛快说话了;但在外人看来,他在“文革”中得意得很,如果不是卖身投靠,哪会如此风光?结果,在举国欢欣的时候,汪曾祺又一次被“挂”了起来。
在汪朗的记忆中,老头儿一向随遇而安,那段时间却闹腾得厉害。白天在单位受审查,回家后喝了酒,嚷嚷着要把手指头剁下来以“明志”。酒足饭饱后,便开始胡涂乱抹,画瞪眼睛的鱼,单脚独立的鸟。画完之后还题上字:“八大山人无此霸悍”。
“我们当时不知道八大山人是何方神圣,后来明白了,才发现他是拿这样一个大画家说事儿,这个老头儿,实在是有点狂。”
老头儿成了“下蛋鸡”
知道汪曾祺的人,基本都知道 《受戒》。
1980年,60岁的汪曾祺发表了短篇小说 《受戒》。当时的文坛,幽怨的小说和愤怒的诗歌风行,汪曾祺的出现,有一点旁门左道的意味。《受戒》 写的是一个小和尚的恋爱故事,其间点染着高邮的风土人情,描画出一个充满诗意的水乡。
“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受戒》 写成后,汪曾祺好像一下子来了劲儿,不管不顾地写个不停。
“当时我们家住在甘家口,仅有的一张写字桌子放在妹妹住的小屋。我妹妹是工人,逢到上夜班,都得在家先睡一觉。老头儿晚上急着要写文章,又不能进屋,到处乱转,就像一个憋着蛋的老母鸡。好容易熬到晚上10点,我妹妹上班了,他‘噌地冲进屋里,铺开稿纸,一直写到半夜。以后,一见到他这样,我们就问:‘老头儿,又憋什么蛋了?‘别闹,别闹,这回下个大蛋!”
80年代的汪曾祺,一反往日的沉寂,下了不少“蛋”。《异秉》 《大淖记事》 《陈小手》……他写的都是平凡人的日常生活,没什么波澜的故事或宏大的场景,也没什么华丽的词汇和高深的思想,只是充盈着民俗的情调,流露着温情与暖意。
这些文章的发表,让汪曾祺成了“著名作家”—— 前面还要加上一个“老”字。家里人还是常常拿他打岔、开涮。“他在我们面前炫耀自己的文字,我们就逗他:‘老头儿,别臭美了!他就颠儿颠儿地跑回自己的书房,把门一关,好像是闹了情绪。我们也不理他。不一会儿他就把头探出来,看外边比较平安,又出来和我们闲扯了。”
如今的汪朗,倒是越来越能领会父亲文字的功夫。他提起了《异秉》 的结尾。小说的主人公是卖熏烧的王二,生意红火,引人羡慕。一天晚上人们聚在保全堂药店闲聊,当地一个“侃爷”张汉说,凡是成就大事业的,都有特殊的禀赋。于是大家让王二说说有什么“异秉”。他的回答是:“大小解分开。”闲聊结束,各人回家,保全堂两个地位最低的伙计,40多岁还没娶亲的“痰篓子”陶先生,和总是被先生拿门闩痛打的陈相公,在厕所遇上了,“本来,这时候都不是他们俩解大手的时候”。小说就此打住。
“有一个评论家和我说,他把这句话看了三遍,才大笑出来,明白是怎么回事。老头儿说,文章贵在含藏,如果说破了,再发一通议论,就全完了。”汪朗说,“老头儿有一股‘坏劲儿,讽刺老辣,入木三分,但他用清淡的笔触点到为止,其中有一种大的悲悯和同情。”
散文家·美食家
“在老头儿心里,我们都不是干这行的料,借用他评论别人的话—— 不是嗑这棵树的虫。”汪朗上大学那会,抒情散文风靡一时,汪曾祺却颇为厌恶。“有一次,电台正在播配乐散文 《荔枝蜜》,我在大屋里听得起劲,老头儿从小屋里‘噌一下窜过来,把收音机关上,甩出一句话:‘散文配乐,一大恶俗。写文章最忌无病呻吟。”
汪曾祺也写散文,而且自视颇高。他精通杂学,尤其爱看古人的笔记,岁时风土、野史传说、草木虫鱼、文化掌故都包罗在文章中。他甚至还写菜谱,拌菠菜、拌萝卜丝、松花拌豆腐,题目就叫 《家常酒菜》。
汪曾祺是个公认的美食家,也是厨房的一把好手。他写过很多吃吃喝喝的小文章,把各种日常吃食写得有滋有味。这其实也是他的人生态度:不管遇到什么坎坷,都不忘记生活的情趣。1977年,尽管还在接受审查,没完没了地写交代材料,汪曾祺却觉得日子“颇不恶”。他在给老友朱德熙的信中说,“我最近发明了一种吃食”,并详细列出了做法:“买油条两三根,劈开,切成一寸多长一段,于窟窿内塞入拌了剁碎的榨菜及葱丝肉末,入油锅炸焦,极有味。”顺带也提到了儿子,“汪朗前些日子在家,有一天买了三只活的笋鸡,无人敢宰。结果是我操刀而割。生来杀活物,此是第一次,觉得也无啥。”
子承父趣,汪朗也烧得一勺子好菜,据林斤澜评判,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水准。有一道四川的夹沙肉,是他的拿手菜。用肥膘肉,半煮熟,切大片,中间夹上红豆沙,上面再盖上拌好红糖的糯米,然后上笼屉蒸。“菜一上桌,老头儿一边嚷着:‘不能吃了,再吃我就要死了!一边又用筷子对着一块肥肉扎下去。”
“老头儿”去世后,自嘲“不是那块料”的汪朗,也像父亲一样写起了吃吃喝喝的文章,从帝王高官到文人百姓,从猪头火腿到萝卜白菜,相比父亲的单纯,汪朗的笔触里多了些借古讽今的微言大义,但意趣、幽默和对生活的一腔热忱,还是打上了“汪氏出产”的烙印。
在父亲走后的20年里,他也渐渐活成了另一个“老头儿”。
(选自《环球人物》2017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