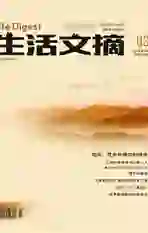塘房茶马古道上的石头村庄
2017-10-14庄文勤
庄文勤
这是一个石头砌成的世界。
房屋是石板房,道路是石头铺,塘基是石头砌,水渠是石头筑,菜园的垄基是石头垒。石门墩、石院墙、石前檐、石鸡笼、石厕所、石畜圈不胜枚举。石槽、石盆、石凳、石桌、石碾、石磨、石臼琳琅满目。石台阶、石板路、石垱……甚至烤茶、烧肉的用具都是用石头制作而成。
这是一个承载滇西茶马古道七百年历史的村庄。滇西茶马古道是唐宋以来至民國时期汉、藏之间以进行茶马交换而形成的一条交通要道。路线有两条:南线由云南的普洱、大理、丽江、中甸、西藏的察隅、波密、拉萨、日喀则、江孜、亚东、柏林山口,分别到缅甸、尼泊尔、印度;北线从四川的雅安、康定、西藏昌都、尼泊尔、印度。石头村,正是位于南线从普洱到大理这一条中的塘房村。
龙年开春,我徒步踏上了滇西茶马古道保留得最完整的云南省凤庆县鲁史镇到塘房村这一段旅途。在乍暖还寒时,我打量着古老通道,想象着当年行走在古道上的马帮,浩浩荡荡的驮着茶叶、毛皮、药材、核桃等山货,唱着“……赶起百十匹马帮(哟咳),驮上百十斤驮子(哎),翻过(哦)百十个梁子(呀),换回(哟)百十样货子,填饱(嗯)干瘪瘪的肚子(呀),狂欢一阵子(啊)”的号子进城,从一个山谷到又一个山谷,从一个村寨到又一个村寨,马帮踏出了一条沟通各地的生命道路,换回必需的盐巴、布匹等生活用品。从此,那些崎岖逶迤的山道上,诉不尽马帮的神奇;刀砍斧削的绝壁,说不完赶马人的辛酸;不老的风峡谷,回荡着许多赶马号子的豪迈和悲壮。
如今,茶马古道上的马帮已经离开了几十年上百年了,走在悠悠的古道上,似乎还可以听到久远的年代里传来的阵阵马蹄声,滴滴答答地响彻着整个山谷。
1913年以前,凤庆(旧称顺宁)与外地的交往,最主要的就是顺下线,线路有三条 :凤庆(顺宁)、鲁史、巍山、下关、丽江、中甸、西藏;凤庆(顺宁)、鲁史、下关、昆明、省外;大理、下关、巍山、鲁史、凤庆(顺宁)、镇康、耿马、缅甸。无论走哪条路,都必须过塘房村,因此,塘房承载起了茶马古道七百多年的历史沧桑。
塘房距鲁史镇约6公里,沿着弯弯曲曲的古道,跟着猎奇的游人一直向上攀登,刚开始还感觉有使不完的劲儿,可是,不一会儿我就感觉气喘吁吁,大腿酸痛,干脆拿着相机在路上拍起照片来。此时,一个村民赶着马,身上扛着百十斤重的小型农用机械,竟然在古道上健步如飞。他说这段路是茶马古道赫赫有名“九曲十八弯”,到塘房村还早着哪。随后,他唱着“身着大地头顶天,星星月亮伴我眠。阿哥赶马走四方,阿妹空房守半年”的赶马调很快消失在古道的尽头。
沿着古道一路向上行进,阳光透过湛蓝的天空投射到山头上,让山林遍染了一层金黄色,清冽的山风吹过,卷起一层层的落叶,抬头仰望天空,干枯的树枝盎然的屹立在蓝白相间的天际,直指苍穹,显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在那密密的枝杈里,孕育着来年生机勃勃的绿色和百折不死的生命之魂。脚下的道路崎岖坎坷,这真的就是那条千年的古道吗?千百年来,这条道路曾经是何等的繁华,过往商贾,游人如穿梭般的从它身上走过,它也曾承载着多少人的希望和梦想,谁又能说清楚,在它身上演绎过多少感人的故事呢?世事如烟,沧海桑田,它如今就像一位年至耄耋的老人,静静地躺在这里,在它的梦里,是否还依稀记得那往日的繁荣以及行人如织的那些年代?如今,只有偶尔路过的徒步探险者和匆匆而过的狩猎人还能让它偶然醒来,可是,又有谁能静静地聆听它的故事呢?那划过枝头的风声,是否就是它的低声哀怨。
到达塘房村,我们的目光被石头房屋豁然点亮,瓦是石板,墙是石墙,地是石地,石头做成的房子里,住着终年和石头相伴的人。
石头是塘房的财富,这里产的石头像千层的油饼,用扁锤沿石角一敲,就能起下一大块。一层一层的石板,像一本厚厚的书,层次之间毫不粘连,只要你乐意,就可以随意地翻阅。村民们建房就地取石,不做任何二次加工,没有污染,无需能源。石材是天然具备的,木材是自然生长的,粘接的材料无需运输。墙是石头砌的,支离的碎石,平面往外地块块砌起,不用半点沙灰水泥黏合。石墙的顶上,再架木椽,木椽的上面,再铺石板。石板从檐口铺起,块块叠压,至脊而收。石材的地基,石材的墙体,石材的屋面,天然的材料,被塘房村人巧妙利用,筑屋造房,建宅修舍。村里的老人说,这样独特的石板房,雨季,屋顶石板遮挡,水不入室。晴天,满室潮气蒸发,沿缝隙罅漏四散飘逸,室内很快又可干爽如初,居住于内,冬暖夏凉。
大块小块的石板,充当了遮风挡雨的屋瓦,参差不齐的石板,在一幢房子的屋顶上,都被派用到了最为恰当的位置。这就是塘房村人的高明,深知才尽其用、物尽其能之理。对于石板来说,再不规则的长相,塘房村人都能给它们找到最为恰当的位置。
石头垒成的房子毕竟不能建得太高大。在村里,几乎每间屋子都一般大小,而且结构也基本相同。屋子都不高,高一点的人走进屋门,可能还得稍微低下头。并且,每间屋子里都没有一扇窗户,只有一个天井,是屋子采光的重要途径。
村民搭建的石屋,大多是随意而为,有的石块横着叠砌,有的斜着堆砌,大石块和大石块之间用小石块补缝加固,连木质的梁柱也特别讲究自然。用在石屋里还是保持原来的形状,没有刻意修整过,使得塘房村的石屋显得更加硬朗,看上去厚实凝重,极具质朴之感。
走进一户人家,里面别有洞天,大大的天井里,有石头砌的猪圈、鸡窝,院里有长石头条搭的凳子,地面是用薄石条铺成。猪圈里喂猪的槽子是石凿的,洗衣服的搓板是石板做成的,捣蒜用的也是石锤、石臼。小院里香椿、月季花、木槿花香味弥漫。
主人家在办喜事,几个小伙正往青石板上放肉,我们一问,才知道要做塘房特色菜青石板烤肉。几个烧得火苗通红的炭火盆并排支在厨房里,炭火上有一块石板搭在上面,另一块一模一样的石板压在烤肉上,打开上面的石板,果然里面夹着猪肉在烤。这种石板烤肉就是用新鲜的猪肉直接放在石板上烤成的,工艺很简单,石板烤出的肉外观看焦黄焦黄的,让人垂涎欲滴。割下一块来,嚼在嘴里,味道既香又脆,不像直接在炭火上烤出的肉有烟熏火燎的味道,也许,这才是人们爱吃塘房烤肉的真正原因。endprint
石水缸是塘房家家必备的石水缸,正方形、长方形居多,也有正六边形等样式,有的能装十多担水,有的只能装两三担水。水是从屋后的老林里用水井槽引来的,水井槽用龙竹或整棵的圆木挖成,涓涓的山泉沿着高高低低的水井槽,翻过一个又一个山坡,把塘房人家的石水缸装得满满的,做饭、洗菜时就舀水缸里的水用。我舀了一瓢水咕咚咕咚地一气喝下,那沁人心脾的清凉和痛快深入五脏六腑。
我们有幸在另一户人家品尝到了青石板烤茶。青石板烤茶是塘房村人的一种独特饮茶方式。石板是薄片青石,质地细腻而均匀,似乎不容易找。在温火上预热十多分钟后,石板都有些烫手了。主人从竹筒里取出几小撮早已准备好的晒青茶。这可是开春第一尖春茶揉制的呢,据说是专门款待第一位踏春而至的客人。诱人的茶在青色的石板上欢快地翻滚着,烤茶最讲究火候,几个来回叶色渐渐由棕黄色变成棕褐色,整个院子也已经是茶香漫溢了。将烤好的茶叶收入备好的竹筒,所有的茶具都是竹制的,据说这样茶才更香。
茶叶在水中沸腾的一刻,香气弥漫。主人将茶壶盖子一扣,再用沸水浇注壶身,接着将竹制的茶杯翻转用水洗净,片刻之后,青透的茶水一一流入竹杯。一切流畅得让我有些眼花,一晃神,香茶已在眼前,我赶紧双手接过,低头一品。真可谓“石屋忘言对此茶,全胜羽客醉流霞。尘心洗尽兴难尽,一树鸟鸣片影斜。”
老人们说,塘房是一个被茶香浸泡的村庄,当年茶马古道最盛的时候,每天来往的人像排队一样的经过。据《滇南新语》记载,在明代,凤庆就能用手工制造出太平茶、玉皇阁茶,色、香、味可与龙井茶媲美。有了这样的好茶,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顺宁知府刘靖督土民修建青龙桥于镇南金马明子山脚下的澜沧江上,走过澜沧江过金马翻越黑山门,就到塘房。青龙桥连通的茶马古道上茶事不断,凤庆茶源源不断地进入内地、上贡朝廷、远销东南亚。悠长的山街成了茶叶交易的场所,那叶形平肥的“尖山云雾”、条索分明的“太华茶”、细润色正的“银毫”、秀美质佳的“特级工夫茶”……各色茶叶摆满悠长的街巷,浓郁的茶香令人心旷神怡。
或许正是受凤庆悠久的种茶、制茶历史熏陶的缘故,在塘房村,人们从茶园采回鲜嫩的茶叶,洗净晾干后用手揉软搓细,放进一只大碗中,再加上柑橘叶、酸竹笋、大蒜、辣椒、盐巴等佐料拌和,就成为一碗“凉拌茶”。这种茶,滋味变化多端,苦中透出暗暗鲜香,是下饭的好凉菜。有的则把采来的新鲜茶芽放进小缸里,撒上盐巴拌匀,层层压紧,腌制几个月后,拌上佐料,也是开胃佐餐的好菜。当然也有三五人相聚一起,持一杯茶香,懷一份闲情,细细品茗,渐渐境宁心净,在幽香芬芳中涤尽俗尘,享人生之无穷真趣。
塘房村子偏僻,但这里生产的茶味道好,香气浓。那香气,据说,在村庄山顶的黑山门都可以闻到。塘房村几乎家家户户都制茶,能不香么?何况,四周都是茶山,即使没有烘焙茶叶,村子也被茶山的阵阵清香氤氲着。何况,村里的人家都爱喝茶,日泡茶夜泡茶,茶汤的香气不时腾挪着。几十年数百年,这里的房砖屋瓦,这里的柴门木窗也该都贮满了茶香。
走出塘房村,寻一处墙边的石凳歇歇脚,摘一束在石缝中长出的野花闻闻香,看屋前公鸡昂首阔步踱过石头的街道。夕阳西下,身边和脚下的石块静静地闪烁着岁月的印痕。那些深深浅浅的印记,明明暗暗的沧桑,那是一种无言的石头历史,更是一种特有的村落文化,塘房以特有的魅力,支撑起了滇西茶马古道一方数百年的历史,这是一条辉煌的道路,这是一部生活的历史书籍,无论什么时候,都永远值得我们用心去阅读,永远值得我们用步伐去丈量。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