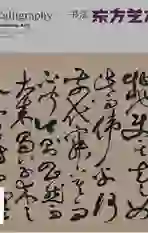谈“烟霞灵气”与祝帅的书法
2017-10-11周勋君
周勋君
其道微而味薄,固常人莫之能学。
其理隐而意深,固天下寡于知音。
——唐·张怀瓘
一
美国诗人毕晓普说:“写作是最不自然的举动。”把这句话里的“写作”两字换做今天的“书法”如伺呢?
近三十年来,中国现代教育体系中书法专业的设置带来的最为显著的成效之一就是,对积累、演变了数千年的书写“法度”作了极为学术的清理与强调,今天,一个书写者如果不能在技法上有过人的领悟和绝招就难以算作专业。一笔下去,起笔当如何,行笔当如何,收笔又当如何,承接处、暗过处要怎么处理,字内,字外,行间,墨色,等等,皆是讲究——这些讲究有相当一部分早已不是为达到一般的书写美观所需的了,而是为了更纯粹的“书法艺术”之美。书法由最初质朴的写字到发展成这种“最不自然的举动”既有一部足够的文献可考,也有相当的实物可察,且无论文献之详备,字迹之精美,确实都有惊人之处。
但是,除了经由后世种种“最不自然”的法度规训过后得来的极精极美之外,确又有另外一类书写常常深为人们所动。
比如,不久前在匡时春拍上所见曾国藩的行书《颐亲弹琴八言联》,马一浮的篆书“兼善堂”三字。这类书作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在笔墨上不事雕琢,书写多半比较质朴、自然。但是,从中焕发出的那种清朗、沉古或者雅人深致如此分明,使人过目难忘,回味深长,为追求技艺精湛者少有。
人们容易说出技艺精绝者的好处,用笔怎么样,结构怎么样,线质如何,等等。这些都是“当于目而有据”的。但对于后面这类字所焕发出的神韵却只有心领神会的份,不能说出所以然来。好比北宋时期的苏轼,今天看来当然是书史上一流的书家,当时在书法上却倍受时人挖苦。黄庭坚是这样替他的老师兼朋友做辩护的,“今俗子喜讥评东坡,彼盖用翰林侍书之绳墨尺度,是岂知法之意哉?余谓东坡书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此所以他人终莫能及尔。”他的意思是,苏轼的字是不能用“俗子”的“翰林侍书之绳墨尺度”这种东西去衡量的,苏轼的卓尔之处在于“学问文章之气”。显然,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尺度。往后,只要人们多么强调诸种法度并且身体力行、趋之若鹜,作为矫正,另一边就有人多么郑重其事地强调后一个标尺的重要——“馆阁中清润庄肃,专事修饰而乏性灵,不可以称法书。”“后世书固不及魏晋,然必读书之士出笔,见雅人深致;虽点画有象可求,而不博群书,胸次鄙俗者,往往尽力临摹亦多形似,绝少烟霞灵气。”
“翰林侍书之绳墨尺度”、“法度”、“形似”,这些我们是知道的,可以列数的,但“学问文章之气”、“烟霞灵气”指的究竟是什么呢?换言之,苏轼,上面提及的曾国藩、马一浮,他们字中的神韵既然不是得自对法度、形似的精益求精,那么,它们从哪里来?
我有一种怀疑,历来人们只能心领神会而无法说清的这类“学问文章之气”、“烟霞灵气”大概只是源于这样一种书写:遵守基本法度,质朴、自然地写字。然后,让有关的因素——个人性格、气质、身体、工具、环境、书写动机及内容等等(它们关乎速度、力量、节奏、细微动作的不可预计)——在书写过程中自然的发挥作用。这里面孕育的可能性也许是l京天动地式的,也许微妙之极,极淡,甚至不易觉察,然而,都是人们难以想象的。
——倘若把所有这些未可预计的奇妙之物都交付给对技艺的高超控制,“性灵”、“烟霞灵气”从伺而来呢?
细究以上书者,大抵如是。
唐代张怀瑾曾用“其道微而味薄,固常人莫之能学;其理隐而意深,固天下寡于知音”来相容王羲之的字,说的也许正是“书法”、“法书”这一看似平淡无奇的事实。——试想,王羲之身前身后皆書名远播,怎么会“寡于知音”呢?他的字道媚妍美,怎么会“道微而味薄”呢?能这么说,理由只有一个,屡经后世阐释、装点的“王羲之”远非真实的“王羲之”。以今天流传下来的王羲之那些可靠的信札来看,做这样的推测大概并不为过。
这些,都是由观赏祝帅的书法时想到的。实际上,也皆是为他所说。
因他的书法同上文所列举的例子实为一类,书写质朴,不事雕琢,朗然有一种古淡和庙堂之气,使人观之一动。
例如,他作于2013年的行书《左琴芝草八言联))o这在今天,尤其在青年书家中并不多见。
二
当祝帅因连续三次问鼎全国书学讨论会而广为书法同道所识的时候,人们并不知道他其实自幼习书,并且,几乎一直处在书法的核心圈子里。古代书史、当代书法理论,以及各种书法思潮、现象,他都谙熟于心。且都有不俗的见解。
少年时代,在当地名师的指导下,他已经写得一手法度严明的颜体楷书和李北海风格的行书,同时,兼及魏晋小楷。他那时的书法热情与才能从当年所获的各类大小书法奖项中,从他小小年纪为不同报刊题写题头的泰然气概中都能窥见一二。只要略玩他的小楷手卷《朱柏庐<治家格言>》,就能见出尚不及志学之年的他对于书法中规范与巧变的领悟。
此外,从他那时的各类书迹来看,他似乎天生有种在放松、自如的情况下把握规范的能力。他的字几乎从一开始就没有因为要谨守或敬畏法度而显出拘谨的迹象,它们总是既安然守法,又带着些许怡然自得的神情。
这无疑是他的过人之处。
及至年长,随着眼界的开阔,尤其,对书法史,对当代书法理论的目渐深入,祝帅的作品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保留对基本法则的遵守同时,他从有损内在节奏和神韵的点画经营中摆脱出来,不再斤斤于对这些形模自身的玩味,回到了一种更为质朴、流畅,甚少“作意”的书写状态。如同我们现在看到的,也如同我们在前面指出的那样。
这一改变对他的书法生涯来说自然有其意义。——我们已经谈及过沉溺于对技艺的雕琢,欲以高超的技艺替代或控制书写与“魏晋平淡”,与获得“神韵”、“烟霞灵气”之间的相悖。
我以为,这以后,他距离真正的书法更近了。从后世逐渐衍生、过度渲染的那些对起、收、转、承处的着意刻画中脱化出来,他就能尽情地体验书写中自然推移的运动与节奏了。在蒋彝、林语堂等人看来,这种“运动”、“节奏”正是书法的生命所在。想来这个观点王羲之、颜真卿也都是同意的。因为谁如果为了要制作点什么用笔或结构上的花样而请他们中断或改变——哪怕是极为短暂的——手中浑成的正在运行的书写轨迹和节奏,那一定会使他们愕然。
在这一过程中,给祝帅以指引最多的显然是唐代的颜真卿。这正是他少年时代钟爱、熟悉并取法的对象,那时,他沉迷的是颜氏宽博沉雄的楷字。现在,祝帅沉入到他更为动人心魄的行书里。
从祝帅所临《祭侄稿》中能充分见出他对颜真卿。对书写中运动、节奏的领悟——颜真卿的行书用笔极为单纯、质朴,其动人之处也正在于这种质朴、力量、内部奔涌不息的气韵,以及其间不可预期的正奇与方圆变化。祝帅临摹的祭侄稿迥异于人们通常对某个法帖的临摹。通常的临摹力求在形模上达到相似,一点一画,着意模刻,以毫发不爽为目标。但是,这样的临摹往往“于神理不得”。祝帅临摹的祭侄稿并不在形似,在于深处的,导致形模产生的动作、运动节奏上的相似,通过对动作、运动节奏的准确理解与运用来达到形模的相近。这样,即使细微之处有别于原作,不十分相像,在神韵上却逼肖古人。
颜真卿行书手稿中的那种“篆籀气”,那种在连续挥运中仍保存完好的力量,今天都借他临摹时对动作、运动、节奏的体验与领悟熔铸到了自己的笔下。仅此一点,祝帅已在取法古人上超越了同辈及前代许多人。
有此禀赋、学识与勤勉,加上个人的“性灵”,祝帅已然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他的书作,除刚才所举行书《左琴芝草八言联》外,行书《自作诗初到杭州》《自论书册页》,小楷《杜甫诗<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等等,都是近年的佳作。其中的古淡,生动与气度,使人在遍观妍美、精绝的字迹之后,重拾对“烟霞灵气”的记忆与向往之心。
2015年7月29日
于望京南湖中园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