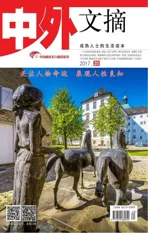邮票里的1500次别离
2017-09-30□陈卓
□ 陈 卓
邮票里的1500次别离
□ 陈 卓

部分写于民国时期的家书
1500封家书和谭安利74岁的身体一样,在一点点衰老。
一封封书信,曾小心翼翼地把许多家庭的故事折叠封存,然后通过深达中国每一个乡村、集镇的邮政网络延展。然而现在,信纸在慢慢发黄、变脆。
脆黄的纸张维持着谭安利的许多记忆。这个湖南茶陵的普通家庭,从7口之家开始生根发芽,直到变成现在百余人,枝丫伸到了长沙、北京、内蒙古,甚至美国。这个家族经历了百年沉浮。
谭安利记得,小时候,信几乎是分散四处的家人之间唯一的联系方式。“文革”中母亲被隔离审查,哥哥在另外的地方上班,弟弟成人以后,就作为知青到了农村。一家人聚少离多,四散在各处的家人,通过书信保持着联系。后来,即使上世纪90年代初家里装了电话,他仍保持一个月写一封信的频率。
他曾想过要孙辈继续写家书,可是“现在孩子学习太忙了”。网络取代了邮路,建立起家人之间的联系。
书信的衰落让谭安利担心。他想尽各种办法保存这些脆弱的纸张。在报纸上看到有博物馆收藏家书的消息时,他立刻就联系了捐赠。
在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副馆长张丁看来,谭安利保存这些书信集结在一起,就是一部家史,“由此扩大到一个又一个家庭和家族,构成某个乡村、某个社区的历史,然后再扩大到某个地区或区域的历史,再扩展,就是一个国家的历史。”
1500 封家书勾勒一个家
谭安利的1500封家书拼凑在一起,一幅隐藏在历史深处的悲欢离合画面也逐渐被勾勒出来。
14岁离开家以后,母亲谭珊英就一直在四处漂泊。在厦门的地下党机关,由于任务需要,她与陶铸假扮夫妻。
除了谭安利兄弟3人外,谭珊英还有一双儿女。第一个出生在1931年的中秋节,是个女孩儿。那时,谭珊英正在“白色恐怖很厉害的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女儿出生后,她还没喂过一口奶,就被第一任丈夫陈柏生用绒毯包着送去了美国人办的公共育婴堂,并且安慰她,这是为了革命工作万不得已之举。后来,她和陈柏生去苏联学习前夕,又生了一个男孩,为了不耽误行程,她把孩子送给别人照看,不到一周岁就病死了。
经历过那么多分分合合后,谭珊英变得越来越平静。谭安利和大哥陈洣加都不记得见过母亲悲伤或者愤怒。但在1961年,当三个儿子中有两个不在身边的时候,她才在正月初七无奈地给谭安利写信:“本来以为你和哥哥都会回来过年,心中感到好不快慰。谁知你俩都不回来……这又多少使我失望。”
那时物质匮乏,谭珊英还随信给儿子寄了自己做的糯米粑粑,“十二个糖的,抹了红点,八个菜的,共二十个。另外给你附来一点腊鸭蒸盐菜,鸭的味道不错,不过份(分)量不多,给你尝尝。”
这些家书“不仅打开历史的一扇窗,也打开人性的一扇窗”
分别的苦楚隔三岔五地击中谭安利一家,也在中国千百年的历史中时隐时现。家书曾经是中国人对抗分离的强大武器。
谭安利一家一直在时代的潮流中起伏,少女时代就离开家的母亲,直到1948年才回到茶陵。那时这个家庭和中国的许多家庭一样,度过了一段艰苦的时光。
去世前做过官的外祖父,曾经在村里起了一座两层楼,“宽敞极了”。可是陈洣加记得,等到他们3兄弟和母亲回到茶陵的时候,屋子只有一层可以住人,第二层连楼板都没铺。外祖父的1个儿子和3个女儿中,母亲是那时唯一归来的。家里没有她的田地,她只好在村子里的宗族公共食堂吃饭。直到1950年,谭珊英才有了工作,在小学教书。
在那个年代,这个家庭并没有享受多少团聚时光。几乎每一次政治运动,都要在这个家庭里掀起波澜。文化大革命开始,谭珊英因为陶铸的问题被牵连,隔离审查,然后是关牛棚,下放五七干校。其间整整3年,都无法和家人见面,连通信都断绝。谭珊英也曾写信给孩子,希望“能回来转转,多给我以思想上的帮助”,但这样的愿望只能落空。
在五七干校的时候,谭珊英早已到了该退休的年纪,却因为历史问题悬而未决不能离开。陈洣加和谭安利都在那几年迎来自己的孩子,作为奶奶的她一心想要请假去照顾,但是请假条交上去,得不到批准,只好自己一个人在干校,等待孙辈降生的消息。
谭安利决定把1500余封家书全部捐给家书博物馆。如今,已经有5万多封家书藏在这里。这些普通家庭的书信,曾经和中国最重要的文物一起,被送进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后来又登上了综艺节目《见字如面》的舞台,在网络上“红”了一把。

1934年,谭珊英和陈柏生在上海
“不仅打开历史的一扇窗,也打开人性的一扇窗”是《见字如面》的选信标准。这些本来无意发表的书信,“就像一个人在自己家客厅一样,穿着随便”,展现人性最真实的一面。
洣,意思是要以洣水为家,最后却没有了家
谭安利现在越来越感觉到家庭的重要性,他努力把家人团聚在一起。可在深圳待久了,他也慢慢不能习惯老家湖南的气候和氛围。
他1990年来到深圳,此前在湖南衡阳机械工业局的一个下属公司做经理。但随着计划经济的壁垒打破,这个曾经风光无比的单位连工资都发不下来。他不得不带领一批人到深圳“打开一扇窗”。妻子还在衡阳的工厂里上班,大女儿眼看要第一次走出家门读大学,年迈的母亲正在步入人生最后的时光。这一家人又一次被新的时代潮流冲散。
在历史的起起落落中,这家人见惯了分分合合。姨妈1952年就“响应党的号召支援内蒙古建设”,最后在那里去世。弟弟1965年高中毕业时决心“学习董家耕献身社会主义新农村”,在山区农村一待就是10年。舅舅后来倒是一直留在老家茶陵,但是因为曾经是国民党的军官,“镇反”时差点丢了性命。
如果不是当年离开家参加革命,谭家可能是另一副模样。在湖南茶陵县美吉村老家,谭安利的外祖父是村子里官做得最大的人。参加革命前,谭珊英也已经从湖南第一女子师范毕业,在当地谋一个教职并不是难事儿。但是这些,都比不上革命气氛对小女孩的吸引力。
当谭珊英再次回到茶陵,就是差不多10年以后的事情了。那一次回到茶陵,她生下了陈洣加。“洣”是距离茶陵美吉村不远的洣水,“意思是要以洣水为家”,但是在那不久,她带着孩子又离开了茶陵。
直到生命的最后,她也没有再回到茶陵的家。新中国成立后,谭珊英随着工作四处搬家,茶陵老家的房子也因无人居住渐渐荒废。从苏联回来后没多久,谭珊英的第一任丈夫陈柏生就因为肺病去世。1942年国共合作期间,谭珊英经人介绍认识了第二任丈夫李华柏。李华柏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副团长,这成了文化大革命时期谭珊英的重要罪状。因为生父李华柏的关系,谭安利也在高考上遇到诸多困难。
除了把书信捐赠给家书博物馆外,谭安利还自费把书信结集出版。并把书名取为《岁月印痕》,有人读完以后跟他说,在这本岁月印痕里,读出了时代的印痕。
当这家人再次分散于全国各地,整理并出版家书是谭安利和亲朋重新建立联系的途径之一。不仅家书的选用都要征集相关当事人的意见,有时候他还会把那些带着时代印痕的家书整理好寄给下一辈看。
家书一遍遍翻看得多了,谭安利对家和家人有了更多理解。谭安利也去找过生父留下的痕迹,去了父亲以前居住的房子。那所房子临着路,可是那里修起了新的宽敞马路,房子早已没了踪影。
(摘自《时代邮刊》2017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