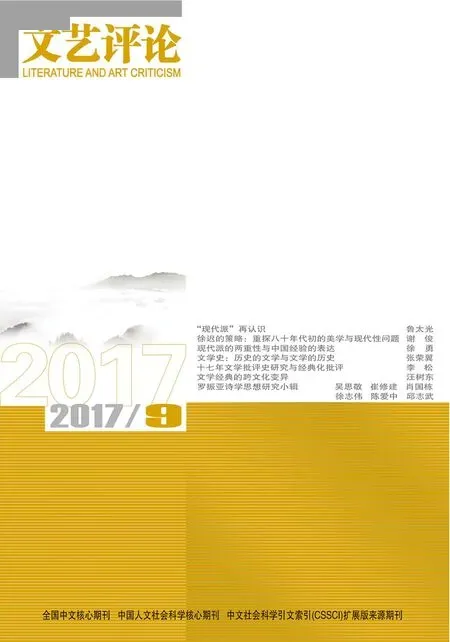罗振亚新诗研究学述
2017-09-28肖国栋
○肖国栋
罗振亚新诗研究学述
○肖国栋
在汉语新诗百年的时间坐标系里,我们所要进行的清理应该有两个方面,一是以新诗本身百年发展与流变作为对象,进行深入研究,系统总结百年汉语新诗的经验与教训等,另一方面,我们还应及时进行这一百年来新诗研究的学术史清理,某种意义上说,汉语新诗百年发展的研究是离不开这种学术史清理的,两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所以,对罗振亚先生的新诗研究做学术史的清理就具有了双重学术意义:一方面现代汉语新诗究竟是如何发展怎样流变的,通过罗振亚先生的新诗研究可以一窥究竟,实际上汉语新诗百年的面貌如何是脱离不开学者选择以何种方式加以呈现的;另一方面,罗振亚先生以他的学术研究参与了汉语新诗百年历史发展过程的三分之一,并且他的著述囊括了新诗整个一百年的历史进程,所以把新诗百年和罗振亚先生的诗学研究并置在一起,是一种十分有益的互相发现。这无论对罗振亚先生个人,还是百年新诗历史的建构,都是极有意味的。
我把罗振亚先生30年新诗研究的学术理路概括为5个特点:百年视野、先锋视角、与诗俱进、精雕个案和有所不为。这5个特点能够体现他的历史观和诗学方法论,更能反映他的审美取向和价值标准。百年汉语新诗借由他的研究呈现出一种丰厚而又单纯、热情但不乏清醒的面貌和品格。
一、百年视野
纵览罗振亚先生30年的新诗研究历程和丰硕成果,我们几乎看不到以“百年”字样为名头的专著(《20世纪中国先锋诗潮》可以视为具有百年命意的命名),这样的论文也极少看到,仅见的两篇是《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潮概观》《中国新诗百年:教训不少启示更多》。
但是我们又分明感觉到,他的全部研究视野是着眼于汉语新诗百年历史建构的。这体现在他几乎以一人之力独立完成了现代新诗百年历史的贯通式研究,比如他在《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史论》中用六章的篇幅从诗歌流派演进的角度梳理了百年新诗的嬗变和承继,按照时间先后论及了象征派、现代诗派、“九叶”诗派、台湾现代派诗、“朦胧”诗派和第三代诗,截止到该著出版的2002年,几乎把现代主义这个脉络里的流派都囊括进来了;在时隔6年出版的《20世纪中国先锋诗潮》这部著作中,他又在“时序”和“流派”这两个维度上续写了《“个人化写作”的确立与分化:20世纪90年代的先锋诗歌》《“另类”的声音:“下半身写作”领衔的’70后诗歌》,及时捕捉和总结诗歌发展的动态讯息,完成并留存了历史的快照,积极参与新诗历史化过程,建构属于他自己的新诗研究的小宇宙。进入21世纪的汉语新诗也同样反映在罗振亚先生追踪新诗历史轨迹的目光里,被加以频繁聚光和多维度考释,这些论述或着眼于新世纪诗歌发展的整体取向与特质,或着重于性别流派,或瞩目于特定理论问题,或流连于年份扫描,不一而足,也几乎无所不包,比如《新世纪诗歌形象的重构及其障碍》《新世纪诗歌写作:方式、特质与问题》《在突破中建构:论新世纪女性诗歌的精神向度》《21世纪诗歌“及物”路上的行进与摇摆》《沉静中的悄然生长——2010年中国诗歌观察》等论文。此外,他还以诗人专论的形式,随时写下他对当下诗歌写作的观感、意见与建议,这种写作既是一种标准的诗歌批评,同时随着时间的流逝,也必将成为当下诗歌史建构的一部分资源,同样不失为一种有着独特价值、不可替代的新诗研究的历史建构方式。因此,所谓百年汉语新诗,如果作为一种历史形态的概念和命题,其历史阶段性特征和内涵缺少了罗振亚先生(以及像他这样紧密跟踪诗歌发展进行研究的同类学者)的诗学研究,是很难成立的。
二、先锋视角
在罗振亚先生的百年新诗研究中,他几乎把所有精力都灌注于对具有独创或反叛精神、更多关注个体、诗艺更具有现代性倾向的这样一个谱系的发掘和研究。他在《近二十年先锋诗歌的历史流程与艺术取向》一文中,对先锋诗歌的概念有一个提炼:
“先锋诗歌”兼具时间与社会学意义,当是那些具有超前意识和革新精神的实验性探索性诗歌的统称,它至少具备反叛性、实验性和边缘性三点特征。
同时,他“惊喜”地发现,在夹杂一些浪漫主义诗歌在内的以现代主义为主体、注意探索诗歌与心灵内宇宙联系更突出艺术价值的内倾诗(包括新月诗派、象征诗派、“现代”诗派、九叶诗派、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现代诗派、朦胧诗派的诗歌)那里,组构起一条颇为壮观的连绵风景线,它们都堪称各自时代诗歌阵营中的先遣队,只是那时从来没有人用“先锋诗歌”的字样为后一流脉命名。①结合罗振亚先生在上述论文中的这一描述,我们不难发现,他是自觉把梳理先锋诗歌这一流脉作为自己的学术使命的。在此前后的三十年中,他可谓孜孜不倦、一心一意地进行现代主义诗歌研究,源源不断地贡献着凝聚了他的才情和智慧的著述,称得上是在完成一项投入巨大的工程。
他之所以自觉选取“先锋”视角进行百年新诗研究,在我看来是具有历史再生产和续写文学史意义的。所谓“历史再生产”是指罗振亚先生对先锋诗歌这一流脉所进行的清理和研究,拂去了它身上覆盖的历史尘埃,复活了它鲜活丰富和充满创意的本真面目,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这段历史的“命名”和再生产。所谓“续写文学史”是针对于他对先锋诗歌进行跟踪研究而说的,无论自觉与否,这种研究终将会沉淀为未来先锋诗歌研究的历史的一部分,并自然会构成对已经具有稳定历史形态的前先锋诗歌史的续写。在这样两个向度上,罗振亚先生又表现出钩沉历史力图鲜活可感、续写当下务求冷静辩证的述史方式,很好地反向把握了历史描述的分寸感,实现了同情之理解和审慎之热情的辩证统一。
三、与诗俱进
关于这一点,我想强调的是罗振亚先生对当下新诗发展的追踪研究,这反映在他一系列重要的论文和论著中,时间和研究对象始于20世纪80年代前期和中期的朦胧诗,并紧密结合着当代新诗的创作延伸到当下,及时对新诗的创作与流变加以批评和总结,给予其理论化提炼、历史性省思。这样一份参与新诗历史进程的热情和理论敏感是难能可贵的,也是需要极大勇气的。我记得陆耀东先生在给罗振亚的《朦胧诗后先锋诗歌研究》撰写序言时就比较审慎地说:他的著作“涉及的是尚未成为历史的‘现象’,而且评价分明,恐招驳论”。②关于当代文学或当下文学是否宜于写史的问题,一直是一个见仁见智的事。这对于一些稳健谨慎的学者来说,甚至具有相当程度的冒险意味,在他们看来可能或难免陷入争议。但是,克罗齐也说过一切历史在某种意义上说也都是当代史,因此以一个亲历者的身份对当下先锋诗歌进行跟踪研究,反而具有了某种历史叙写的优势。
这类跟踪式研究成果在他的全部著述中至少占有半壁江山,而且选题的视角相当丰富,并且随着他对现代先锋诗歌历史清理相对告一段落之后,对当下先锋诗歌的研究与批评投入了更多的精力,出产的成果也更加丰硕,可以说是蔚为大观。他对当下诗歌的跟踪研究与批评,大而言之是出于一种学者的责任感,小而言之也是一种为人的热情和朴厚。所以,我们既能看到他从宏观角度对新诗发展动向的迅速捕捉与宏观概括,前文已经结合他的新世纪诗歌研究有所述及,这可以视为一种学者对学术的责任和敏锐。另一方面,他的跟踪式研究更多地体现为针对诗歌写作个体进行的无微不至的批评和助推,他通过自己的批评保留了一种与当下诗歌写作水乳交融的细腻感受和鲜活细节。我甚至在隐约之间感觉到,正是这种植根于诗坛与诗人的近距离互动,才使他在出入诗与史的研究时拥有那样一种不乏深沉的活力和不失生机的理性,彰显了学问与诗的双重魅力。
四、精雕个案
罗振亚先生的百年新诗研究有一个十分关键的着力点就是个案研究,这种个案或者体现为一些著名或有特点的诗人研究,或者聚焦于一个流派的研究,表现形式是多样的。他是有意识地把个案作为历史要素加以研究和配置的,使其作为一种历史视野的支点撑起整个理论或史学论述的架构。所以,我们把他研究的个案串联起来,就是一部出色的百年新诗史,有着非常清晰的脉络和面向,彰显的是他强烈的对于诗歌流变和个体创作的双重关怀。就其所着重研究的流派而论,涉及到象征诗派、新月诗派、乡土诗派、20世纪30年代现实主义诗派、现代诗派、九叶诗派、朦胧诗派、第三代诗、女性主义诗歌、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等等,组合起来基本等于一部中国新诗流派史,当然是一部以流派为个案的诗歌史。基于流派研究的基础和需求,罗振亚先生对于诗人个体的研究同样相当丰富和充分,以上所列流派之中,除了乡土诗派、20世纪30年代现实主义诗派之外,其余流派所属重要诗人均有个案研究,现代诗人诸如胡适、闻一多、徐志摩、李金发、戴望舒、卞之琳、何其芳、废名、林庚、金克木、施蛰存、徐迟、路易士、艾青、穆旦等,当代诗人诸如海子、胡弦、西川、梁平、张曙光、李琦、于坚、伊沙、翟永明、巨狼、李少君、任白、王小妮等等,这个重要诗人的名单整整贯穿百年汉语新诗发展的全过程。
在讨论灵魂“个案”解读时(这一提法见《问诗录》),我想着重提出《雪夜风灯——李琦论》这部著作,可以说这是罗振亚先生所做最具规模的一个个案研究。除了作为个案研究的规模巨大之外,我觉得这部虽然未必产生重要影响的著作还充分体现了其间灌注的地方精神文化的特殊质地,它是龙江特色作家研究丛书中的一种,具有乡邦文献的性质,老实说没有几个地方作家能够获此殊荣。但是,正因为是这样,可以说罗振亚先生用这样一部个案从时间与历史的洪流中打捞了龙江文学的生命与情感的丰厚具象,它的可贵就在于这种鲜明的地方性,就在于它的细小和独特。
在个案研究中,还有一篇以诗体研究为着眼点的论文不能不提,这就是《中国社会科学》在2010年第1期发表的《日本俳句与中国“小诗”的生成》一文。这是一篇角度新颖,辨析精当,阐发系统,剖析深入,发表之后产生广泛影响的力作,可为诗体个案研究的代表性作品。
总之,我们说他是把流派和重要诗人、诗体等多种元素作为历史要素加以配置和研究的,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只是着眼点不同,但是贯通其间的眼光是统一的。当然,这个名单是不完整的,也很难完整,这里潜藏着相当丰富的继续加以解读的空间,因为罗振亚先生还是相当年轻的中年学者,完全没有封闭和停滞的迹象。
五、有所不为
在讨论罗振亚先生诗学研究的百年视野和先锋视角时,就揭示了他的新诗研究有他的角度和侧重,实际上也是暗示了他基本回避了对现代新诗发展中另一个谱系的梳理和研究,比如左翼诗歌、革命现实主义诗歌、十七年诗歌和文革诗歌等等。仅就中国知网检索来看,除了个别文章论及臧克家或乡土诗、现实主义诗派,他唯一一篇讨论十七年诗歌的论文是总结这一阶段诗歌教训的。这就是我所说的有所不为。
任何学者的学术研究都是结合主客观条件,进行综合思考和选择的。我想,罗振亚先生自研究生毕业,就投身于现代美学和先锋诗歌研究,这反映了他的个人趣味、历史觉悟和美学准则等等综合性因素的影响,在有所为与有所不为的抉择中,承担起了在当时具有启蒙和创新意义的学术使命,并在超过三十年的学术坚守中,构建了一个美丽绚烂、充满生机的诗性宇宙,中华民族的诗性血脉在他的笔下和当下先锋诗歌的写作中涌动不息,生生不息。
综合以上的论述,我的结论是,作为一位诗歌史学者和诗歌评论家,罗振亚先生的学术进路坚定扎实,根深叶茂,已经构成了当代诗歌史一道亮丽的风景和不可逾越的堡垒,他的新诗研究将继续发挥阐发作品、推介诗人、建构历史的多方面作用,也值得诗歌研究和评论界寄予厚望,将沾溉诗坛、泽被后世。
(作者单位:齐齐哈尔大学文学与历史文化学院)
①罗振亚《近二十年先锋诗歌的历史流程与艺术取向,诗探索》[J],2005年第1期,第20-37页。
②罗振亚《朦胧诗后先锋诗歌研究》(序一)[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