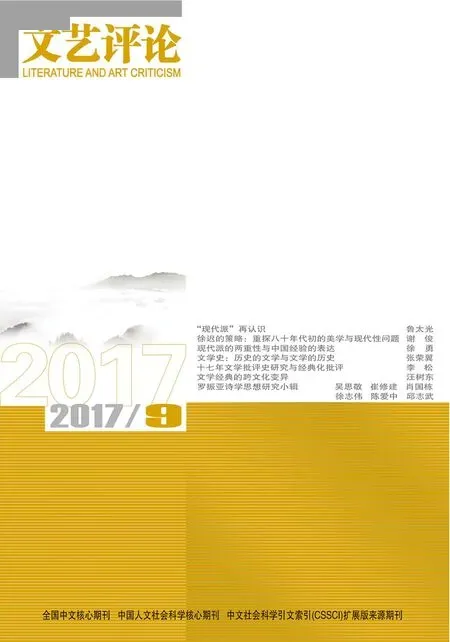现代派的两重性与中国经验的表达
——以《你别无选择》和《顽主》为中心的考察
2017-09-28○徐勇
○徐 勇
现代派的两重性与中国经验的表达
——以《你别无选择》和《顽主》为中心的考察
○徐 勇
在讨论现代派与中国经验之间的关系之前,有必要重温20世纪80年代的两个经典的文学场景。一个是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一个是王朔的《顽主》。先看第一个场景。在《你别无选择》中围绕贾教授和金教授,形成了针对现代派的两派。赞成派以金教授为代表,反对派则以贾教授为核心,两派互相攻击、彼此不满。但有意思的是,在这部小说中,反对派虽然代表秩序,但其实是弱势,因为几乎所有作曲系的学生都对贾教授不满。另一个场景是在《顽主》中,王朔借杨重、马青和于观之口这样调侃“现代派”:
“你不知道这女人是个现代派,爱探讨人生的那种,我没词了,我记住的所有外国人名都说光了。”
“对付现代派是我的强项。”马青在一边说。
于观瞪了一眼,对话筒说:“跟她说尼采。”
……
“你们可快来,我都懵了,过去光听说不信,这下可尝到现代派的厉害了……她向我走来了,我得挂电话了。”
“记住,用弗洛伊德过渡。”
(《王朔谐趣小说选》第11—12页)
两部小说写作发表的时间相近,(《你别无选择》)是写于1984年11月,发表于1985年第3期的《人民文学》;(《顽主》)是发表于1987年第6期《收获》杂志。两部小说中针对现代派的态度截然不同耐人寻味。短短两三年的时间,现代派在人们心中的形象何以出现如此反差?
当然,在《你别无选择》中,我们尽可以把现代派的赞成派视为反叛、“创新”和“不协和”以及对现存秩序的不满。这样看,便会发现,当他们在说现代派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在争夺话语权。也就是说,当他们在言说“现代派”的时候,他们只是在表达某种情绪和态度。他们是以破坏和不合作的热情,参与到这一对现代派的争论中来的。因此,诸如卡夫卡、勋伯格等西方现代派诸代表只是他们用来表达对现实和秩序的不满的资源和符号。至于如何学习卡夫卡和勋伯格,及其如何使之在中国落地生根并结出果实并不是他们所考虑的问题。
如果说卡夫卡和勋伯格在《你别无选择》中只是某种符号的话,那么同样,尼采和弗洛伊德在王朔的《顽主》中也是符号。它们都只是作为能指的符号,没有固定的所指,所以可以无限地罗列下去,就像于观所说,“用弗洛伊德过渡”。这说明,西方的现代派诸代表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很多时候是作为能指的符号的游戏被使用的。所指的不确定和不稳定,决定了前面两个文学场景在现代派的使用方面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如果说王朔的嘲讽,显示出来的是现代派话语的正面意义的消失的话,其实这一点早在《你别无选择》中就已有表征。只不过当时,现代派所具有的创新和反传统的积极意义正当其实。《你别无选择》这一小说告诉我们,现代派在新时期中国的语境,自开始就存在两种面向和可能。第一种面向是,表明一种批判的态度,一种拒绝传统和反抗平庸的态度。这样一种态度发展到《顽主》中就演变成“爱探讨人生”,与现实日常生活脱节且不务实际的那种。另一种是仅仅作为语词意义上的符号的游戏存在。
这样一种错位,显现出来的其实是现代派的两重性及其分裂。即作为一个总体倾向和作为一个具体流派的两重性。现代派只有结合进具体流派或形式中的时候才能作为一种总体倾向显现其意义,否则就只能作为能指的符号无限延宕。现代派在中国新时期的分裂,显示出来的其实是现代派作为总体倾向和具体流派的分裂。当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的时候,现代派是外在于中国的现实经验的。现代派只能以具体流派或具体技巧的形式呈现其意义。这使我们想起了王蒙的意识流小说以及宗璞的《我是谁?》等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现代主义文学实验。当现代派还只是一种技巧或形式的时候,它其实是内在于中国现实经验之中的,一旦它从一种技巧演变成一种潮流和时尚,其实也就远离了中国现实,而成为一种西方人名或语汇的脱口秀,乃至于成为王朔嘲讽的“过街老鼠”。
王朔的这段文本,其实可以看成是现代派与中国经验之间关系的命题的提出。于观的逻辑很明显,关于现代派,可以谈论尼采,可以以弗洛伊德过渡。也就是说,现代派等于尼采加弗洛伊德,并可以延续下去。这其实是表达了对现代派的批评,当现代派只是可以无限延续下去的能指的时候,其所指何在?是否只是所指缺失的能指的游戏?可见,王朔所表达的,其实是对现代派话语实践在当时造成的能指的无限增值现象的不满。现代派不能是自说自话,不能是空洞无物,不能是无限的滑动的能指。而应该与中国的现实语境相结合,必须有效地参与中国的现实经验的阐释和表达。
一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有过一场关于“伪现代派”的争论。“新潮文学处于两种文本模式之间,同时选择了两个参照物——我们可以从文本的分析中有力地证实这种情况,概括地说,它们常常表现出既想学习‘现代派’文学的观念和手法又明显受到传统的影响,似乎意欲鱼和熊掌兼得,又似乎两意彷徨。假如它们不这样,要么是全然的‘现代派’,要么是全然的传统派,便不会被人称作‘伪现代派’——所谓‘伪’字,正是指这不尴不尬、不伦不类的状态。广而言之,就不仅仅是文学了,我感到当前整个时代的思想都处在两意徘徊的踌躇之中,人们想获得些什么又对另外一些东西难以割舍:上不去下不来、高不攀低不就、新不新旧不旧——这就是目前中国社会与文化面貌的写照,文学中的‘伪现代派’不过是它的一个侧影而已。”①李洁非的这篇文章题名“‘伪’的含义及现实”,很好地表明了有关“现代派”之争与现实的互文关系。
也就是说,有关现代派的讨论,涉及到的不仅仅是文学写作上的形式问题,更是一种思想问题和现实问题。这也是一种形式的意识形态表达。因此需要追问的是,这样一种形式问题,如何才能上升到思想问题和现实问题?它们之间的勾连如何才能成为可能?
这一讨论,其实是关于要不要借鉴现代派,西方的现代派是否可以完全横移到中国的问题的进一步延伸。关于这一点,袁可嘉在写于1987年的一篇文章中仍在强调关于现代派的两分法:“西方现代派与西方现代化具有双重关系:一方面,现代派表现出它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制约的因素,如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自我的矛盾脱节的现象,社会悲观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之类的思想,以及一部分作家对艺术技巧的盲目追求,并无意义的标新立异,这些,与社会主义的中国是不协调的;另一方面,它又有不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制约的因素。如科技革命和社会科学新发现,实际生活新变化所引起的现代人类的思维方式、感受方式、表达方式上的变革,它们代表人类认识能力的进步,是与任何国家的现代化过程相通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生活和文学中同样已经初步出现这类变化。这些重大变革必然会导致对文学主体认识的某些变化和新技巧的实验、新理论的探索和新研究方法的采用。”②袁可嘉的这篇文章让我们想到《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中他的序言及其相关文字;同样,这一文章也让我们想起茅盾写于1958年的《夜读偶记》中的相关文字。他们的逻辑很明显,都是采用形式和内容二分法,所不同的是,在茅盾那里,形式技巧与思想内容之间密不可分,因此现代派不能借鉴,袁可嘉则倾向于提出它们间的区分,以此表达对现代派的某种程度的肯定。这样一种在形式和内容上的二分法是当代中国(包括上世纪50—70年代)讨论现代派时的焦点和“认识论基础”。比如冯骥才、李陀和刘心武三人《关于“现代派”的通信》中所争论的也是这个问题。就像李陀所说:“形式和内容往往有着密切的联系,一定的形式又是为一定的内容服务的……这些表现技巧中哪些因素有可能和它们特定的表现内容分离开来,成为我们吸收、借鉴的营养呢?这不能不是一个需要谨慎对待的问题。”③
从以上不同时代的关于现代派的讨论中,不难看出,他们提出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现代派与中国经验的关系问题。其中一个核心问题是,形式是否具有独立性,因而具有普遍意义?其普遍意义又如何与中国的语境相结合?对于这一问题,如果不能跳出这一二元对立模式的束缚,理论上便不可能有更深一步的探索。其逻辑上的结果只能是:要么全面否定,要么完全肯定,或者既肯定又否定(辩证法)。20世纪50—80年代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从前面王朔的小说可以看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实际情况是,现代派已经深入人心,虽然在理论上仍有很多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所以,此时袁可嘉的文章,虽然在思路上同他写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文章有一脉相承之处,但其实完全是两个不同的福柯意义上的“声明”。语境的不同,决定了这一篇文章(《中国与现代主义:十年新经验》),具有了为所谓的“伪现代派”辩护的意味,而不仅仅是为现代派的合法性辩护。因为这一合法性已经不再成为问题,此时成问题的是当现代派在中国流行后如何与中国现实相耦合的问题,以及如何或能否保持中国传统的问题。就像前面所引的袁可嘉在同一文章中所说:“如果我们在强调借鉴西方现代派的同时,轻率地否定我们自己传统中的优秀部分,那就是很不明智的。”④
二
20世纪80年代早期,在关于现代派的争论中,其中一个核心问题是懂与不懂的问题。这在关于朦胧诗和王蒙等作家的小说创作的争论中都有呈现。王蒙在一篇与读者的通信中指出:“你为什么不懂呢,因为你已经习惯了看情节小说,而情节小说里提到的物件总是具有道具的性质,提到的环境总是具有布景的性质,提到的气象以及音响总是带有灯光、效果的性质,都与中心情节,与所谓‘主线’有密切的关系。例如,如果提到一双皮鞋,那就要弄清这双皮鞋是不是赃物?是不是罪犯穿过而成为破案线索?是不是爱情的礼物或订婚的信物?然而《春之声》的写法却不是这样的。”⑤王蒙的这段话很值得分析。这段话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即现实应该以一种什么方式进入小说。它应该是以连贯的有头有尾的讲故事的方式(即“情节小说”式),还是应该打破这种彼此联系的方式,而单独以事件本身的形式呈现?王蒙提到的“皮鞋”这一细节很有意思。这篇小说中,出现的“三接头皮鞋”这一细节,看似闲笔,但其实具有典型的20世纪80年代特定时代的意义。这一“三接头皮鞋”与“电子石英表”“结婚宴席”“差额选举”在小说中的关系,是以联想的方式建立起来的,按照王蒙的话说“通过主人公的联想,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把笔触伸向过去和现在,外国和中国,城市和乡村”⑥。可以说,这既是主人公的联想,也是读者阅读时的联想,通过联想的方式,20世纪80年代的现实进入了文本。而这,恰恰是传统现实主义小说所不具备的。某种程度上,现代派的意义,正在于建立了“情节小说”之外以联想的方式联结现实的意义。它实现的是现实在小说中的联想的存在方式,而不是彼此之间的简单的因果逻辑关系。
这一联想的方式,建构了情节和情节、意象与意象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建构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方式。就像王蒙所说:“这种靠联想来组织素材、放射性结构的手法当然有借鉴外国文学、包括借鉴现代派手法之处。然而这生活、这思想、这感受、这语言、这人物、这心理,这都是货真价实的国货土产。国货土产中又出现了斯图加特、法兰克福、斯特劳斯这样的洋词儿,这正是80年代中国的特点。”⑦联想创造了情节和时间的并置的形式,让现实在小说中以一种多层次并置一起的方式呈现。也就是说,联想创造了历时和共时并存的局面,传统现实主义则常常是一种单线或多线并行的方式。
可见,在这里,“懂”与“不懂”所涉及到的,并不是文学与现实的表现/被表现关系,而毋宁说是通过文学理解现实的问题。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提供了通过文学理解现实的模式,这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我们是通过理解文学来理解现实从而介入现实的。现代主义则相反。它不仅打破了这一关系,而且使得文学和现实的关系出现逆转:我们必须从现实本身的角度来理解文学,而不是相反。现实本身的混乱和文学中现实存在的非理性,是使得现实在小说中难以被理解的原因之所在,前引王蒙信中的读者遇到的“不懂”的问题,正是这个问题。这是双重的难度,既是理解小说中的现实的难度,也是理解现实本身的难度。现代派的难题正在于如何重建两者的联系。
今天看来,现代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的实验具有如下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方面,王蒙等人的技巧上的实验,他们的作品当时虽然被斥之为“读不懂”,但正是这“读不懂”里蕴涵了现实进入文学的另一种方式。即文学如何在“懂”与“不懂”之间建立一种平衡,从而创造一种现实进入文学(特别是小说)的可被理解的方式。这是以联想的方式,而不是逻辑的方式,建构现实与文学的关系。这一模式,在朦胧诗创作中有鲜明体现,此后为先锋派所继承,乃至被发挥到极致。先锋派不仅造成了现实在小说被理解的难度,还打破了现实本身和文本中的现实之间的互文关系,使得它们之间两不相干。先锋派后来的转向,充分证明了这一打破逻辑关系的联想方式的局限所在。
另一方面是刘索拉和徐星等人的作品,他们的主人公以一种叛逆的桀骜不驯的形象显示出来的其实是一种针对现实日常的批判态度。但在形式方面,比如说表现在具体如何作曲上,他们小说的主人公却不知道怎样去反抗,“现代派”只是它们的反抗的武器,而不是形式建设的借鉴,《你别无选择》中森森的苦闷,正是这一苦闷的表现。这其实是告诉我们,现实在小说中是以否定的形式呈现自身的,某种程度上其实是提出了现实在小说中的存在方式问题。当现实以否定的形式存在时,并不意味着现实的不可理解,而只是表明现实的另一种存在形态。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对应关系:以现实反映主流意识形态,两者彼此对应。现实在小说的存在方式可以是多样化的。
综合王蒙等人和刘索拉等人的两方面的努力,可以看出,他们并不是要打破文学同现实之间的关系,而毋宁说是建立现实与文学之间的重新联结的方式。
三
熟悉西方文学史的人大都知道,现代主义作为一个潮流确实存在过,但界定它却很难。就像彼得盖伊所说:“从来没有学者试图将现代主义的所有表现形式详细地罗列出来。”⑧这意味着,谈论现代主义,必须从两个层面展开,一是从现代主义的总体倾向,一是从具体的各种形式的现代派入手。必须把两个层面结合起来,才能有效把握现代主义。就前者而言,就是“所有的现代主义者都毋庸置疑地达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不同寻常、标新立异和实验性强的东西显然比那些耳熟能详、司空见惯和按部就班的东西更加魅力无穷”⑨。换言之,现代主义必须建构“他者”和对立物,没有“他者”,便没有现代主义。只有建立“他者”,才能完成他们的标新立异。这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的两个规定性内涵。他们当时的一个共识就是,把“文革”视为“他者”,以文化的“现代化”作为主体建构的目标,视西方现代主义诸流派为其资源。这正是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特有的“现代主义氛围”。“现代主义氛围”是彼得盖伊的说法,“这种氛围是现代主义革命的重要前提。在这种氛围中,不论社会大众有多么地不情愿,他们还是可以接受对传统艺术习惯的严重背离,认可非主流的审美观以及各种艺术风格之间的冲突”⑩。20世纪80年代的特定语境,创造了现代主义可以接受的氛围,这一氛围,就是可以不证自明地把“文革”视为“他者”,并把传统与之对应起来。这也决定了“现代主义革命”必须不断地从“文革”和“传统”中汲取前进的动力,否则便会枯竭,失去其革命性。反过来说,则意味着,当现代主义失去了“他者”和反抗的对象之后,它也就失去了意义,而变成一种自我言说和话语上的增值。王朔眼中的现代派就是这样一种自我的话语增值。因此,对于王朔而言,他所反对的是这种失去了“他者”和主体建构目标的现代主义的自我表演,而不是“现代主义”的总体精神。在王朔看来,现代主义(现代派)需要不断构筑“他者”,而不是把“他者”建构出来之后就定于一尊(即以“文革”作为“大他者”),以此展开其话语上的不断的自我增值。可以说,正是这不断地重建“他者”,才是现代派具有中国经验和当下性的切入点。因为,只有不断地结合现实语境,重建“他者”,才可以同中国的现实和经验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找到中国经验的表达方式。从这个角度看,现代主义各流派都只是一种中间状态和过渡形式。它们就单个而言永远都无法完成对现实的充分表达和把握。
这样一种不断建立“他者”的实践,其实也就是阿甘本意义上的“同时代性”[11]问题。当它作为一种总体称谓的时候,表明的是一种针对现实的态度,一种所谓的“审美的现代性”,但这样一种“同时代性”,只有落实到某一流派或某一技巧时才有意义,而不应是一种空洞的能指。建立“他者”,也就建立了现代派的主体位置,只有这样,现代派才能同时作为批判立场和创新性而显现其存在。只有这样才能建立其“同时代性”的位置。
最后还是回到《你别无选择》。其中有一个细节可能为大多数读者和论者所忽略,即森森的苦恼和困惑问题。森森是现代派的推崇者,但他与一般意义上的现代派不同。
森森的苦恼,其实也就是现代派与中国经验之间关系的苦恼,也即如何在民族的和世界的之间寻找平衡的苦恼。森森并没有加入到他的同学们的叛逆的行为中,他一直都在寻找,以至于毕业典礼开始时,森森还在琴房里苦苦思索,做困兽斗。小说没有为森森的困惑提供解决之道,但它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可能。小说结尾,森森无意中翻出“一盘五年都不曾听过的磁带,封面上写着:《莫扎特朱庇特C大调交响乐》。他下意识地关上了自己的音乐,把这盘磁带放进录音机。顿时,一种清新而健全、充满了阳关的音响深深笼罩了他。他感到从未有过的解脱。仿佛置身一个纯净的圣地,空气中所有浑浊不堪的杂物都荡然无存。他欣喜若狂,打开窗户看看清净如玉的天空,伸手感觉大自然的气流。突然,他哭了”。这里的“五年”看似随意,其实隐含深意。小说写作的时间是1984年11月,五年前即1979年,那时刚好是“文革”结束,追求创新和反传统,是当时的潮流,在这种情形下,古典被很多人认为是不合时宜的和保守的,因而不被关注。森森五年来都不听,正说明了这点。但也恰恰是这点,使得现代派与传统和古典之间,人为制造出一种对立,他们不会想到也不可能想到要去吸收传统和古典中可以吸收的地方。前面所引的王朔的小说,所显示出来的某种程度上就是现代派所造成的词语的盛宴。也即所谓“爱探讨人生”但却只限于在弗洛伊德和尼采等“外国人名”之间无尽地滑动。它们与中国现实之间是一种脱节的关系。或许还可以这样理解,这是词语与词语之间的游戏,而与现实不构成对话关系。他们找不到出路,或许正源于此。关于这一点,可以以北村的小说《最后的艺术家》为例。小说中的艺术家们就是一群现代主义的追求者,但他们只会表达狂热的拒绝的态度,制造事件,故作耸人之语,而不知道如何面对日益发展变化的现实,其结果,最后被社会淘汰乃至疯掉也就是必然而然的事情了。如此种种一再表明,现代主义要想在中国生根发芽并结出伟大的艺术之花,就必须学会努力面对日益发展变化的现实,而不仅仅是在“外国人名”上来回绕圈。从这点来看,王蒙和朦胧诗诸诗人的创作提供的经验或教训,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①李洁非《“伪”的含义及现实》[J],《百家》,1988年第5期。
②④袁可嘉《中国与现代主义:十年新经验》[J],《文艺研究》,1988第4期。
③李陀《“现代小说”不等于“现代派”——李陀给刘心武的信》[A],载洪子诚编《中国当代文学史·史料选》[C],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68页。
⑤⑥⑦王蒙《关于〈春之声〉的通信》[A],彭华生、钱光培编《新时期作家谈创作》[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64页,第466页,第466页。
⑧⑨⑩彼得·盖伊《现代主义》[M],骆守怡、杜冬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17年版,第6页,第6页,第29页。
[11]参见吉奥齐·阿甘本《裸体》[C],黄晓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8-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