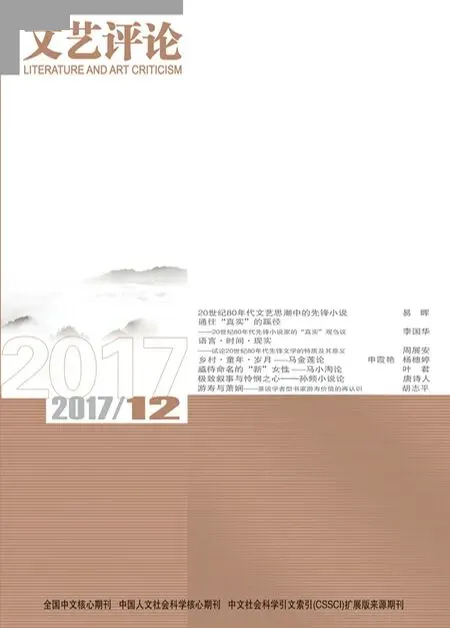在现实与想象中纠葛:贾平凹《极花》的叙事艺术
2017-09-28○程华
○程 华
在现实与想象中纠葛:贾平凹《极花》的叙事艺术
○程 华
秘鲁伟大的作家加尔克斯·略萨认为,任何虚构文学都是“由想象力和手工艺技术在某些事实、人物和环境的基础上树立起来的建筑物”①。这么说来,当作家对某一现实生活中的素材发生兴趣,并要依此素材完成一件虚构性的文学作品时,他要做的工作就是如何发挥想象力,使这件紧贴现实的素材飞起来,使想象和现实融合。贾平凹近几年关于农村题材的作品都是指涉现实的,他也总能借助文学手法,在现实和想象之间进行很好的调度,这部《极花》也不例外。原始素材是作者十年前听到的真人真事,对类似社会新闻事件的想象和编织需要高超的技巧,《极花》不论是叙事视角的选择,还是超越现实的叙事,以及作品中的象征和隐喻等暗示手法的使用,都有想象力参与其中,作者借助这一系列叙事手法,企图完成对真实事件的超越,同时在想象的背后,注入作者对人生内容和社会历史的思考。
一、限知叙事视角及其现实指涉
小说一开始即透过女主人公胡蝶的视角描绘出这样一幅画面:金锁因为媳妇被蜂蛰死而疯了,顺子爹因为儿媳妇被外地人拐跑而自杀,这两件事的背后就可看出这个近乎封闭的圪梁村里弥漫着非同一般的空气,男人们对女人的非正常死亡或离去的恐惧。在贾平凹看来,“原来是经济可能把一个村子毁掉,现在是从性上彻底毁掉,从人种上彻底把村子毁掉,这是从根子上把人毁了”②。这是现实农村生活的实景呈现。农村的消亡一部分是因为撤村并乡城镇一体化的发展,另一部分是在那些贫穷偏僻的乡村,因为种种原因未在城里谋生的男人逐渐沦落为光棍而在人们的视野里消亡。贾平凹是从人种难以繁殖为继的层面,关注光棍村,也从这里打开缺口,引入被拐卖妇女胡蝶的故事。当农村的女人们不愿回到出生地,呆在村子里的光棍会以掳掠的方式,维系自身及村子的生存与延续,这是真实的事件。这真实的事件背后似乎有这样的声音:这种野蛮掳掠的暴力行为,是传统农村在现代化背景下挣扎与反抗的一种方式。贾平凹用文学的方式,将城市与农村并置在这个时代面前,也并置于读者面前。
胡蝶,因其波折的经历,被贾平凹赋予极丰富的想象。同时,也在叙事层面具有其他人物不可替代的作用。胡蝶作为千万离乡者的一员,见证了城市化不可摧毁的力量;胡蝶又以非正常的方式被暴力挟裹到农村,充当生殖繁衍的工具;在这个大时代下,胡蝶这个形象就成了农村最后走向灭绝的见证者;在文学的想象中,胡蝶也成为联系城市和农村两种文化力量的关键人物。在小说中,圪梁村是胡蝶被拐卖进的村子,如果把圪梁村看作是中国最后一个农村,那么这个村子里的文化生态是值得关注的,小说通过猴子、黑亮等人说明农村找不到女人,是因为城市将农村的女人都卷走了。这也说明,作者其实欲将胡蝶作为农耕文明和城市文化在最后较量中的见证者,从而思考城乡发展何去何从。作为见证者的胡蝶,就是叙事的关键元素。如何叙事,才能提供如亲历般的真实经验,作者选取了以胡蝶作为第一人称限知叙事视角。贾平凹在和韩鲁华的访谈中谈到:
写《极花》的时候,也想用个第三人称来写,第三人称的好处就在于它可以铺开来写,但是写着写着就觉得毕竟拐卖如果把它铺开来写,它就是一个单纯的故事,这个故事不可能涉及到更多更多面,这个故事不可能涉及到我刚才说的整个农村的这种情况。那就说是换一个第一人称,就只能把它篇幅写小,它这个故事情节简单,主要是心理的东西,心理的东西在写的时候,就写短一点,就以她这个眼光,看她在村子里看到的一些情况,就这样写。所以这一切都要看你想写啥,再者题材就把你决定了。③
小说以胡蝶的视角叙写其在圪梁村经历的事实。胡蝶作为被拐卖妇女在圪梁村经历的惨痛经历无疑是兽性对人性的摧残,作者突出了群体势力对胡蝶个人身体的戕害。小说中两次写胡蝶身体遭暴力侮辱:一次是胡蝶企图逃出窑洞,被村里的光棍们凌辱,在胡蝶的眼里,他们已经变成了一群狼;一次叙写黑亮在全村人的帮凶下,凌辱和占有了胡蝶。胡蝶作为黑亮买来的媳妇,在小说中是在群体力量的帮助下,完成了生殖和繁衍的行为,突出群体的兽性和残暴。在农村和城市的对抗中,这种群体参与的嗜血的暴力暗含农村的衰微。
贾平凹绝不仅仅只是在叙说对女性凌辱的暴力行为,暴力的背后是城乡文化的较量,包含有在较量中呈现出的复杂的文化和心理因素。胡蝶被拐卖和禁闭后,自身所遭到的惨痛的事实,主要是以圪梁村光棍们的行为呈现出来。作者运用暗示和隐喻的手法,突出了男人们的内心焦虑。小说中出现的血葱,可以激发生殖的力量;黑亮父亲雕刻的石女人,也是村民对女人的臆想,这都“暗示了性苦闷在农村的普泛性、焦虑感”④,村民们集体对胡蝶的暴力性侵犯,也未尝不是男性欲望无法实现的一种报复性心理。作者透过女性视角,正视圪梁村的男人们的现实问题,将城市与农村的对立与冲突表现出来,农村的野蛮性存在,未必没有城市文明的压迫与侵犯,圪梁村光棍们的现实生存是通过正常的渠道找不到媳妇,因而也就会有胡蝶们被拐卖、被凌辱以及被禁锢的事实。贾平凹从两性层面,凸显村庄的灭绝,这是一种关乎人性、关乎历史也关乎文化的独特而深刻的视角。经济贫穷,文化落后,导致女人们离乡出走;为了避免村子的灭绝,就会产生灭绝人性的交易和野蛮兽性的行为;人性的野蛮和道德的沦丧是城市文明的压抑,这是恶性循环的结果,这也是贾平凹所关注的落后农村的现实存在。
二、民间文化资源与小说的超越性想象
如何叙事才能使作品既指涉现实,又具有超越现实的力量,这是对作者虚构能力的考验。如若只是纯粹叙写胡蝶在圪梁村的真实经历,作品因为贴近现实无法承载更多的思考。贾平凹之前的作品,多用非正常人的视角达到一种超越现实的叙事和想象,比如《秦腔》中疯子引生的视角,《古炉》中的儿童视角,《老生》中能穿越生死的唱师的视角,非正常人视角的运用,突破了现实的拘囿,可以承载更多想象的空间。在《极花》中,胡蝶是一个受过高中文化教育的正常人,胡蝶眼中的事实,比较近于生活真实,胡蝶作为第一人称限知视角还是很难发挥出更多超越现实的想象内容。
一个作家的文学想象,总是受制于其思想认识和对文学的看法。莫言作品中充满奇幻的历史传奇,源于具有奇幻文学源头的齐文化背景,动荡的民间历史和传奇故事能激发莫言的创作欲望。贾平凹的文学接受与传统文化渊源颇深,其对民间道德和传统文化思考较为深入,传统和民间文化资源能给贾平凹提供更多的文学想象。比如《极花》中关于“分星分野”的插入,和《老生》中《山海经》内容的大段插入有异曲同工之妙。再往前追溯,《秦腔》里的秦腔片段的插入,《古炉》里善人说病文字的插入,这些素材多源自民间,恰说明贾平凹的文学创作特征。在现实的叙事中加入奇幻的想象,和将现实叙事纳入到悠远的历史和深广的民间中一样,都是文学的超越性想象。贾平凹的小说多取材现实,如若从现实素材讲故事,容易使人对号入座,故事很难超越现实,这种具有民族历史特点或是具有民间文化含义的意象,充当小说叙事内容,与故事紧密联系,与人物和情节自然粘合,不仅使当前故事具有悠远的民间与历史意蕴,也是一种超越性的想象,给作品增添迷离神秘的意味。
老老爷关于“分星分野”的论述,出现在胡蝶被禁闭在窑洞里六个月后,顺子爹死后,全村人都去吊唁,胡蝶被禁闭在窑洞,与窗外的老老爷对谈,老老爷说:“天上的星空划分为分星,地下的区域划分为分野,天上地下对应着,合称星野。”⑤“分星分野”的论述在作品里是很自然的锲入。胡蝶被蒙着眼带入圪梁村,在现实中,其对自己处所的认知是蒙昧的。引入“星野”的说法,时间上可回溯,空间上可定位,还与中国远古的民间有了联系,这样的艺术设置和安排,就拉长了作品事件背后的历史空间和隐喻空间,就像《老生》中的《山海经》一样,具有历史渊源的文化意象的插入,“如同站在历史的高处俯瞰历史”⑥,贾平凹通过艺术构思,让其作品具有丰富的表现和阐释空间。
在胡蝶的视野下,老老爷的思维和城市文明的思维相对立,是一种反现代的思维观念,比如:
瞎子看天,拴牢说:“他看天?他能看见天?”老老爷说:“天可看他么。”……我往好豆子里捡坏豆子,老老爷说,你往出捡好豆子么……黑亮买来瓷碗,刘全喜喊叫让我挑碗,老老爷说,不是人挑碗,是碗要挑选人。⑦
老老爷代表的思维观念不是从人的维度看天地与自然,在他那里,是天地神人共同存在于一个世界之中。老老爷说:“地下一个人,天上一颗星。”⑧天地人间,万物有灵,人的精神世界在现代社会尤其需要神的照护。在胡蝶受到屈辱、魂魄不能安位时,神的力量就显现出来。小说中,老老爷让黑亮他爹找麻子婶为胡蝶招魂,招魂的方式是将用纸剪成的小红人贴在房间各处,剪纸原本是祭祀鬼神的方式,是一种与神对话的方式,最后使胡蝶神情安然。老老爷说:“戏是要给神唱的,安顿下神了,神会保佑咱村子的。”⑨对神的敬祈,使老老爷的形象更像是民间的巫者。氏族时代,巫师是与神鬼沟通的法师,巫的作用如同君王,“巫君合一”是氏族文化时期的巫史传统。⑩贾平凹之前的作品中也出现过类似能与神灵沟通的巫者,但其旨在营造神秘的氛围。自《古炉》中的善人,《老生》中的唱师,以及《带灯》中自始至终的寺庙线索,再到《极花》中的老老爷,贾平凹的兴趣已经不是在作品中营造巫的氛围,而是在思考民间宗教对医治现代人心的作用。老老爷身上的天地神人一体的整体思维观念更为贾平凹所看重,其将天地人纳入到大自然中,有生态反思的意识,还有更为素朴的民间宗教意识。
作为民间巫者的老老爷,同时也是乡村的智者,其智慧的背后有民间道德和传统文化的支撑。他“按照仁、智、德、义、信、孝、理等给村人起名”“每年还用毛笔撰写笔画异常繁多的古汉字送给村人,寓意各种吉祥幸福。每年二月二,老老爷把用五彩的细线编成的彩花绳儿,一一拴在全村人的手上,寓意平安兴旺”⑪。老老爷就如同李泽厚先生所说的巫史,起着沟通天人、凝聚人心、保持秩序的作用,他是圪梁村里的精神治愈师。
胡蝶经过暴力蹂躏后的精神归位正是受到老老爷的影响而发生变化的。胡蝶怀孕后,在圪梁村的上空找到了属于她和孩子一大一小的两颗星,也就在找到自己归属的星之后,胡蝶的生活中有了光:
我看着我的身子,在窗纸的朦胧里是那样的洁白,像是在发光,这光也映着黑亮有了光亮,我看见了窑壁上的板架,板架上的罐在发光,方桌在发光,麻袋和瓮都在发光,而窑后角的凳子上爬着了一只老鼠,老鼠也在发光。⑫
老老爷连同他的民间智慧和乡土文化,作为想象性的存在,成为贾平凹用以对抗城市对农村的压迫的一种方式。老老爷作为超越现实的想象,也给我们更多的思考,在科技现代化的今天,在人类的生殖繁衍都成为危机的现代,人应该获得怎样更好的存在?是在利益的世界里蝇营狗苟,还是获得精神的栖居?在物质和精神的天平中,是物质更为强大,还是精神更为重要,现代人需要为人性注入什么力量?老老爷身上所具有的天地神人整体思维观念值得我们思考。
三、结构的象征和词语的隐喻
胡蝶作为《极花》的绝对主角是毋庸置疑的。她是小说的叙事者,又是悲剧命运的经历者。加诸她身上的惨痛经历一方面以实景描绘的方式呈现出农村无以为继的现实;而她在圪梁村的所见所感,作者以想象参与其中的叙事方式又使她有了遥望星空的梦想。被拐卖的胡蝶到底该何去何从,无论如何,贾平凹也要给胡蝶一个选择。
贾平凹在小说中写到胡蝶做了一个梦。梦,在贾平凹以往的作品中是很少涉及的,特别是将梦作为结构性的支撑元素,在《极花》中还是第一次。要通过叙事因素完成作者对现实的认识,可以有很多技巧,比如之前说到的叙事者的设置,超越性想象,但以主人公做梦方式进行叙事是比较直接地表现作者对故事的思考。
梦在小说的结尾出现,主人公胡蝶梦见被家人从被拐卖地解救回来,但不堪忍受在城中村的生活,又回到被拐卖地。这和贾氏听到的现实故事如出一辙。在《极花》的后记中,贾平凹叙述了小说的素材来源,作者十年前听到老乡的女儿被拐卖后,家人历经千辛万苦将女儿从被拐地接回,没想到女儿又回到被拐地。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事件为什么会在作品中以梦境的方式处理?这就体现出作者的叙事技巧,是讲述真实的被拐卖妇女的故事,还是借助这个故事,讲述超越故事本身的作者对故事和生活的思考?如果对梦这个叙事形式进行分析,“梦”的形式,就是文学叙事的手法和技巧,作者想要借助梦这种潜意识的心理呈现,完成他对胡蝶命运的设定,表达他对整个作品所要呈现的主题思想的思考。
如果对梦中内容进行分析,那么,这就涉及到一个非常关键的词汇——“回去”,“回去”是关涉到胡蝶命运的重要的关键词,对“回去”的想象和思考,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人物的思考,也是对主题的探索,是贾平凹处理、想象以及借用这个素材进行文学创作最重要的一个词语。对于主人公而言,如若回到父母家,这是大部分读者的共同愿望,那么社会正义得以伸张,但这就成为一个纯粹的社会事件。对回去的处理,贾平凹没有如常理所见,而是想象胡蝶回到了被拐地——圪梁村。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原始素材的主人公回到封闭野蛮的地方?这是作者审慎思考的,而他的小说,其实就是要通过胡蝶被拐卖的事实,揭示这背后的原因,同时,也是站在更开阔的地方,对农村与城市做进一步的文化观照。
贾平凹说,“《极花》中写那个叫胡蝶的女人,何尝不是写我自己的恐惧和无奈呢?”⑬贾平凹多年以来的创作,始终未曾离开过农村,也始终对老百姓的生存充满忧患。在《秦腔》中,他通过秦腔衰微影射了传统农耕文化的没落,也触碰到农村的现实,农村的年轻人逐渐远离农村,土地荒芜,农村逐渐成为空心村。贾平凹在写完《高兴》后,面对记者采访时,他几次说明,城市终归不是农民的家,农民的根据地依然在农村,农村要发展壮大,还需要农民自己的力量,所以在作品里,五福死后,刘高兴背尸还乡,不仅仅是草民恋土、魂归故土的说法,而是从那时起,贾平凹就通过小说情节,表达他对农村现状的思考以及农民命运的探索。写完《高兴》的十年之后,面对他熟悉的农村现状,在农村城镇化的必然趋势下,通过胡蝶的经历,宣示作者这十多年的思考。圪梁村,或许是最后一批农村,将面临着族户的绝种而无以为继,这种绝种比经济的贫穷更可怕。
城市文明在发展的过程中,也是社会现代化和经济市场化的过程,人们的观念逐渐趋于“利”而舍去“义”,导致了现代性的野蛮。“现代性的野蛮是从人类为自己谋利这个角度来讲的。现代性所有的义,是用利来解释的,义是相对的,利是绝对的,是最高原则,资本主义是有史以来最激烈的社会思潮,它摧毁过去的一切,使世界荒原化和简单化。”⑭以利为本的工具理性与美好的人性、人情愈来愈远,人的素朴的道德情感被人的私利欲望控制,这也是近代以来人类道德的堕落、社会的邪恶和苦难的根源。在《极花》中,胡蝶叙写梦中被母亲解救回来,面对城市小报记者和周围人的异样眼光,作者写道:“我觉得他们在扒我的衣服,把我扒得精光而让我羞辱。”⑮比起圪梁村的农民们用暴力摧残身体,精神上的侮辱更为痛苦而难以弥合,贾平凹在《后记》中也谈到,“这些失踪的妇女儿童,让人想的最多的,他们是被拐卖的。这些广告在农村很少见,为什么都集中发生在城市呢?偷抢金钱可以理解,偷抢财物可以理解,怎么就有拐卖妇女儿童的?社会在进步文明着,怎么还有这样的荒蛮和野蛮?”⑯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贾平凹,他看到了社会剧变过程中人们道德观念的沦丧。
乡村的衰亡是必然趋势,但胡蝶在梦中选择衰亡的乡村,是贾平凹在这里看到了乡村在衰亡过程中,仍有令人温情的一面,而这恰是城市过度发展中被忽略的。优质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对农耕文化的破坏力是巨大的,但这种破坏是良莠不齐的,作者借助胡蝶的眼睛,通过老老爷的一系列行为说明,圪梁村中残存着的传统道德和民间风尚是不应被席卷而毁坏的。如同上节所述,对于传统民间道德,贾平凹在他的小说创作中有坚定的引线。从《秦腔》中的秦腔,到《古炉》中的善人说病,以及《带灯》中的寺庙,这都是贾平凹在农村颓败和没落过程中对传统思想文化的想象。这种想象,在《极花》中也是以隐喻和象征的方式出现。比如,极花——象征传统民间道德,这个原本的虫子,经过冬天的蛰伏,也可以蜕变成花。极花或许是贾平凹对传统和民间道德在现代社会的想象,它在具有巫史身份的老老爷身上得到集中表现,并得到主人公胡蝶的认可,在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中,极花虽然很难找到,但谁又能否认传统在现代化的转化中不需要经历阵痛?
①[秘鲁]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给青年小说家的信》[M],赵德明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18页。
②③韩鲁华,贾平凹《虚实相生绘水墨极花就此破天荒——〈极花〉访谈》[J],《当代作家评论》,2016年第3期。
④杨友楠《二元结构的设置与个人立场的悬搁——对贾平凹长篇小说〈极花〉的一种解读》[J],《文艺评论》,2016年第11期。
⑤⑦⑧⑨⑫⑮贾平凹《极花》[J],《人民文学》,2016 年第1期。
⑥程华《语言本体论的写作探索:贾平凹〈老生〉中的反抒情话语与方言写作》[J],《文艺评论》,2017年第8期。
⑩李泽厚《由巫到礼 释礼归仁》[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8-33页。
⑪梅兰《〈极花〉:巫史传统下的和解与暴力》[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
⑬贾平凹,舒晋瑜《写胡蝶,也是写我自己的恐惧和无奈》[N],《中华读书报》,2016年 3月3日。
⑭张汝伦《狂者的世界》[N],《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 4月20日。
⑯贾平凹《〈极花〉后记》[J],《人民文学》,2016年第 1期。
陕西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基金项目“贾平凹与中国文学传统研究”(17JZ028)]
商洛学院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