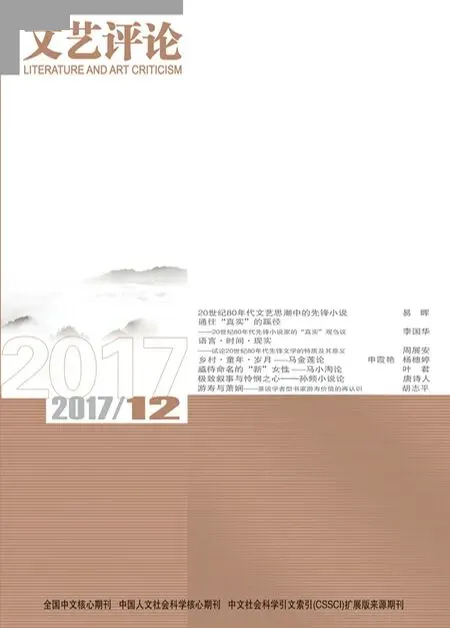语言·时间·现实
——试论20世纪80年代先锋文学的特质及其意义
2017-09-28周展安
○周展安
语言·时间·现实
——试论20世纪80年代先锋文学的特质及其意义
○周展安
一
关于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文学,无论是评论性的赏析、历史性的研究还是理论性的阐发,都已经足够充分了。在阅读围绕先锋文学所积累的研究文献的过程中,我常常产生词穷之感。在这里试图就先锋文学展开思考,说到底并无什么新意,只能算是对自己阅读先锋文学作品所得感受的一个整理。
先锋文学是本文的研究对象,其所指涉的主要是马原、格非、孙甘露、余华、洪峰等人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所创作的作品。将这些作家的作品命名为“先锋文学”,这已经是研究界的一个共识,然而历史地来看,这个概念颇多含混。概括地说,这其实是一代代的评论家在评论中不断回溯强化的结果,近似于史学领域古史辨派所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逻辑。当然,这并不是完全否定“先锋文学”或者“先锋小说”等提法在20世纪80年代的存在,但是我们也的确应该看到,除了“先锋文学”的概念,“新小说”“新实验小说”“新潮小说”“探索小说”等等提法也被使用,甚至是更广泛地使用。①这一现象提示我们,“先锋文学”并不是一个在源头上就确定下来的概念,因此,它很难成为对于其所指涉的特定文学作品加以研究的有效起点。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看到不少先锋文学的研究者对于“先锋”这个概念在中外的文化语境中做追根溯源的剖析,或者围绕“先锋”概念大量征引特别是西方学界的理论著作,并借此建立起一个标准的规范化的“先锋”,然后把20世纪80年代的特定作品放在这个标准的“先锋”之上来加以衡量。诚然,这种思路能丰富我们对于“先锋”以及“先锋文学”的认识,但“新实验”“新潮”“探索”等提法的同时存在,提醒我们,避开以概念、理论为起点的研究方法,从具体的作品分析入手,从作品的内部出发,或许是一种更有力的把握方式。
另一方面,和上述将概念化的“先锋”作为研究起点的方法相关,不少研究是在一种比较宽泛的意义上来理解先锋的,即将“先锋”理解为“先锋性”、先锋意识或者先锋精神,内容大概是指“一种探索精神,就是不停息的自我突破,敢于否定自己、超越自己的创新意识”②。循着这样的解释维度,我们会理解何以有的研究者将20世纪80年代先锋文学的发端追溯到“文革中的地下写作时期”③,有的研究者又会把刘震云、贾平凹、莫言在20世纪90年代和新世纪所创作的部分作品划为先锋文学,而阎连科则被评价为这个时代最具有先锋精神的作家。④的确,马原、格非、孙甘露、余华等人的作品具有如此这般的先锋性,但这样来定义“先锋”,也会产生一种泛化的可能,从而削弱上述作家在特定历史阶段的创作特点。因为,在几乎任何一段文学史中,都可以发现或者归纳出具有探索、超越、突破、否定意识的作品。就如有研究者所概括的,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都可以用“常态和先锋”这个对子来分析,“20世纪有许多或大或小的文学运动,可归纳为先锋运动,它们构成了整个20世纪文学发展的一种特殊力量”⑤。这就要求我们,从先锋、探索、超越、否定这些概括性的词语继续向下沉,沉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那些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的内部,由内而外去剖析其特点,而不是用某些描述性的词汇或者现成的理论概念加以固化。
本文倾向于认为,格非、孙甘露、余华等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创作固然和文学史之前的发展有各种隐秘的连续性的关系,比如格非所总结的和汪曾祺小说以及朦胧派诗歌的关系,⑥但是,这些人的创作更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断裂性,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历史上,是一次堪称把“文学”在本体的意义上加以锤炼的极致性试验。它们区别于新时期的反思文学乃至寻根文学的发展脉络,也区别于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发展特点。本文将尝试从语言、时间观、现实观三个角度来分析这一批作家的创作特点,并用“不及物”来概括其独特性;进而基于这种“不及物”来分析这些作品的创造性及其在当下的意义。
二
“难读”,这是先锋小说作品常常遭受到的诟病。先锋小说作品中不乏有对国外的小说家如博尔赫斯、罗布·格里耶等加以模仿的学步之作,这种意义上的“难读”是作家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尚没有找到自己得心应手的创作技巧所造成的,不必深论。但是,除此之外,先锋小说的“难读”也体现了一种值得认真对待的异质性。读者们不必因为自己的阅读和理解习惯而快速把这种异质性冠以“难读”之名而草草打发,而应该将自己的阅读和理解习惯与先锋小说所呈现的意义结构方式置于同一平面上进行对话。本文认为,先锋小说的这种异质性主要表现为一种强烈的“不及物”性,我们可以从语言的不及物性、时间的不及物性、现实的不及物性三个层面来加以理解。
所谓语言的不及物性,概括地说,就是先锋小说的语言主要不是去指涉一个语言之外的事物,不是去指涉一个外部世界,不是去服务于一个相比于语言显得“更高级”的内容或者思想,而是将语言呈现为语言自身,语言在自身中自我满足。这样的语言不仅仅是具有一种形式上的新鲜感或者陌生感,而且更进一步,语言自身构成一个硬核。在一个极端的意义上,这种语言具有强烈的不透明性,它不允许语言之外既定的某个内容或者思想来加以穿透,语言就是内容,语言就是思想。⑦
一般来说,作家们所使用的语言总是有别于我们的日常语言,而且作家和作家之间在语言的使用上也各有区别,由此形成所谓风格。在20世纪80年代的当代作家中,王蒙、韩少功、贾平凹、莫言等等的语言都有相当鲜明的独特风格。寻找自己的语言风格,这是20世纪80年代作家的一个普遍追求。王蒙的围绕一个意思从多个角度来加以铺陈而造成的汪洋恣肆乃至叠床架屋的风格、韩少功将规范乃至精致的叙述语言与充满地方特色的人物对话进行嫁接而造成的反差与新奇之感、贾平凹的平淡中略带古朴的风格、莫言的泥沙俱下滔滔不绝的风格、张承志的沉思中张扬着抒情的风格等等,都显示出这一点。然而,本文倾向于认为,这些作家语言总可以在一个通常的意义上来理解,即这些语言虽然各具特色,但总体上说属于形式层面的问题,它们还没有放弃或者说没有摆脱去指涉一个外部对象的自我定位,它们是及物的语言。而先锋小说的语言在典范的意义上可以说在努力摆脱其臣服于内容的从属性的定位,把形式层面的语言从内部凸显为内容。这样的表达,自然是在一种强调的或者说理念的层面上展开的。这并不是说先锋小说的语言已经全都是不及物的,而其他作家的语言都绝对是及物的。在一个普遍的意义上,所有的文学语言都试图在传递某个明确的意思之外保留属于语言自身的某种剩余物,即都具有某种不透明性乃至不及物性,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历史中,特别是自寻根文学以降的文学潮流中,追求语言的不透明性是普遍的现象。王蒙的《来劲》便是其中特别突出的一个作品。⑧同时,先锋小说作家也不是每个人都充分体现了语言的不及物性这一特点。但是,就一种文学史现象来观察,也许不能不承认不是别的而就是在先锋小说当中,将语言和外部世界的通道斩断的努力最为醒目。
格非曾坦承《褐色鸟群》“就是文字游戏,就是做一个实验——能不能把我心目中的那样一种文体表达出来,可以做一个极端的游戏——没有任何其他的考虑。这些都贯穿了先锋小说写作的始终”⑨。本文认为,这种所谓的文字游戏,就是语言的不及物性,是语言的自我指涉和自我消解。以《褐色鸟群》为例,这可谓是一个“用语言来讲述语言”的典型作品,一般所谓的“故事”在这种讲述中呈现为空心状态。褐色鸟群的故事层次可以概括为:这本身是一个故事a,故事a的内容就是作者准备写一个故事b,在写这个故事b的过程中,一个女人不期而至,作者开始对这个女人讲述一个故事c,在故事c中,有一个陌生女人和作者存在某种关系,但这种关系最后被显示为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当我们把小说的语言当成是形式,而试图穿过形式去寻找小说的内容/故事的时候,我们最终是一无所获的。因为小说并不是在内容/故事的意义上成立的,而就是作为层层包裹的语言而存在的,所以,语言/叙述自身就构成了小说。语言不及物,语言并不是依靠在故事上而存在,语言在维度上并不指向某个故事或者思想,而是把自身彰显出来,这不仅表现在上述整篇小说的结构上,也表现在小说内部一种可以概括为“语言的溢出”的现象上。在先锋小说中,我们常常遇到很多段落很多句子并不是要去引出或者烘托下一个情节,而是自成一体,这种现象即“语言的溢出”,也就是语言从它所指涉的对象那里的溢出。在这方面最典型的先锋作家是孙甘露。如果说在格非、余华等作家那里,语言的不及物指的更多的是语言和外部世界的断裂,是语言相对于外部世界的溢出,而小说自身即语言和语言之间尚有脉络可寻,那么在孙甘露这里,语言的不及物则扩展到上下文或者说语言和语言之间关系的断裂。《信使之函》从几十个角度对于“信”的解释和定义可以说是关于“信的哲学”的汇编,但是这几十个定义之间并无清晰的故事脉络。在孙甘露这里,每个段落乃至每个句子,也即每一处语言,都从叙事的链条上挣脱下来,将自身呈现为饱满的沉甸甸的状态。每个句子都占据着属于自己的位置,都具有自己的份量。
三
时间的不及物性是先锋小说的第二个特点。所谓时间的不及物性,主要表现为时间并非朝向某个目的纵向推进,它并非是一条直线,乃至并非一条曲线,而毋宁说是时间的错综、颠倒、循环,甚至是一种非连续性的并置或者时间的空心化。时间被取消了所谓目的或者说终点,不管这终点是积极的抑或消极的。当这时间的终点不复存在,则时间本身也处在一种崩解的状态中,每个瞬间都从原来平滑的链条上坠落下来,处在一种互不联系的无规则的并置或者冲突当中。
这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进行分析。第一个是显而易见的记时的层面。在大部分传统小说当中,时间是构成人物活动的最基本线索,乃至有所谓成长小说的命名。在这些小说中,时间是纵向延展的,人物都附着在这条时间的链条上,其命运因为时间的延伸而不断变动。时间也构成小说故事的基本容器,在现实主义小说中,小说时间和历史时间或者完全重叠或者遥相呼应,历史时间成为叙事时间的基本参照,也是读者用来判断故事真实性或者现实性的准绳。时间,构成传统小说叙事动力最无可置疑的前提,即便小说中的人物没有任何行动,小说依然可以依赖着时间的推移而产生叙事的逻辑,所有人物都在时间中存在,这一点在20世纪中国文学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当代文学中表现得尤其突出。但是,在先锋小说中,时间被置于一种可有可无的境地。历史地来看,这当然是一种有意识地对于此前那种时间模式的抵抗,是叙事时间对于历史时间的抵抗。
余华的《世事如烟》是一个没有任何时间标记的作品,如果不是有“司机”这样的名词提示我们这应该是一个现代故事,那么即便说它发生在古代也并非武断。洪峰在小说中直接声明:在我所有糟糕和不糟糕的故事里边,时间地点人物等等因素充其量是出于讲述的需要。⑩有的小说即使有时间标记,但是时间也是处于一种颠倒交错无可把握的状态。《褐色鸟群》在一开始就为小说中时间的颠倒交错埋下伏笔,叙事者以自己的“记忆”和“时间”对抗:“我想如果不是我的记忆出现了梗阻,那一定是时间出了毛病。”唯一能够供叙事者来猜测时序的是褐色候鸟的迁徙。但是在整个叙事中,候鸟的迁徙又根本没有参与到叙事活动中。可以成为叙事参照的是1987年、1992年这几个时间标记,1987年被记录为一个“很久以前”的时间点,1992年则是“我和那个穿栗树色靴子女人的重逢是一次意外的巧合”的日子。总之,小说中场景都发生在回忆当中。但我们知道,这篇小说完成于1987年,如果以此为基点,则对于1992年的描写不是回忆而根本是幻想。在这里,过去、现在、未来被交错在一起,也就打破了过去——现在——未来的计时顺序,“现在”不能成为我们判断的起点,“未来”也不再能够扮演过去或者现在的终点或者目的,时间本身处在一种四处弹射的状态。时间,这在传统小说中构成人物活动框架的东西,在此翻转成了记忆亦可说幻想——因为记忆和幻想的明确区分也正是依赖于连续性的时间——自由驱遣的对象。
时间的不及物性除了那种明确的时间标记的颠倒、错综和空置之外,更重要的是时间——时序逻辑本身的破坏状态,是和明确的时间标记相呼应的先后时序、线性逻辑以及目的论的取消。而当我们意识到传统的叙事往往是依赖于时间,因此时间的不及物性也自然就带来叙事的不及物性,即每个叙事都指向自身,而非用来推进下一个叙事。时间的不及物性带来了每个瞬间的独立,也就带来了每个片段性叙事的独立。把握故事的“高潮”或者“主题”是我们解读传统小说的一般路径。高潮和主题的存在意味着叙事将被编织成一个纵向推进的逻辑。但是,在先锋小说中,不仅明确的时间标记无可把握,就是这个纵向的逻辑也被尽量压制乃至消失不见。于是,先锋小说中的每个片段时间的意义不在于它们通向某个目的,不在于它们可以连缀成一条清晰可辨的线索,而在于每个瞬间本身。传统小说的主题设置可以说是以叙事的目的论吞噬所有的片段情节,所有的瞬间以自我否定的方式参与到线性的目的论逻辑之中。但在先锋小说中,这些片段的情节及其所依托的瞬间都被解放出来,随处绽放而成为丰富的、有深度的存在。
《迷舟》并非是极端的先锋之作,但它的叙事逻辑已经很能透露上述线性逻辑的松动。《迷舟》的故事线索相对清晰,但是,小说对于主人公萧的心理描写以及投射出心理活动的景色描写之频繁之生动,使得这些描写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独立于作为故事线索的萧的人生经历,而给整篇小说加上了一种立体的效果,萧也成为一个有情感深度的人物,这和他的军人身份构成强烈的反差。在一般的描写中,作为一个处在战事中的军人,萧的形象应该是围绕战争而显示出来的。但在格非的笔下,萧几乎有着诗人的灵魂:“已是黄昏时分,他独自一个人骑马从北坡登上了棋山的一个不高的山头。连日梅雨的间隙出现了灿烂的阳光,浓重的暮色将涟水对岸模糊的村舍染得橙红,谷底狭长的甬道中开满了野花。四野空旷而宁静。他回忆起往事和炮火下的废墟,涌起了一股强烈的写诗的欲望。”⑪故事,这原本是传统小说营构的核心,但在先锋作家的笔下,故事被从线性的逻辑上不断拉扯出去、拆散开来,最终弥散在孙甘露所说的“故事的次要方面”⑫,也就是拯救了那些向来被目的论压抑和吸纳的瞬间,这些瞬间不再只是通向目的的媒介,而是叙事中不可化约的组成部分。由此,我们能理解何以一把钥匙在手里握着的感觉也能被余华铺陈到一百多字,由钥匙而体会到冷漠的金属感觉,联想到温暖的嘴唇和凹凸艰难的路。⑬
这种不及物的、将瞬间释放为永恒的时间观颇类似于现代作家废名从佛学中所把握到的印象。在以反对进化逻辑为宗旨的《阿赖耶识论》中,废名说:“世界本是示现,不是生化。”⑭这即是说,世界并不是如进化论所解释的那样是一个线性的逻辑,不是逐步生长的结果,更不是要牺牲前面去成全后面成全目的,而是一个顿显,是一下子打开显现的结果。由此,废名说自己的诗是“天然的,是偶然的,是整个的不是零星的,故又较卞之琳林庚冯至的任何诗为完全”⑮,其原因正在于废名用“示现”的方式来看待世界,从而也是看待世界在诗中的存在方式,因为是“示现”,所以诗乃是完全的,是整个的,是当下的。废名是通过对于佛教唯识宗的分析,特别是对唯识宗的第八识阿赖耶识的分析达到这样的认识的。当代评论家多用主观化之类的描述性概念来理解先锋小说中的时间观,但对照废名的论述,正可以发现20世纪80年代先锋小说的时间观有相当开阔的可供分析的理论空间,虽然先锋小说家在写作时未必对此有自觉的认识。
四
先锋小说的异质性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表现,就是“现实”之边界的模糊乃至取消,本文把这种现象概括为“现实的不及物性”。所谓现实的不及物性,指的是在先锋小说家的笔下,叙事并不试图将自己成立的理由维系于一个客观的对应物,不诉诸一种公认的现实性,文学内部的“现实”和它本来所趋向的对应物,即和一般所认为的现实之间的联系中断了。在传统的文学观念中,不管作家的用笔如何肆意,作品总是要引导读者去认识一个具有现实性抑或说是真实性的对象,即作品总要营造出一种现实性,要说服读者,让读者去相信作品所描写的是真实有力的东西。即便是在神怪小说中,也要去营造一种合乎逻辑的链条,从而使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文学所描写的世界是具有真实有效的逻辑的,尽管小说本身是虚构,但是小说所试图传递出来的却绝不是虚构,而是一种真实、一种具有现实性的逻辑,这是传统小说所孜孜以求的。但是,在先锋小说这里,文学内部的这种“现实”已经不再追求自己的现实性,不仅如此,它还公然宣布自己就是虚构,就是梦幻。中断文学内部的现实和客观现实之间的对应关系,抹掉文学内部的现实的“现实性”、它的现实支撑,即抹掉它的及物性,这就是所谓“现实的不及物性”,我们可以尝试从文学的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来进行更详细的分析。
首先从文学的外部来看。所谓外部,即是作家。在传统小说的写作中,作家总要尽量拉开自己和作品的距离,尽量隐藏自己,从而使得自己的写作/虚构行为获得一个趋近真实的效果。先锋小说则反其道而行之,它对自己的虚构行为毫不隐瞒,其方式就是作家本人不断在小说中现身,从而破坏了传统小说小心翼翼维护的“现实”边界,也就破除了“虚构”和“真实”的对立。这直接带来了两个后果,一是“虚构”成为了公开的从而也是有力量的介质,“虚构”不必隐藏自己,从而也就不必再害怕被指责其所营造的对象不具有“现实性”抑或“真实性”,它从防守的、隐匿的状态一转而以积极的态势进入到作品当中;另一方面,原来被努力维护的“现实感”因为“虚构”的自我宣告而趋于瓦解,它原来相对于“虚构”而呈现出来的“现实”自明性变得模糊。但是,两方面合起来观察,“虚构”对于作品的强力介入最终并不是完全取消了“现实”,而是改变了“现实”的内容,扩大了“现实”的范围。或者说,当“虚构”勇敢宣告自己的“虚假”身份,这反而使得“虚构”本身获得了现实性的力度,获得了真实感,并直接导致原来由“虚构”所维系的有限的“现实”也因为暴露出自己的边界而获得了一个自我清算的机会,即不必再“冒充”真实,而是本身就成为了动态性现实的一部分,它和现实的关系从间接变成直接。
马原如果只是写出了主人公在西藏玛曲村的见闻,则《虚构》只是一篇写出某种奇闻的传奇小说而已,它只会引导读者拿着小说中的西藏景象和现实中的西藏景象加以对照,从而得出马原作为一个作家写西藏写得是否“真实”这样的结论而已。但是,马原的创造性在于他不仅把西藏写进了小说,而且把“马原写西藏”也写进了小说,因此,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就不只是西藏,而是,或者说更是“马原在写西藏”这件事情,极端地说,书写的对象是不是西藏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马原在写”这个行动。马原在写、格非在写、洪峰在写、孙甘露在写,先锋作家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把自己的写作行为变成了自己的写作对象,这就是说,通过自己对于“作品”强力的介入,攻陷了、弥合了自己的写作和写作对象之间的距离,也就是弥合了作者和世界之间的关系,弥合了作者和现实/真实之间的关系。作家已经不是要通过一个外在于自己的东西来曲折地映照现实/真实,而是自己要纵身一跃直接进入现实/真实之中。
“现实”边界的模糊、“现实的不及物性”也表现在作品内部,这就是先锋小说中随处可见的回忆、幻想、梦境等等的描写。以回忆、幻想、梦境来引出小说的内容,这并不鲜见,这甚至是古典小说尤其是民间文学的主要呈现形式。但是,古典小说中的梦境和幻想只是小说内容的外壳而已,其内部包裹的还是“现实”,梦境只是为了更突出“现实”而采取的修辞手法。但是,在先锋小说这里,梦幻就是梦幻,它不隐藏自己,不伪装成现实。不仅如此,它还不断对我们通常以为的“现实”进行攻击,在小说内部不断破坏“现实”的边界,同时也是在不断扩充既定“现实”的内容。当“后”既可以是《请女人猜谜》中的人物的名字,也可以是《请女人猜谜》这篇小说所提及的《眺望时间消失》这篇小说中的人物的名字的时候,对于孙甘露来说,梦幻和“现实”已经没有任何区别了。我们在这里反复提及梦幻,关键并不只是说先锋作家在小说中加入了梦幻的元素,也不只是说作家在想象力的层面上使用梦幻以补充自身现实经验的不足,而是说作家完全取消了“现实”和梦幻的区别,而在这种取消的努力中,正凸显了作家自身强烈的主体姿态,因为说到底,幻梦只能是属于作家本人的创造。
五
语言的不及物性使得语言摆脱了作为“内容”之“形式”的臣仆地位,使语言本身成为不透明的硬核;时间的不及物性使得时间摆脱了“目的论”的操控,使每个片段时间同时也是使每个片段叙事都获得了自身的位置与分量;现实的不及物性使得文学内部的“现实”摆脱了外在客观现实的压制,使文学意义上的现实得以有力地介入到外在既定现实的脉络中,松动乃至改变其结构。合而观之,则可以说,正是先锋文学的不及物性使得先锋文学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学”,或者说本体意义上的文学。
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这种本体意义上的文学并非是自外于现实,并非没有“现实性”,相反,正是因为文学凸显了自己的本体意义,所以才更具有“现实性”。格非曾多次强调先锋小说有自己的政治和经济维度,⑯我们在其他的先锋作家比如洪峰的小说中,也能看到作家对于以往政治口号的解构。⑰但是,以上的分析显示,先锋小说的现实性并非仅仅停留在这个意义上,而是更进一步,它不再是满足于去“反映”或者“表现”外部“现实”,而是要创造现实。我们习惯于说文学要表现现实,仿佛文学并不在现实内部一样,仿佛作家都不是在现实中生活一样。而当我们说文学要表现现实的时候,又不自觉地把文学当成透明物,当成现实得以呈现出来的媒介,当成安放现实的容器。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正是这样来理解文学的。由此我们推衍出了文学与政治、形式与内容等种种二元对立模式。先锋文学的异质性则提示了一个新的思路,那就是文学的意义不在于或者不仅仅在于作为媒介等待某种更高级的“内容”“思想”的穿透,它的意义的有无也不在于它是否反映或者抵达了既定的“现实”,而是它通过自身的异质性,以无中介的方式加入既定现实当中,从而从内部去改变既定现实的编码序列。在这个意义上,先锋文学就不再是杰姆逊所说的一种“社会性象征行为”⑱,而是一次实实在在的改变既定社会序列的行动。就其改变的潜能来说,先锋文学是文学,但同时也必然是政治的。我们认为,这是当下的中国文学应该从先锋文学那里认真学习的地方。⑲
①吴亮、程德培编选《新小说在1985》收录了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等作品;程德培、吴亮评述《探索小说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也收录了马原、残雪、刘索拉等人的作品;程永新曾编辑《中国新潮小说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收录马原、格非、孙甘露、余华、洪峰等人的作品;盛子潮曾编辑《新实验小说选》(浙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收录洪峰、格非、余华、孙甘露、北村等人的作品。评论家也更倾向使用“探索”“新潮”等朴素的提法,如钱谷融《论探索小说——中国新时期文学的一个侧面》[J],《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第 2~3期。
②陈晓明《先锋的隐匿、转化与更新》[J],《中国文学批评》,2016年第2期。
③张清华《谁是先锋,今天我们如何纪念》[J],《文艺争鸣》,2015年第10期。
④陈晓明《先锋派的历史、常态化与当下的可能性》[J],《文艺争鸣》,2015年第10期。陈晓明《先锋的隐匿、转化与更新》[J],《中国文学批评》,2016年第2期。
⑤陈思和《先锋与常态——现代文学史的两种基本形态》[J],《文艺争鸣》,2007年第 3期。进一步的分析,也参陈思和《有关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J],《文学评论》,2016年第 6期。
⑥格非对汪曾祺极为推崇,认为汪曾祺是“先锋文学一个真正的源头”,是20世纪政治文学的大脉络中“真正出现的大逆转”。格非《文学史研究视野中的先锋小说》[J],《南方文坛》,2007年第 1期。
⑦陈思和曾指出五四的欧化语言代表了一种新颖的思维方式,这一强调非常重要。陈思和《先锋与常态——现代文学史的两种基本形态》[J],《文艺争鸣》,2007年第3期。
⑧可参考孟悦《文人体验中的中国生存》[A],收入《历史与叙述》[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特别是86~89页。
⑨格非《文学史研究视野中的先锋小说》[J],《南方文坛》,2007年第1期。
⑩洪峰《极地之侧》,收入程永新编《中国新潮小说选》[C],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322页。
⑪格非《迷舟》[A],收入程永新编《中国新潮小说选》[C],第74页。
⑫孙甘露《请女人猜谜》[A],收入盛子潮选评《新实验小说选》[C],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87页。
⑬余华《四月三日事件》[A],收入程永新编《中国新潮小说选》[C],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224页。
⑭废名《阿赖耶识论》[A],王风编《废名集》[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07页。
⑮废名《谈新诗》[A],王风编《废名集》[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22页。
⑯王中忱、格非《“小说家”或“小说作者”》[J],《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5期。
⑰可以参见洪峰《极地之侧》[A],收入程永新编《中国新潮小说选》[C],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⑱Fredric Jameson,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2.
⑲本文集中从正面分析先锋文学的特质与能够创造新现实的意义,限于篇幅,对于先锋文学创造性的限度、先锋文学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的位置、先锋文学和20世纪80年代文化精神之关系的分析将另行撰文。
上海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