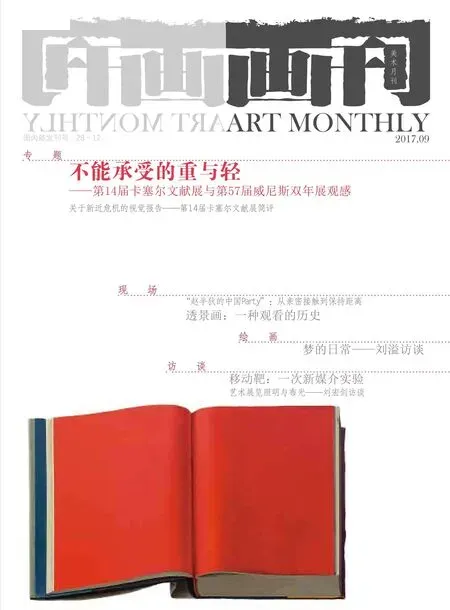梦的日常
——刘溢访谈
2017-09-25本刊
本 刊
梦的日常
——刘溢访谈
本 刊

《晦在牧羊女》 刘溢 布面油画 135cm×70cm 2010年
《画刊》:之前看你的作品,都是网上见的图,觉得画面色彩有些俗气。今天在你工作室看到原作,我发现差别挺大。这再一次证明,通过复制的二手图像来判断一个画家的能力,经常不靠谱。印刷品和现在电子屏幕给的信息,都有“失真”。但通常来说,好画在转换的过程中都是“减分”。我看维米尔、提香、安格尔的印刷品,当然觉得好。但真在美术馆见到原作,才发现那些真正的好以前压根没看见过。相反,一些之前看图觉得不错的画家,看原作反倒是差强人意。
刘溢:油画我们简单地分这么两类:一个是多层画法或者是透明画法,一个是一次性画法。一次性画法比较适合印刷,因为它是比较实实在在的颜色;而多层画法,有些像我们买的玻璃糖纸包的糖,你能看到玻璃纸上的图案,又能看到那块糖,这种现象在印刷品上不易显示。
多层画法讲求衔接,不太容易表现厚重的笔触,印刷品上也容易表现出光溜溜、滑腻腻的效果,显得俗气。尼德兰画家勃鲁盖尔(Pieter Bruegel)、博西(Hieronymus Bosch),特别是凡·艾克(Jan van Eyck)的画,看印刷品都不免俗。只有站在原作面前,画面的厚重感才显现出来,一层一层叠加出的微妙感,让你立马肃然起敬。
收藏界有个词叫“一眼假”,说的也是上手看包浆。再比如自己的儿女,光看照片,特别是PS之后的照片,真不敢肯定那是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女,一旦站在眼前,没有一眼看不出的,除非你不是亲爹。
或许将来的信息社会,会有更高级的印刷术。比如在印刷过程中,包括这么三遍过程:一遍是画家的原稿,一遍是画家最后完成的效果,最后一遍压模加上光亮透明的效果,类似油画的上光油。谁知道呢? 现在的印刷品,能印刷出一些包浆效果就算不错了。
《画刊》:中国人画油画,尤其是画古典技法的油画,经常给人感觉画得不地道。但我觉得这个地道不地道的事儿,又不仅仅是技术问题。你多年来一直钻研古典油画语言,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刘溢:这个问题我想有两个原因:一是自发的表现意识,而不是追求别人的经验。二是对油画材料所能鼓捣出的油画效果的痴迷。说到底,这两者是一回事,学别人还是表现自己。如果是学别人,你永远也学不地道,或者表现不出别人已然精彩表现过的。你永远不知道别人酒醉、做梦时的心理状态,你永远介入不到别人潮湿、黏稠的调色程序中。
《画刊》:你很早就进入西方画廊的系统,从一个画家的角度来说,你怎么理解艺术家和画廊之间的关系?
刘溢:实际上每一次美术史的辉煌都是跟当时社会科学进步、经济发达有关。一般说来,社会有了闲钱,大款们喜欢收集自己喜欢的,这个时候绘画就活跃许多,就有更多的绘画意识、表达手段以及材料质感的进步。中国传统的美术教育,包括美术史的教育,比较是无产阶级的灌输方式,比较是让穷孩子脱贫致富,学画商品画的教条实施。西方美术史就是西方资产阶级的美术史,文艺复兴是因为有了几大家族才养活了像达·芬奇、米开朗基罗这样的艺术家,才滋生了某些个人否定传统、表现自身的欲望,才促使和赢得别人、后人的认可。尼德兰的码头,搬运金银货物的同时,也搬来了色彩原料,搬走了肖像订件作品。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中,才能产生心灵的细腻交流,促进表达语言和表达手段的进步。

《草莓熟了》 刘溢 布面油画 130.5cm×120cm 2009年

《中国女仆》 刘溢 布面油画 120cm×150cm 2009年
我们教的是什么?恨不得一套方法、一个口号、一伙子人,一个晚上就创造出两个文艺复兴、三个印象派,土匪进城的感觉。什么跳广场舞、新年晚会,别管什么想法,只要大家抱团造势,只要大家尝到甜头别松口,就一定是正确的、值钱的和伟大的。
我出国的时候,中国还没有一家画廊。到了加拿大,看了他们的画廊,这才意识到卖画的问题。要不要给人画肖像?要不要将色彩画得更鲜艳些?要不要跟风走俏?要不要卖手艺?要不要连人带画一起打包卖?
我觉得,最好是连人带画一起卖,所谓“身在曹营心在汉”。我刚刚从中国的教育体系里爬出来,没必要再掉进老外的“万人坑”。我就塑造了一个老头,用了一个犹太人的名字,中文我就叫他胡大爷。我天天画胡大爷卖,画大爷塑像旅游品、胡大爷遛狗;狗长得也像是胡大爷,瞎胡大爷背着瘸胡大爷行走,瘸胡大爷给瞎胡大爷指路;等等。

《烽火诸侯》局部 刘溢 布面油画 120cm×180cm 2011年
《画刊》:在艺术的表达方式变得无比丰富的今天,你觉得写实绘画的价值是什么?
刘溢:当年我还在国内,第一次看到安格尔肖像画时,那真是亮瞎了我的双眼、人生没戏的感觉,甚至是国家和民族没戏的感觉,当然,我说的是油画的欧洲画法的没戏。每一个成功的艺术家,都是在他嗜好的语言或材料上做绝了的。这就如同在李白之后,咱就没必要还写什么五绝七律,至少没必要还写潇洒豪放的五绝七律了。不是咱潇洒不过李白,是咱的潇洒不像李白的潇洒。过了没几天我又活了下来,安格尔好,是因为安格尔把安格尔最好的东西拿出来了;自己不好,是因为自己没有把自己最好的东西拿出来。好在前者是完成时,后者是进行时。赶紧抓住自己喜欢的,在喜欢的心境里将它做成大家喜欢的。至于写实绘画的价值,绘画的价值乃至艺术的价值,说得再大也不过如此。
《画刊》:你常说你自己不是一个在表现手段上有多少个性的画家,更多的是文化上的反思。作何理解?
刘溢:印象派之前的画家,多画宗教的、叙事的、人文的和文学性的东西;印象派之后的画家,多画风格的、个性的、语言的和材料尝试的东西。我个人比较喜欢前者。比如我们现在有新水墨画的现象,有人画得怪,有人画得“坏”,比如朱新建、李津、刘庆和等画家,我看他们就有很重的人文情怀。当然,任何人做任何事,都多少包含一种新的尝试,任何人的社会认知,都多少有些与众不同之处。这种东西囿于个人的生理,不好深刻地解说,不注意它,它反而会更加健康地表现出来。很多人也关心我的绘画手段,我也尽快地、无保留地告诉大家。但凡我是一个艺术家,我不喜欢将自己的表现手段神秘化、商品化、固化和僵化。如果相信明天能画出新的东西,最好的表现是坦白今天的自己。
另外,如果将对象画得真实细腻,就是所谓的写实绘画的话,真的就不会多表现特异,这对我来说是个很好的借口。我不多想自己的特定技术,那是昨天的事;我只管我的兴趣,那是明天的事。
《画刊》:《搓麻将的女人》这幅画可能是你最知名的作品了。这幅画被不停地阐释,但基本都是过度阐释。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我觉得是因为你的绘画本身负载了足够多的信息量,给了观众想象和发挥的空间。既然有这种信息量,你也一定有你的考虑。可不可以再谈谈这件作品?
刘溢:怎样解说是一回事,是否愿意解说是另一回事,我比较看重后者。假定同样是搓麻将的内容,我把它画成白描,解说的人就会大大减少,或者根本就没有人会注意到它。
写实绘画,哪怕只画风景或景物,都回避不掉内容。在内容的表现上,画家应该画出一些超常的、有绘画感的东西。绘画感对画家来说,无非是绘画的趣味性,如果做得好,或者赶得巧,别人会将其说成是思想深刻。这个时候,作品已经是别人的孩子了,画家没有监护权,最多有一点出版权。
如果我将搓麻将的画,改画成苏联人民挥起铁拳打倒美帝国主义,第一没人愿意解说,因为肤浅;第二随着苏联的解体,我也完蛋。表面上看,这样的绘画没有超越公共想象,也很难超越公共想象,至少我不可能通过这样的绘画成为一个优秀的社会公知。我只不过是图像思维、图像表现。只有这样的创作才是有机的,才能保鲜,才能感染别人。

上左·《网络女》 刘溢 布面油画 101cm×152cm 2006年

上右·《我下飞机抽根烟》 刘溢 布面油画 200cm×120cm 2013年

下·《2008北京》 刘溢 布面油画 182cm×121cm 2005年
我举两个例子:一、达·芬奇被许多人解读,可是直到今天,我还没有看到有谁说出达·芬奇的精彩之处,尤其是他用图像表达出他对科学的人文关怀。达·芬奇不是一个下定义的人,而是提供可能的人。图像的表现比文字的、符号的表现更能提供直接的、同时也是潜在的信息内涵,丰富的同时也不乏指向性的。因此达·芬奇也最是一位令人解说、令人琢磨不透的画家。二、我们现在的手机和电脑的界面,多是一个一个的图像标志,而非一组一组的文字名称,这有别于早期的家庭电脑,刚打开时蓝屏或者黑屏上都是一串一串的文字,那种界面让现在的孩子们看见,肯定觉得你是一个程序员,而且是一个不会画画的程序员。我觉得,会画画的程序员比不会画画的程序员更有魅力,也更有潜力。
很多画家喜欢说自己是在画自己的梦。现代临床表示,人的梦大多是图像的,而不是文字的;人们的梦有太多的共同性,估计得有50%的集体意识,还有25%的祖先意思。很少有人能梦见一个完全不同的怪物。我觉得,就算是能梦见,并能表达出一个彻头彻尾的怪物,恐怕也没有太多的交流意义。梦的共通性有很重要的意义,甚至是艺术的根本,也可以说是我创作的立足之本。所以我说,我画的不是自己的梦,我的日常工作是用白日梦的方式画大家的梦。
《画刊》:回国后你画了《钟馗嫁妹》《烽火诸侯》《闹洞房》和《苏武牧羊》等等,我感觉你这批作品从中国历史、民间神话、民俗生活里获取的灵感和养分更多,而你以往在加拿大的作品,似乎很少关注这些主题。
刘溢:你上面说的这几张画,虽然有个人的解说,确实存在文化背景的限制。去国多年,由于地理上的隔绝,中国历史文化里极其熟悉的内容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全新的、令我痴迷的对象。我想,是我特殊的环境经历和心理状态造就了这些画的产生。我以后只会更加个人化、更加真诚、更加不拘于题材,更加以现实生活的画面表达自己。

左·《春城女》 刘溢 布面油画 100cm×80cm 2013年

右·《钟馗嫁妹》 刘溢 布面油画 150cm×150cm 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