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闺里的等待者:从诗歌到图画
2017-09-22李晓愚
李晓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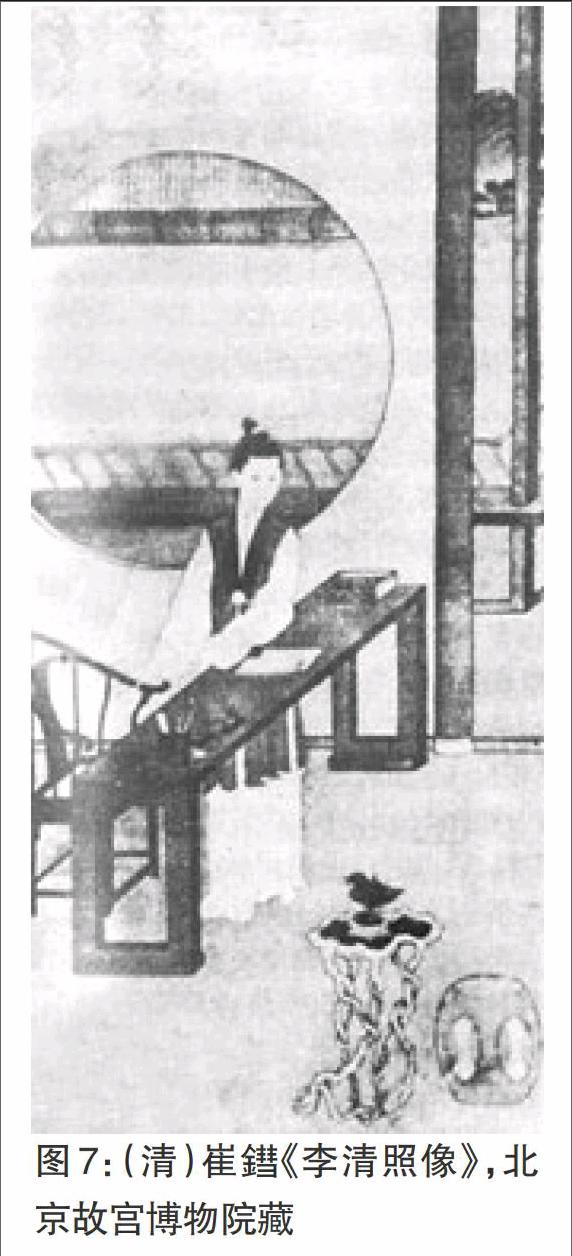
天津博物馆收藏的《春闺倦读图》是清代宫廷画师冷枚的代表作。画中的女子身着长裙,发髻高绾,一人在香闺中独处。这是一问陈设精美的屋子:木嵌大理石面方桌、瓷质鼓式坐墩、天然木香几。桌上放着盛有佛手柑的红釉盘和一套蓝色的书函;香几上陈列着插有月季花的瓷瓶以及“瓶炉三事”,即香炉、香盒和香瓶;墙壁上悬挂着一只缀着流苏的青色竹箫。女子斜倚书桌,一手持着书卷,另一只手托着香腮,还将一根手指轻触嘴角,脉脉含情地望向画面外的观看者。
当我最初注意到这幅画的时候,很想知道画中美人正在读的是什么书,通过对高清图片的局部放大,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书卷里的内容,甚至可以辨识出注释的小字:
子夜,子夜晋女子……有四时行乐……子夜歌:芳是香所为……冶容不敢当……
由于美女纤纤玉手的遮挡,我们能看到的文字并不连贯。但已经可以推断出她所读的是晋代一位名叫“子夜”的女子为远方情郎所写的“子夜歌”。诗歌抒发了对爱人的思慕和对情感的痴迷,也为我们提示了画作的主题:佳人正在苦苦等待缺席的爱人,承受“思春”的煎熬。
熟悉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人,或许会在观看《春闺倦读图》时自然地联想到南朝时的宫体诗。《玉台新咏》的翻译者白安妮女士(Anne BirreⅡ)这样概括宫体诗中的常见情境:
南朝宫体诗人在写作情诗时,通常是将女性作为描写对象,而很少以男性为主。这些女性又通常被赋予高贵的品质:出身华胄,居住华丽,体态娇羞,服饰光艳照人。但这只是外表的形象,诗人所着意描绘的主要是这些女性的孤寂的心境,使人感到一种深沉的抑郁浸润其中。在华丽服饰的背后,她们的感情明显地受到压抑,却甘心屈从于命运的摆布:孤守在华丽的闺房中,听任时光的流逝,只能在那里苦苦地等待着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的情人。诗人通过细节的描写,突出闺房中的某种摆设,并将女主人公肖像镶嵌其中,华贵的装饰和美丽的容颜相得益彰,但却为人所冷落,无情的时光成为这里的匆匆过客,女主人公只能在期待中备受煎熬。
如果我们将以上段落中的“诗人”替换成“画家”,就可以较为妥帖地用来描绘《春闺倦读图》了。华丽的深闺、精致的摆设、光艳的佳人、孤寂的等待、缺席的情人,这些南朝宫体诗里的常见元素均体现在这幅图画中。那么,画家是如何将这些元素转化为可视的形象呢?又有哪些不同于诗歌描述的创新和突破呢?
一、深闺
《玉台新咏》的编辑者徐陵将宫闱和深闺作为爱情诗吟咏的典型场所。在诗集的序言中,他写道:
夫凌云概日,由余之所未窥;千门万户,张衡之所曾赋。周王璧台之上,汉帝金屋之中,玉树以珊瑚作枝,珠帘以玳瑁为押。其中有丽人焉。
徐陵列举了历史上著名的宫殿,这些建筑“凌云概日”,十分壮观;“千门万户”,重重墙垣。而旷世佳人就居住在这些“深深深几许”的深闺之中。当男子放马天涯、逍遥红尘的时候,女人却如囚鸟般被困在华丽的牢笼里,在漫长的等待和相思中消磨完岁月,憔损尽容颜。
虽然“深闺里的等待者”这一女性形象在公元5世纪的南朝诗歌中就已普遍,但在绘画中却姗姗来迟,一直到清代初年才出现。高居翰(James Cahill)认为将佳人安置在华贵雍容的封闭空间中,并在她周围摆设各种精巧的物件,这种绘画类型的产生很可能是因为清代画家受到了北欧绘画,尤其是荷兰风俗画的启发。高居翰注意到清代“美人图”与17世纪荷兰绘画在主题乃至画面结构上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如果把荷兰画家杰拉尔德·都(Gerald Dou)的《梳妆台前的年轻女子》(图3)与冷枚的《簪花仕女图》(图4)并置而观,的确会发现许多共同点:女主人公都在侍女的协助下梳妆,她们都被绘制在低垂的帷幕之后,身旁都有打开的窗户,梳妆台上都摆着镜子等其他精致的物件。高居翰推测清代画家很可能是通过当时流传到中国的大量欧洲版画了解到荷兰室内风俗画的。他们并非简单地加以模仿,而是从中吸收了有趣的主题和良好的风格,将之运用到自己的创作中。
自晚明以来,西方传教士将西洋绘画的透视法、光影处理等技术带入中国,宫廷画师成功地把这些技巧与中国传统的绘画技法结合起来,在画面中创造出真实可信的空间。《春闺倦读图》就展现出引人注目的错觉效果:画家选取闺房内的墙壁以及其交角作为背景,借助色彩的深浅营造出立体纵深的室内效果。桌子、香几等家具的描绘基本符合透视原则。挂在墙壁上的洞箫立体感明显。连桌子下、坐墩里乃至女子裙子皱褶处的阴影都处理得很好。与传统中国绘画相比,《春闺倦读图》中的空间更具“可读性”,画中的物件更具“可感性”。
清代之前的仕女画要么把女子安置在室外,通常是花园中;要么干脆虚化女性所处的背景。清代的新型仕女图则不然,通过对西方绘画技法的借鉴,画家令人信服地把女子安置在了精美幽邃的闺房中。南朝爱情诗里的典型场景终于展现在绘画中。观画者的视线可以在香闺中漫游,把玩其中的每一件精美物品,欣赏其中娇媚柔顺的佳人。
二、陈设
高居翰注意到《春闺倦读图》中的种种陈设,特别是竹箫、佛手和月季花,认为它们都具有微妙的情色暗示。如箫象征着男性的生殖器,而佛手的形狀会让人联想到女性的生殖器。高居翰此论大胆而富有新意。的确,“吹箫”常常用作男女性事的隐语,在以《金瓶梅》为代表的明代情色小说中,描写“吹箫”的段落不胜枚举。还有盘里的佛手柑,这种散发着清香的水果在明清时常被用于室内装饰,起到空气清新剂的作用。比如《红楼梦》中探春居住的秋爽斋里“紫檀架上放着一个大观窑的大盘,盘内盛着数十个娇黄玲珑大佛手”。慈禧太后的宫中也从不焚香,而是用佛手等水果来“熏殿”。然而高居翰却注意到佛手常常出现在春宫画中,与男女之间“上下其手”的性挑逗行为联系在一起。
高居翰对这些陈设寓意的解读不无道理,但这并非唯一的解读。在南朝的宫体诗中,诗人就常常不吝笔墨地描绘女性深闺中的陈设。萧纲在《倡妇怨情十二韵》中以铺排延展的方法将镜头对准了女主人公闺阁中的物品:endprint
散诞披红帔,生情新约黄。斜灯入锦帐,微烟出玉床。六安双玳瑁,八幅两鸳鸯。犹是别时许,留致解心伤。
被爱人离弃的歌女困守在深闺之中,这里点点滴滴都是她熟悉的物件:斜灯、锦帐、玉床、六安枕等等。这些东西曾见证过她与他之间的缠绵悱恻,如今却和她一样被冷落、被遗忘。南朝诗人在描绘闺中陈设时,最常用的一个字是“徒”:
更恐从军别,空床徒自怜。(萧纲《和徐录事见内人作卧具》)
罗襦晓长襞,翠被夜徒薰。(庾丹,(币火闺有望》)
宝琴徒七弦,兰灯空百枝。(王僧孺《何生姬人有怨》?)
“徒”就是徒劳、无用。床、被、琴,这些亲密爱人曾经共享的物品,如今却再无用处,不过是怨妇回忆过往的凭借罢了。“徒”这个字也常用于描绘怨妇本身:
玉颜徒自见,常畏君情歇。(谢胱《镜台》)
徒交两行泪,俱浮妆上红。(刘缓《秋夜》)
妾心徒自苦,傍人会见嗤。(萧纲《妾薄命篇十韵》)
美丽的容颜、相思的泪水、幽怨的心绪,种种华美而哀伤的情感,就和那些精致而无用的陈设一样,暗示着对爱情的执迷与绝望。
在了解了南朝宫体诗中频繁出现的意象之后,再来观看《春闺倦读图》,或许可以对图中的陈设产生新的解读:当爱人远去,佳人为谁吹奏竹箫?又为谁焚香?盛放的花朵又有谁来欣赏?这些曾为闺阁增添情趣的物品,如今只能徒然陈列在那里。王融的《自君之出矣》云:
自君之出矣,金炉香不然(燃)。思君如明烛,中宵空自煎。
这首诗或许可以作为画作的注解。情感与香都是易燃之物,如今“香不燃”,而佳人的情感就像烛火一样,空白燃烧,在消耗尽自己之后终将灰飞烟灭。
《雍正十二美人图》的构图和主题与《春闺倦读图》很相似。《雍正十二美人图》是一架十二扇围屏上的十二幅仕女图。围屏原本陈设在圆明园的深柳读书堂中——那里是雍正当皇子时经常流连的地方。每幅画的皆以一位无名佳丽为中心,她身处锦绣香闺之中,孤独地等候着缺席的情人。画家将美人安置在充满女性气质的物质环境中。南朝宫体诗中频繁出现的屏风、锦帐、玉床、雕炉、铜镜、薰笼、团扇、斜灯、兰烛等意象也在《雍正十二美人图》中反复出现。这些华美的陈设映现出美人的优雅,更暗示着她们的忧伤。
三、佳丽
冷枚在《春闺倦读图》中以极其细致的笔墨描绘了深闺中的一位美人。她的穿戴十分华丽:头裹结发巾,发间插着碧玺金簪和点翠嵌珠宝花簪;身着月白色暗花连衣长裙,袖口饰有色彩鲜艳的“多蝠(福)纹”花边,并嵌着珍珠;腕上还戴着金光闪闪的双龙抢珠镯子。尤其特别的是她的耳饰——三只金耳环。一般汉族女子耳朵上只戴一只耳环,佩戴三只是满族妇女的习俗,即所谓的“一耳三钳”。在清朝众多皇后妃嫔的画像中都能看到这种独特的耳环佩戴方式。由此可知,画中的美人应该生活在满族贵胄之家。
珠宝、首饰、华服、化妆品,画家用這些精美之物打造出一个理想化的女性形象范式。这种以华丽的妆饰作为展现女性美丽和价值的手法,在南朝的诗歌中同样屡见不鲜。白安妮分析了南朝诗歌中女性形象的塑造,她引用了沈约《少年新婚为之咏诗》中描写新娘的十六句,指出其中只有一句交代了新娘的活动,两句描写其体态,而描绘其服饰和妆容的内容有九句之多。“显然,对于材料的取舍是不够平衡的,写个性的笔墨少,而写类型化的笔墨多,这在当时确有典型意义。人性价值低于物质价值。女性的价值是由华丽的装饰包裹起来的。至于她的个性却很难找到。”和南朝诗人一样,冷枚的兴趣似乎也是通过华美的外表装饰他的女主人公,至于是否真实,并不在意。此种情形不妨用一句英文谚语来概括:“Woman is adored when adorned.”(女人只有被装饰后,才会被爱慕。)
除了极力刻画华美的服饰之外,南朝诗人对于女性形象最为留意的是她的柔弱与谦恭。《玉台新咏》中的女子大多是一个模子:苍白的肤色、纤细的手指、轻盈的身躯。“惠”“闲”之类表现女性谦卑柔顺的形容词在诗集中出现了数百次。《春闺倦读图》中的主人公也符合这种标准化的理想女性形象。什么样的女子最令男人着迷呢?清代苏州文人卫泳在其著名的“美女鉴赏指南”——《悦容编》中说得很清楚:“态之中吾最爱睡与懒,情之中吾最爱幽与柔。”冷枚笔下的佳人带着慵懒与娇媚,显然是为了迎合男性观众的审美趣味。
四、等待
《春闺倦读图》中的美人手持书卷,却并不阅读。其实,中西方的绘画中都有表现女性阅读完毕或主动暂停的作品,比如法国画家夏尔丹的《私人生活的乐趣》,以及清代宫廷画家崔缮的《李清照像》。
但只要研究一下《春闺倦读图》中美人所持书卷里的内容就会发现,画家着意表现的主题并非“阅读”,而是“倦读”。如图2所示,书卷里的内容是“子夜歌”,传说这是一个名叫“子夜”的女子因为思念远方的情人而作的,表达了对爱情的痴迷和执着。画中美人之所以收起书卷,不是因为身体或精神上的疲惫,而是因为诗歌唤起了她对心上人的相思,而相思的煎熬又使得她难以将阅读继续下去。
表现女子因为相思而中断工作的图画在绘画史上颇为常见:有因为相思而厌倦针黹的(图6),有因为相思而停止采桑的(沈士鲠《采桑图》,天津博物馆藏),有因为相思而不再吹箫的(改琦《靓装倚石图》,广东省博物馆藏)。我们不妨把这类图像统称为“倦X图”。图中的女子“为伊消得人憔悴”,经常放弃所有的努力,甚至连起码的日常琐事都懒得去做。
这类图像的主题可以追溯到古老的诗歌传统中。《诗经·国风》中就出现了因为相思而百无聊赖的女性形象,如“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真彼周行”(《国风·卷耳》)(因思念无心劳作),“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卫风·伯兮》)(因思念无心梳洗)。
在《玉台新咏》中,“不成”这个词反复出现,用来强调女子在苦苦等候中倦怠生命,了无乐趣的情境。有因为相思而无心纺织的:endprint
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枚乘《杂诗九首》之一)
遐川阻昵爱,修渚旷清容。弄杼不成彩,耸辔惊前踪。(谢惠连《七月七日咏牛女》)
西北有织妇,绮缟何缤纷。明晨秉机杼,日昃不成文。(曹植《杂诗·西北有织妇》)
有因为相思而无心演奏乐器的:
北方有佳人,端坐鼓鸣琴。终晨抚管弦,日夕不成音。(张华《情诗》)
思妇临高台,长想凭华轩。弄弦不成曲,哀歌若送言。(王微《杂诗二首》之一)
鸣鹂叶中响,戏蝶花间鹜。调瑟本要欢,心愁不成趣。(徐悱妻刘令娴《答外诗二首》之一)
还有因为相思之痛连给爱人的信都写不下去的:
妾家边洛城,惯识晓钟声。
钟声犹未尽,汉使报应行。
天寒砚水冻,心悲书不成。(刘孝威《奉和湘东王应令冬晓》)
当爱人远去之后,女子被困在幽闭的深闺里,什么事都做不成。被否定的不仅是她从事的工作(装扮、纺织、演奏、书写),也是她生存的意义。高居翰注意到“中国的爱情诗歌、戏曲和小说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們通常致力于刻画爱情被延迟或被否定的忧郁感伤,而不是庆祝爱情的圆满”。画家延续了这一传统,创作出“倦X图”。这类图画可以看作是对中国情诗中“不成”这一主题的形象化再现。
早期的图画与诗歌呼应,多表现女子无心梳妆、纺织、刺绣或演奏乐器,随着明代中叶之后女性阅读活动的增多,社会对女性的审美从对容貌品德的狭隘欣赏转向对才华气质的推崇赞美。与此同时,在描绘女性的绘画中,便多了一件新道具:书籍。“倦读图”(图1、8、9)大量涌现。图画中苦苦等待爱人的不再是目不识丁的普通女子,而是能读书的知识型女性。她手中的书本和她柔媚的体态一样,都令男子赏心悦目。
五、缺席的情人
南朝的情诗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女主人公的夫君或情人一定不在身边。然而,尽管男性并不作为主角在诗歌中出现,他却仍然主导着女主人公的喜怒哀乐,是她情感世界真正的主人。这位看似缺席的情人,其实无处不在。
绘画亦是如此。画中的女子扮演的只是一个从属、顺服的角色,真正的主导者——男性,不在画幅之中,而在画幅之外。那么,画家借助哪些手段暗示“他”的存在呢?
在《春闺倦读图》中,冷枚通过女子手中书卷上的诗歌提示我们画作的真正主题:
芳是香所为,冶容不敢当。天不绝人愿,故使侬见郎。
女子的千般娇媚万种柔情都是为了那个远在天边不能相见的“郎”。《雍正十二美人图》的绘制者也采用了类似的手法。其中一扇屏风绘有一位手执书卷却无心阅读的美人(图8)。近距离地观看这幅画不难发现,画中美人翻开的书页上正是传为唐代名妓杜秋娘写给情郎的《金缕词》: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须惜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除了书卷上的诗词之外,画中还有另一个重要线索,将我们引向缺席的“他”。那就是美人身后墙壁上悬挂的书法作品:
丹唇皓齿瘦腰肢,斜倚筠笼睡起时。毕竟痴情消不去,缃编欲展又凝思。
这首诗的题写者不是别人,正是雍正本人。诗作点明了美人无心阅读的原因——“毕竟痴情消不去”。巫鸿指出画中女子所思念的、不在场的情郎就是未来的雍正皇帝。尽管他在画中没有出场,但他的书法和题款代表了他的存在。“她的美貌和才华则凝聚在其迷人的姿容和手握的诗卷之中。她在等待他(雍正)来攀折。他不仅仅只是钟情于她的美貌、空间与文化的有情郎君,也是这些美貌、空间与文化的征服者和主人。”
清代郑岜屿的《坐在竹椅上的仕女》同样描绘了一位搁下书卷,凝神沉思的女子(图9)。不过,画家无意让我们窥见书卷上的内容,而是借用了另一件道具来暗示画面的主旨。在女子身旁的几案上放着一件特殊的首饰——两个彼此相连的玉环。玉连环是古代男女间传递爱情的信物,寓意着“哪怕粉身碎骨,绝不相离相弃”的坚贞。唐代诗人韦应物在《行路难》中就提到了玉连环:
荆山之白玉兮,良工雕琢双环连,月蚀中央镜心穿。故人赠妾初相结,恩在环中寻不绝。人情厚薄苦须臾,昔似连环今似殃。连环可碎不可离,如何物在人自移。上客勿遽欢,听妾歌路难。傍人见环环可怜,不知中有长恨端。
赠环的“故人”虽然不在身边,但“物”仍在。诗中的玉连环令女主人公惆怅于“故人”的薄幸,画中的玉连环同样提示着在那个画面中不曾出现的男人。《雍正十二美人图》中的一幅描绘了一位倚榻观鹊美人,她的手中把玩着一对玉连环,眼光投向门外花园中的两只喜鹊(图10)。成双的动物象征着爱情的圆满和谐,却也反衬出闺中佳人的孤寂清冷。当他不在,她只有凭借定情之物追忆过往的缱绻相依的美好时光。
除了嵌入画面中的诗歌和代表相思的物件之外,画中美人呈现的姿态本身就提醒着我们:画面之外还有一个她极力想要取悦的对象。只要把《春闺倦读图》(图1)和《李清照画像》(图7)加以比较就会发现,两幅画中的女子虽然都暂停了阅读,但她们的状态截然不同:李清照落落大方地站立着,似乎刚刚从座椅上起身,神情若有所思,仿佛还沉浸在刚刚读过的书里;而春闺里的佳丽将身体扭成了销魂的“S”形,她的手轻托粉腮,还将一根手指轻触嘴角,一双媚眼脉脉含情地望向画面之外。女子为何要“拗”出这个与读书毫无干系的性感造型?英国艺术史家约翰·伯格(John Berger)对西方绘画中女性裸像的分析或许会有助于我们的理解。伯格认为男性观察女性,女性注意自己被别人观察,因此她会把自己变成一个极特殊的视觉对象:景观。西方油画中有许多裸露的女子,她们故作妩媚,搔首弄姿,这是向画面外观察她的男人作出的反应——虽然她同他并不相识,却自觉地作为被观察者,奉献自己的女色。
彼得·莱利(Peter Lely)的《维纳斯与丘比特》就是一例(图11)。这幅画是查理二世(Chales the Second)请莱利为他的情妇内尔·格温(Neil Gwynne)秘密绘制的画像,画中的她正温顺地凝视着画面之外观赏者——国王本人。“但这样的裸露并非她自己的情感表达,而只标志着他屈从于主人(女人和作品的拥有者)的感情或要求。”和国王的情妇一样,《春闺倦读图》中的女子时刻意识到有人在观察自己,她身体的姿势正是摆给那个画面之外的那位观赏者一收藏者看的,为的是激起他的情欲。
结语
南朝的宫体诗不厌其烦地吟咏女性的寂寞深闺。深闺总是被诗人描写为一个封闭的情色世界,“女子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那些元素,比如侍女、孩子、闺蜜、家庭的其他成员,尤其是她的夫君或情人,全部被排除在诗歌的情境之外。在南朝繁盛的宫体诗中,身处锦绣香闺里的佳丽囿于符号化的孤寂里”。以冷枚为代表的清代画家成功地将南朝诗歌中描绘的深闺场景转化为可视的形象。画家既采用了中国传统的仕女画技法,也借助了西方错觉艺术的技巧,使得闺房的空间更具穿透感,画中的佳人和种种陈设也似乎触手可及。
清代“香闺美人”这一类型的绘画尺寸通常比较大。《春闺倦读图》的画芯高一百七十五厘米,宽一百〇四厘米。当画作被悬挂在墙上时,会令观者产生“如对真人”的错觉。《红楼梦》中描述了刘姥姥醉酒后误闯入宝玉房中的经历,这段文字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类“美人图”的功用:
刘姥姥便踱过石去,顺着石子甬路走去。转了两个弯子,只见有个房门,于是进了房门,——便见迎面一个女孩儿,满面含笑的迎出来。刘姥姥忙笑道:“姑娘们把我丢下了,叫我磞头磞到这里来了。”说了,只觉那女孩儿不答,刘姥姥便赶来拉他的手,——“咕咚”一声,却撞到板壁上,把头确的生疼。细瞧了一瞧,原来是一幅画儿。刘姥姥自忖道:“怎么画儿有这样凸出来的?”一面想,一面看,一面又用手摸去,却是一色平的,点头叹了两声。
美人图中人物的尺寸如真人大小,加之画家运用了透视、光影处理等错觉手法,才让刘姥姥误以为是个真正的“女孩儿”。《春闺倦读图》应该也会让观者产生类似的错觉。值得注意的是,刘姥姥撞见的美人图是悬挂在宝玉房中的,画中美人“满面含笑地迎出来”,是为了讨好画作的男主人。这类“香闺美人”画作的观赏一收藏者通常是男性,陌生女子的深闺是他们平时难以涉足之地,但凭借这类画作他们可以“窥见”深闺中的一切:精致华丽的陈设耀人眼目,媚态万方的佳人随时准备着奉献美色。这与其说是真实女子的闺房,不如说是一个由男性的性幻想所构筑的情欲世界。画作的主人公是深闺里的等待者,而画作的主人却是画面外的观赏者。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