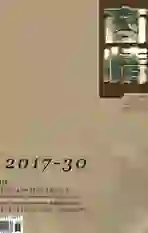论法律的必要性:从柏拉图到卢梭
2017-09-18樊蓉
樊蓉
【摘要】从古希腊时期开始,西方的哲学思想家们都对法律的必要性进行过各自的研究。随着时代和阶级的变革他们对法律的论证都各有不同,但唯一不变的是他们始终都坚持着“法治”。
【关键词】法律 理想国 社会契约
人类的法律思想大概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甚至更远的时期。最开始,古希腊哲学注重的是对自然本身的研究,而从智者开始,研究对象逐渐转变到注重社会伦理和人的研究,但其也都只停留在感性的阶段,所以得出的结论具有相对性,直到苏格拉底的出现才根本改变了这种状况。苏格拉底要求作“心灵的转向”,把哲学从研究自然转向研究自我,即后来人们常说的,将哲学从天上拉回到人间。从苏格拉底开始,自我和自然明显地区分开来,而关于社会,国家政体的构想也逐渐发展起来,法治理论也随着时代背景的变化而不断发生变化。
柏拉图,出生于雅典城邦衰落时期,他痛心雅典贵族政治堕落为寡头政治,在苏格拉底死后,继承苏格拉底大业,终将自己的政治立场和观点著述为影响深远的《理想国》。他在《理想国》中描绘了这样一副画面:以社会的自然分工为建国原则,以理念、哲学为根本指导,遴选出有哲学与政治智慧的“哲学王”,建立以正义为伦理基础,以善为最高目的的政治体制,实施各种明智的经济、社会、教育制度,谋求城邦国家的整体幸福,并能保证统治集团成员不腐化变质,能长治久安。”柏拉图认为这种贤人政制是“最好的政制”,但他同时也回归现实,他清楚的知道这是世界上不存在的“理想国”。现实如此,哲学王既非天生,也非后天可以造就的。,因为他认为,人性包含理性、意志和欲望三方面,只有在理性支配意志和欲望时,人才能获得正义的德性,但是由于人性中始终存在善恶两部分,兽性的欲望需要外在的权威来约束,而他所认为外在的权威就是指的法律,此为柏拉图关于法律的必要性论证。
亚里士多德主张正义论。他认为作为正义的体现,法律离不开正义,立法的根本目的就在于促进正义。他是这样论证法治优于人治的:
主张君主政体较为有利的人说:法律只能订立一些通则,在国家发生事故时不会根据事故来发号施令,全盘按照法律通知来运作的政体不可能是最优良的政体,但作为统治者,其心中必然存在着通则,凡是不凭感情因素治事的统治者总比感情用事的人们较为优良。主张君主政体的人可以强调个人的作用,但是应该让最好的人为立法施命的统治者,遇到通则不能解决的特殊事例才让才能让此人通过理智作出较好的审判,但在平等人民所组成的城邦中,一人高高凌驾于全邦人民之上显然是不合理的,既然人人具有同等价值,应当分配给同等的权利,依此,统治者的名位应该的轮番的,同等的人交互做统治者也做被统治者,这才是合乎正义。
但他又在人性论中指出人性普遍是恶的,人的行为受到感情、欲望等本能的驱使,人性不可信,所以由平等人民轮番做统治者不能达到正义的目标。所以建立的轮番制度应该是法律,因为法律恰似全无感情的,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无论哪一种形式的统治都应当遵循法律。
同时他也认为个人权力或若干人联合的权力可以在法律有所不及的时候发挥个人智慧的作用,但执法者应该接受法律训练,在解释和应用一切条例的依据是法意,在对法律没有周详的地方,他们作出公正处理和裁决时也应当遵从法律原来的精神;法律同时也允许人们根据积累的经验,修订或补充现行的各种规章,以求日臻完美。这是亚里士多德关于法律必要性的论证。
到了十七世纪,英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作为英国封建贵族同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妥协下的产儿,洛克的法治理念产生于资产阶级欲脱离封建制度的大背景之下,一切都围绕着保护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而论证。他创造出一种反历史和唯心的自然状态和自然法。自然状态下,自然法赋予每个人同等的执行权力,而没有统一的区分是非的标准和裁判者,事实上人们的实际权力得不到保障,所以洛克强调建立一个足以保护资产阶级各种权利的国家政权的必要性:
处在自然状态中任何数量的人们,进入社会以组成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置于一个最高统治权的政府之下,不然就是任何人自己加入并参加一个已经成立的政府,这样他就授权社会或授权给社会的立法机关,根据社会公共福利的要求为他制定法律,而他本人对于这些法律的执行也有尽力协助的义务,设置在人世间的裁判者有权裁判一切争端和救济国家的任何成员可能受到的损害,这个裁判者就是立法机关或者其为人的长官,而由于这种裁判者的设置,人们便脱离自然状态,进入一个有国家的状态。
在一切以保护财产为目的的前提下,法律的必要性也就体现出来:人们参加社会的重大目的是和平地和安全地享受他们的各种财产,而达到这个目的的重大工具和手段就是那个社会所制定的法律,因此所有国家的最初和基本的明文法就是关于立法权的建立,国家必须以法律来统治而不断临时的命令或决议,立法权最高且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同時,为了资产阶级革命的需要,洛克鼓吹自由论,认为“人类天生是自由的”;“我们是生而自由的,也是生而理性的”;自由意味着不受他人束缚和强暴”,“实在人所受约束的法律许可范围内…不受另一个人的自由意志支配。”除了最高的立法权也即经人们同意在国家内所建立的立法权之外,其他任何意志或法律都不能对人们产生统辖或约束作用。在自由论的支配下,法律的必要性体现为对自由的保护和扩大,“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自由”。
到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作为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卢梭为了表达资产阶级的民主理想,针对法国的封建制度和等级特权,提出了争取自由和平等的战斗口号,并且强烈主张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他提出了社会契约的理论:任何人对于自己的同类都没有任何天然的权威,因为外在强力并不能产生任何超越他人的权利,预示一切合法权威的基础便只剩下人们之间的约定。社会公约可以简化为:每个人都将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下,并且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结合行为就产生了一个道德与集体的共同体,这被称为国家或政治体。然而社会契约形式虽然赋予了政治体生存基础和生命,但这种行为只是使得政治题得以形成与结合,并不能决定它为了保存自己还应该做些什么事情,所以卢梭认为这是法治的必要性,即由立法来赋予国家以行动和意志。他在《日内瓦手稿》中写道:“法律是政治体的唯一动力,政治体只能是由于法律而行动并为人所感受到,没有法律,已经形成的国家就只不过是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虽然存在但不能行动,因为每个人都应该顺从公意,那首先就必须认识公意,于是就出现了法律的必要性”。具体来说,社会中存在一种普遍的理性正义,但从政治或社会契约来考察事物,缺少了自然的裁判,正义的法则在人间便形同虚设,因此就需要有约定和法律来把权利和义务结合在一起,并使正义能符合于他的目的——使正义能应用于社会。
从古至今,法律的来源多样,可以是神意,可以是社会契约;法律的作用也多种多样,可以用来约能束人性中的恶,抑或用来维护新兴资产阶级的权利,但都能体现出每个时代的统治阶级的意志,都是统治阶级用来维护自己统治的工具。但工具有很多暴力,宗教等等,为何每个时代都有人选择法律作为“治国之利器”?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从人性本恶的角度看,法律可以约束人性中的恶,使整个社会朝着“善”的方向发展;第二,法律作为一种规则“全无感情”,一旦制定出来就应当得到遵守的性质是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第三,法律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由人制定出的,所以法律必定会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并且法律不够灵活这一缺点刚好要求一定程度的“人治”来配合,这既保证形式公平也可以保证实质正义。所以法律对于社会统治是必要的,法治虽有缺陷但其仍有优于“人治”的不可替代性。
参考文献:
[1]姚介厚.柏拉图的城邦文明论和“理想国”设计[J].云南大学学报,2010.
[2]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商务印书馆,1965.
[3]洛克.政府论》(下篇)[M].商务印书馆,1996.
[4]卢梭.社会契约论[M].商务印书馆,2005.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