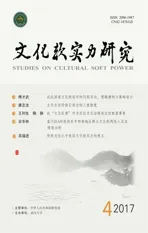论“文化民意”作为社区文化治理决定性配置要素
2017-09-18王列生
王列生 鞠 静

论“文化民意”作为社区文化治理决定性配置要素
王列生 鞠 静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制度功能框架,已经延伸至社区文化治理现场,这显然与世界各国的文化治理前沿场域处在同步位置。在“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常态下,如何在“最后一公里”实现文化平台运行、文化资源配置等方面的有效性,对解决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末梢制度功能提出了诸多现实挑战。问题是,由于制度建构和治理转型还在完善和探索过程中,所以一定程度的失效与失灵在所难免。提出“文化民意作为社区文化治理决定性配置要素”的学理命题,意在为场域解困的时代方案,提供某些知识参照。
文化民意 社区 社区文化治理 配置要素
在国家文化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文化发展战略制度诉求过程中,兼之全球化背景下各国文化治理的成果经验启迪与失败教训参照,社区文化治理不期而至地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乃至“最后一公里”。这既与转型中国文化治理价值导向高度契合,同时也与全球文化治理前沿探索处在同步位置,合法性、必要性与可行性,都不存在遭受本体否定的风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中就没有隐存的问题与危机,无论体制设计还是实际运行,稍不清晰抑或处置得稍加随意,就会形成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负面后果。本文即是从一个特定命题角度切入,初步展开讨论,以期引起相关各方更广泛同时也更系统化的学理关注。
一
对一个特定社区而言,无论规模大小,所谓“文化民意”*我们所定义的社区“文化民意”,是指社区边际内全体居民的“文化意志”。他们的“文化意志”既包括活动形态决策意志,也包括活动行为参与意志;既包括文化设施建设规划意志,也包括其他文化资源配置意志;既包括多样性意志,也包括特殊性意志;既包括民间习俗草根文化意志,也包括公共社会场域文化意志。至于其无条件合法性,可参阅习近平的观点:“要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问题,拆除‘心’的围墙,不仅要‘身入’,更要‘心入’、‘情入’。”(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8页。)由两个互相黏着的部分构成:其一是边际内的“最大公约数”,其二是“特殊少数”。尽管“最大公约数”绝大多数情况下,内在地统辖着包括“特殊少数”文化参与诉求或者文化行为意志,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些诉求和意志之外,就没有“特殊少数”的特殊诉求与特殊意志。于是也就意味着,从社区文化治理的决策过程开始,一方面必须最大限度地使某一具体决策项目,其最终形成方案基于“最大公约数”的坚实支撑之上;另一方面还应该在其所形成方案中,为“特殊少数”预留其文化意志表达通道,同时在社区内所建立的一系列文化活动平台中,预留其必要空间、项目和参与机会,当然也包括资源享有权利。
在社区文化治理过程中,之所以要立足于最终形成方案“最大公约数”的坚实支撑,不仅在于它表征着特定社区的“集合性文化意愿”或者“聚焦化文化诉求”,还因为它能充分体现“文化民主”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原则充分实现的现实诉求,并切实有效地解决文化民主研究专家们通常所描述的诸如“正义的原则、民主的原则,以及公民身份等极其五花八门、争议不断,而配置问题却只有一个正确的答案”*Denise Meredyth and Jeffrey Minson(ed):Citizenship and Cultural Policy,Sage Publications,2000,London.,抑或所谓“社区参与乃是一个总体目标。我们并不想仅仅让一部分人进入其地盘而另一部分人离开”*David Karraker and Diane Grams:Partnering with Purpose,in Diane Grams and Betty Farrell(ed),Entering Cultural Communities: Diversity and Change in the Nonprofit Arts,Rutgers University Press,2008,p.100,New Brunswick.。如果治理事态进展至此,则我们长期在层级文化行政资源配置、平台运转以及活动参与等诸多方面的公平不足与效率障碍,就都能在社区文化治理边际范围内,找到基于新理念有效性的文化普惠方案,并且使诸如“均等化”“参与率”和“满意度”等绩效标杆,演绎为去修辞化的日常绩效现实。恰恰是这样一种有效文化治理后果的真切现实,将会自下而上地重建整个社会对公共服务体系的功能预期与体制信心。
之所以强调在“最大公约数”之外,还必须于治理方案中为“特殊少数”预留必要的文化诉求渠道与文化参与机会,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民主体系,至少从理论出发点而言,具有较任何既有其他社会形态下的民主体系,更具先进性同时更具充分性的价值取向本体特征。正是这一价值本体特征的内在制约,决定了社区文化治理过程中的社会主义文化民主,将在制度安排层面更能体现制度形态的文化普惠优越性。这种制度安排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呈现为补充安排,但终究是以一种体制功能的和解姿态,为所在社区第一次选择失去邀约机会的数量很小的居民,提供了保障性的二次选择机会,并因选择的机会满足针对性而获得有效文化参与的特殊权利。恰恰就是这样一种特殊文化诉求的权利保障,不仅使得边际内的特殊文化诉求个体,能够实现其在场获得感诸如“对他们而言,艺术能与其日常生活更密切相关,而不使其从所珍视的特殊机会中被排除,由此而使他们称道和欢庆”*Steven J.Tepper:The Next Great Transformation: Leveraging Policy and Research to Advance Cultural Vitality,in Steven J. Tepper and Bill Ivey(ed),Engaging Art: The Next Great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s Cultural Life,Routledge,2008,p.364,New York.,而且这种在场获得感将会凝聚其社区身份信心,并在这一的信心建构中促进其与“所在社区的充分合作”*Dorteskot-Hansen:Local Culture and Local Identity,in Jorn Langsted(ed),Strategies,Aarhus University Press,1990,p.31,Esbijerg.。毫无疑问,这样一种制度安排及其功能实现,将使任何机构形态抑或规模大小的中国城乡社区,都能最大限度地规避社区文化裂痕乃至冲突的风险,从而为和谐社区与和谐日常生活方式建构,奠定基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预期制度保障。
很显然,一种融合“最大公约数”与“特殊少数”的社区文化民意,在社区文化治理实践中具有全覆盖意义,因而也就一定能为后续文化治理进程提供有效的充分必要条件,而我们的严峻现实,通常就在于失去而且漠视这个前提。
二
漠视的根源,在于社区文化民意从来就未实质性地纳入文化治理的决策编序,至多不过相关决策程序中给予某些或形式化或游戏性的参照。而功能主导力量,由此也就只能是对称意义上的“文化官意”。
从我们所应坚守的意识形态理性出发,“文化官意”在特定条件下获得“主导”配置的决定性力量,本来应该具有无可置疑的合法性乃至逻辑合理性。其依据在于,“特定条件”中包括一项根本性前置存在条件,那就是“文化官意”在与“文化民意”的语义边界绝对叠合状态下,所谓“官意”与“民意”的对应生成关系甚至对立紧张关系,就会社会化同时也语境态自然消亡*关于这种消亡的合法性与逻辑合理性,参阅习近平同志所说的“党的干部必须做人民公仆,忠诚于人民,以人民忧乐为忧乐,以人民甘苦为甘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413页)。。也就是说,人民的文化意愿本来就应该是我们从事公共文化服务的行为逻辑起点。但我们所常常遭遇的现实紧张关系却恰恰在于,不仅在现实的文化治理过程中很难见到理想价值标杆所指涉的这类高度叠合,而且还更多地与各种形态的非叠合状态照面。其尴尬之最,就是某些文化行政官员以一己意志为权力运作的功能杠杆,以“会议热情”或“红头文件权威意识”代替基层文化诉求的深入调研,剃头挑子一头热地“打造文化”“送文化”“服务文化”直至“审批文化”,并由此而年复一年地忙碌于“文化形象工程”“文化政绩工程”“文化任务工程”和“文化示范工程”,结果是社会文化治理过程中形形色色的“越位”“缺位”“虚位”乃至“体制空转的治理者娱乐本位”。这不仅不能使“社区”在文化治理作用下获得“文化社区”的生存建构,就仿佛美国华人“飞地”的圣·露易斯社区,经过四十多年的文化治理而全面实现其“文化社区”融合性生存建构,从而“大相径庭于全美各地的许多其他美华社区,不是圣·露易斯物质边界差异,而是文化社区发展的变化”*Huping Ling:Chinese ST.Louis:From Enclave to Cultural Community,Temple University Press,2004,p.169,Philadephia.,而且更谈不上将特定社区激活为“创意社区”,使社区在非被动性接受文化资源配置与文化参与机会共享的同时,能够以一种激活后的主动姿态去进行自我整合、自我进化发展以及自我文化再创造与再生产,从而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功能助推下,升级转型为具有社区文化生存主体性与社区文化活动自治性的增量社会单元。这类“创意社区”积极治理成果,来源于“所有的全部努力工作,如今都集合为一种驱动性的规划,而这个规划就是使其社区转型升级。治理者对此十分清楚,而且也很具体,那就是进一步的治理项目人们能够测值评估”*Tom Borrup:The Creature Community Builder’s Handbook: How to Transform Communities Using Local Assets,Art,and Culture,Fieldstone Alliance,2006,p.207,Saint Paul.,而且也来源于社区文化治理者,如何将公共资源、地方文化资源乃至社区自身的潜在资源,进行富有想象力的功能整合与能力再造。很显然,被“官僚主义”牵系着的一些“文化官意”,从一开始就放弃了类似治理的逻辑起点和价值原点,当然也就很容易滑向“权力意志”无条件支配方式的文化治理无效化歧途。
由如上分析不难看出,在社区文化治理过程中,并非我们在理论上缺乏“文化官意”与“文化民意”意志叠合的可能性,而是在制度安排及其实践操作层面,无法使这样的理论可能性真实落地为实践可行性,包括文化治理在内的一切社会治理,只要理论可能性不能现实地转换为实践可行性,那么所有的合法性价值命题与逻辑合理性方案预设,就都只能是毫无意义的“虚拟修辞”,而我们长期所热衷的,恰恰就是一系列文化行政行为过程中,各层级汇报材料的此类“虚拟修辞”唱和之声。正因为如此,与其失腔走调地为“文化官意”的可能性寻找合法理论命题与逻辑结构,就不如在社区文化治理实践中,旗帜鲜明地以“文化民意”置换“文化官意”,使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作为一项基本制度能与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作壮士断腕式的告别,让“文化民意”成为社区文化资源配置、社区文化活动参与方式、社区文化平台搭建以及社区文化身份构建等一系列相关文化生存与文化发展内容的定位标杆,让“文化民意”充当诸多影响要素中的决定性配置要素,让“文化民意”成为特定社区文化治理的支配主体。
在这一置换中,有两个容易引起语义淆乱的敏感关联命题,需要先行予以事态澄清并给予歧义引起的风险清晰规避。其一,要在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引领的前置条件下,充分体现“文化价值分层”的文化规律,从而在社区文化治理过程中按分层价值目标来给予功能清晰的末梢制度安排,从而能够规避粗暴混存处置中以“大词”作为人民群众切身文化利益不能有效保障的托词。诸如将广场舞参与率也绳之以“文化安全”的价值评估尺度,不仅不能确立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定位,而且也会给社区文化治理的真实命题内涵带来理论与实践层面的巨大障碍。其二,把“政府主导”狭隘地理解为而且操作为具体社区文化平台运作、文化资源配置的层级行政权力持有,这种“持有”一旦成为社区文化治理的末梢制度支撑点甚至权力非有效监管下的特定官员行政任性,就极容易事与愿违地演绎为韦伯在《支配社会学》中所描述的“支配权力,通常是基于经济与社会差异之(至少)相对的齐平化”*韦伯:《支配社会学》,康乐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8页。,由此也就至今还在持续我们几十年来一以贯之“办文化”的坚守。哪怕是那些修辞性创新的诸如“点餐制”“网格化服务”“供需均衡”,某种程度上仍然不过是“文化官意”决定性要素配置的末梢功能修复之举,甚至可能是口号而非命题的“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的翻新版或简约陈述句式。问题的实质在于,总是忧虑“政府主导”失灵,总是焦躁于“办文化”权力失去后,文化行政部门或文化平台运营团队将会一无所有。
我们必须深刻地意识到,意识形态安全是更高价值层面的社会本体问题,因而也就需要一套完整的意识形态安全保障制度和治理方案来予以更强有力的支撑,从而使包括社区文化治理在内的公共文化治理,得以脱离混存的价值分析纠缠而获得更加系统、清晰、完整和问题针对性的治理理性与治理体制;另一方面则是在“放管服”大潮的簇拥之下,所谓文化治理的“政府主导”,正在匹配性地同步迈向宏观性、总体性、顶层性乃至监管性,各层级文化行政的价值导向,由此从“文化提供者”向“文化服务者”和“文化治理者”身份转型。所议的两个方面,皆非学理推演的理想状态,而是转型中国正在宏大绘制的“中国方案”所已经给定的文化治理前置条件。这些前置条件一旦以合力作用方式,落地到每一个社区的社区文化治理现场,就会诉诸制度末梢的弹性和张力,考验其是否能够一切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地形成大批差异性有效方案,尤其要考验这样的方案,何以能在社区文化治理模式的本体性变化中获得我们期盼已久的可持续有效性,从而使社区文化生存状态,呈现为“不断地从社会言说走向社区言说。这种言说常常在政府权力部门与市场的非道德化任意交换之间,与自主权利担当个体的自由之间,确立起一片生存领地。这种社区空间俨然一种自然的、政治之外的人际关系地带。不仅仅是本体性的主张,意味着事实就是如此,也意味着一种积极的评价”*Nikolas Rose:Community,Citizenship,and the Third Way,in Denise Meredyth and Jeffrey Minson(eds),Citizenship and Cultural Policy,Sage Publications,2000,p.6,London.。
由此不难看出,不是社区文化治理失灵的事态本身终极无解,亦非政府文化建设的价值主张以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制度安排指向偏离,而是我们不能在全面改革的时代大背景下转换文化治理观念,重新审视政府角色定位,改变运作模式并且对所有配置要素二次编序甚至二阶影响系数定位,使一切文化行政行为遵循客观文化规律而非延续已久的权力意志,一句话,充分实现文化治理“新常态”运行方式与价值目标,如此则效率、有效性、公平正义以及亿万参与者的热情响应等,就都不成其为长期无解的死结。
三
至此,就不是要不要将文化民意作为社区文化治理决定性配置要素,而是问题转场至如何确立其决定性配置要素的社区文化当前语境,以及处在这一语境之中,所谓决定性配置要素,其语旨重心何在?必须先行言明的是,确立“文化民意”在社区文化治理中的决定性配置要素地位,以此置换积习已久的“文化官意”,丝毫不意味着基于精准角色定位的政府及其层级决策机构和运行平台的退场,丝毫不意味着其他相关配置要素在社区文化治理中的要素合成基本功能,丝毫不意味着由此可以删除、削弱以及低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各级文化决策者、文化活动组织者、文化绩效评估者、文化供给服务者甚至文化响应志愿者等诸多行为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新性。在诸如此类都作自明性悬置的知识处置方式下,所要重点讨论的“决定性配置要素”何以得到保障的技术方案,在我们看来突出地表现在:
(1)必须在文化治理基本理念上确立“文化民意”的概念合法性和存在本体性。
(2)必须有一套落地生根行之有效的社区文化治理末梢性文化制度安排,并且这一安排既能够以“文化民意”为逻辑起点,又能够以“文化民意”为价值归宿。
(3)与此相匹配,形成末梢性文化制度安排的调节弹性机制与缝隙修复机制,最大限度减少能量内耗的同时,不断获取增量和升级的内存驱动力。
中华民族在其绵亘久远的历史长河中,创造出辉煌而且充满智慧的优秀文化传统,这个传统作为东方血缘纽带为最重要特征的内在维系和崇高精神家园,这些当然是无条件值得褒称、弘扬和传承创新的民族血脉之所在,所以习近平同志站在21世纪全球化高潮迭起的时间位置,仍然坚信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5页。。但站在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角度看问题,一个同样必须无条件批判、剔除、颠覆并坚决与之保持价值分异态度的思想史事实是,以“官本位”和“愚民思想”等为特征的封建文化沉渣,几千年来一直像一座大山一样压迫着代代因沿的亿万万人民大众,失去他们最起码的社会尊严与最小几率的知识机遇,所以也就是鲁迅“吃人”命题合法性所在。在《老子》所谓“常使民无知无欲”(《老子·三章》),《商君书》所谓“民弱,国强;民强,国弱”(《商君书·弱民》),《论语》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鬻子》所谓“民者,积愚也”(《鬻子·撰史五帝三王传政乙第三》),《孟子》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孟子·滕文公上》)等这一类同质性极强的叙事内容里,愚民对人民的社会本体存在的主体建构机会的剥夺,在某种程度上其伤害并不逊于每一次血淋淋吃人历史个案现场。而问题的不寒而栗之处在于,被遮蔽的封建文化糟粕,不断地在跟进性呐喊优秀传统文化的口号过程中沉渣泛起,腐蚀和异化着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及其经受过现代性洗礼的“权力绑架者”与“知识特权者”,走向文化返祖和身份蜕变,重回官僚权贵或封建士大夫愚弄并且压迫人民大众的历史老路。正因为如此,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制度建构过程中,尤其是在社区文化治理的现实操作实践中,要想“文化民意”成为决定性配置因素,要使人民的主体性建构真正得以实现,观念问题和思想解放问题依然是社区文化治理模式创新与思路转换的拦路虎。只要思想观念拦路虎不被迫让路,甚或彻底消除,一切后续的制度安排与技术方案设计,就都无从谈起。至少就社区文化治理的中国进展现状而言,这是迫在眉睫的消障之首,而且也是消障的复杂性之首。
观念转型的事实后果能否在无数社区真正成为价值预期后果,完全取决于我们能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条件下,在完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制度建构过程中,尤其是在末梢性制度张力可操作性安排中,获得功能化有效支撑。制度末梢作为制度框架的有机组成部份,是打通“最后一公里”的关键所在,因而具有不可低估的复杂微观系统性与复杂可持续循环性,单是匹配设施的硬件规划,制度设计者就被迫充分考虑社区居民大面积参与,并采取诸如“倾向驱动的方式”“机会驱动的方式”“问题驱动的方式”“目标驱动的方式”“远景驱动的方式”以及“混合方式”等相关技术手段*参阅埃里克·达米安·凯利、芭芭拉·贝克尔:《社区规划——综合规划导论》,叶齐茂等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版,第99~102页。。既然如此,我们也就要追问,在社区文化治理中,究竟什么样的制度末梢形态,才能确保“文化民意”成为决定性配置要素?就目前的研究进展而言,我们还只能开列出粗糙而且不完善的清单,即:
(1)聚集性文化民意充分表达机制。也就是说,必须有匹配性末梢制度安排,确保特定社区的全体居民,能够随机或定期获得文化诉求面向制度充分表达的机会,并且能在这种表达中精准捕获“最大公约数”和“特殊少数”,就仿佛细节技术方式的“特定研讨会召开时开始的社交场合,通常都向受邀的利益相关者以及其他感兴趣的人们,呈现出广泛的开放”*Patrick M. Condon:Design Charrettes for Sustainable Communities,Island Press,2008,p.36,Washington,DC.。而制度安排的优势恰恰在于,诸如此类的技术细节方式,对有效的社区文化治理而言,都内存于可持续而且具有运行刚性的制度末梢之中。
(2)定位性文化民意决策参与机制。也就是说,必须有匹配性末梢制度安排,让社区内居民获得所有文化事务参与决策的权利和机会。这种参与,无疑是较文化民意表达参与更加深刻同时也更加具有决定意义的深度参与。这种参与实际上意味着,并非居民身份分化中所产生的卡里斯玛型“特殊居民”,由此获得非官方性自治决策者身份,甚至也并不意味着基层文化单位体制内公共文化服务工作者的缺席或离场,而是他们在社区文化事务中最大限度地邀约社区居民的决策参与,从而确保所有社区文化项目开展的最终决策,都是基于“最大公约数”和“特殊少数”决策参与过程中所形成的目标定位,而且这种定位,吻合“托马斯随机均衡法则”“就是要发现公民参与方式选择随环境变化而变化的优势所在”*约翰·克莱顿·托马斯:《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孙柏瑛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8页。。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无论观念如何转变,抑或与之相适应地将社区文化治理的末梢制度建构推进至相对完善的功能框架状态,但一个不容忽视的最大变量在于,如果所在社区内的全体居民,其文化主体性得不到他们自身的热情彰显,或者换句话说,末梢制度运行过程不能不断获取内生动力的功能驱动,而仅仅依赖于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给定能量及其输血性外在强推,那么毫无疑问,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制度末梢的功能失效,只不过是或迟或早的必然被动事态,至少就现场到处可见的景象而言,由这种被动所导致的“体制空转”或“体制自娱自乐”是较为普遍的事实,尽管各级文化行政官员极不愿意承认这一事实。如果我们对这一被动性的扭转问题,给予较为细化的施策切分,那么它实际上要求至少作出三个方面的体制运行努力,即:
(1)努力使制度末梢具有调节弹性机制与缝隙修复机制。就前者而言,制度末梢作为具有制度本体属性的具体安排,是更大制度框架的有机构成与有效延伸,因而当公共服务体系的更大框架甚至总体框架出现标杆换位或者任务转型之际,制度末梢必须随之体制响应和功能反应,并在响应和反应的末梢活力中,将更高的制度意志与社区文化治理实际事务加以有效链接,同时在链接过程中,能够迅速及时地把作为更高制度意志功能体现的特定政策工具实际效果,基于正负不同测值作逆向信息反馈。就后者而言,社区作为社会本体的现实单元,任何时候都将随社会的宏观变化而变化,并且由此也就会在社区边际内不断出现生存方式、生存结构和生存价值取向等方面动态转型。转型的结果,必然导致原有制度末梢的其他功能失灵与文化治理缝隙,所以只有使其保持与动态转型相一致的缝隙修复机制,制度末梢及其社区文化治理,才能因这种修复能力而延续其与社区全体居民及其文化生存诉求得到满足之间的协调性。
(2)努力减少制度末梢在社区文化治理过程中,参与治理相关各方动机与行为博弈中的能量内耗,最大限度地形成治理合力,并在服务社区文化治理这一逻辑起点与价值原点上保持与社区文化诉求目标的高度一致,而这也只有“文化民意”的前置条件作用才有可能实现。究其根源,在于社区文化治理乃是社会化而且有较大自治性的场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制度末梢,固然在其中具有基础性功能,但诸如第三方非营利社会公益组织、志愿者团队与志愿者个体,以及其他有限介入社区公共文化治理场域的社会文化资源等,都同样是不可或缺且往往具有极强实效性的配置要素,是社区公共文化治理的积极辅助力量。然而由于介入方式、介入程度、介入动机乃至介入身份等彼此之间差异甚大,所以就必然会程度不同地导致现场事态的能量内耗。既有它们彼此之间的内耗,亦有其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制度末梢之间的内耗。无论是哪一种内耗,都将对社区文化治理带来不必要的负面效果,都有违社区文化治理的各方初衷,都应该尽可能予以规避。在我们看来,要使这样的规避长期有效,从而使各种入场的文化资源和文化介入身份得以整合,唯一具有无条件维系作用的就是“文化民意”,因为只要它们都在“文化民意”制约下积极施为,就一定不会发生社区场域外在介入资源配置与服务投入的关联各方能量内耗事态。
(3)努力获取社区文化治理增量升级内存驱动力,改变长期以来将公共文化服务对象单纯看作受动承接客体的文化关系误判,确立社区居民文化活动的主体地位与条件性自治合法性,从而激发隐存于社区场域内部以及社区居民自身的文化参与热情、文化活动能力和更高文化追求的强烈愿望。一旦这样的能动格局得以形成,社区就会在合力作用的服务性帮助下,逐渐演变为文化治理后果诉求的“文化社区”,社区自身文化潜力得以激活和爆发的能动性自为文化空间,而且会是不断自我转型升级的边际社会身躯,就会有文化自衍效果,诸如“与韩国儿童一样,这些印度移民社区的舞者们,在传统价值和美国文化之间体验某种情调和旋律,以此追求他们的社区成员身份。与索马里人社区和库尔德人社区的儿童迥异之处在于,这些移民群体相对而言已高度与当地语境实现了整合,这一语境对他们的文化传统也非常友善,也许就使社区内的原有紧张,在这样的激励下消解并走向融合”*Jennifer C. Lena and Daniel B. Cornfield:Immigrant Arts Participation: A Pilot Study of Nashville Artists,In Steven J. Tepper,Bill Ivey (eds),Engaging Art:The next Great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s Cultural Life,Routledge,2008,p.157,New York.。社区文化治理达到这一步,就已不仅是社区居民文化参与那么表层化,也不是日常文化生活丰富性那么简单,而更在于上升到了社区文化精神家园建构的高度。所以事态很明显,当“文化民意”维系下的社区文化治理,能够促进社区居民自觉成为社区文化生存和发展的主人,则什么样的积极响应后果都在情理之中。
四
文化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制度建构的价值取向。毋庸讳言,社区文化治理作为末梢端制度功能延伸的前沿场域,“最后一公里”能否打通还面临着诸多障碍和困难。我们只有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价值标竿下确立“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社区公共文化服务是否有效的决定性评价尺度,才有可能克服这些障碍和困难。无论障碍和困难究竟有多大,在人民利益至上的“新常态”下,我们必须寻找到能够现实解困的现代方案,并在方案的实践过程中切实获得社区文化治理的惠民积极成果。在我们看来,确立“文化民意”作为社区文化治理的决定性配置要素,乃是时代方案的解困必要构件之一。
“CulturalPublicOpinion”astheDecisiveElementoftheCommunityCulturalGovernance
WangLiesheng
(Culture Policy Center,Chinese National Academy of Arts,Beijing,China)JuJing(Nation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Development,Wuhan University,Wuhan,China)
The institutional and functional framework of the modern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ystem has been extended to the scene of community cultural governance,which puts it on a par with the world’s forefront of the cultural governance field. Under the “people-centered” new normal,it brings many practical challenges on the basic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ystem function,for instance,how to realize the validity of cultural platform operation and cultural resource allocation in “the last kilometer”. However,the problem is that due to the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the management transformation are still in the process of perfection and exploration,therefore some degree of failure is inevitable. This article proposed an academic thesis that “cultural public opinion should be regarded as a decisive configuration elements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And its aim is to provide the field solution of the era with some knowledgeable reference.
:Cultural Public Opinion;Community;Community Cultural Governance;Allocation Elements
10.19468/j.cnki.2096-1987.2017.04.003
王列生,中国艺术研究院公共文化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教授,主要研究文艺学、公共文化政策。 鞠静,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公共文化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