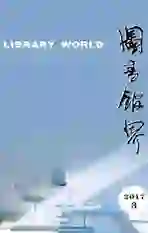《蓼园词选》与《谷诒堂词选》
2017-09-13吕立忠余婧鑫
吕立忠+余婧鑫
[摘 要]《蓼园词选》是乾嘉时期广西词学家黄苏编选的一部词选本,对广西词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该词选问世后湮没无闻数十年,清同治年间被况周颐发现,后又由况周颐嘱人重刊,从此进入学界视野。今研究者所知见者,为1920年重刊本与1988年校点本。新发现有桂林博物馆藏《谷诒堂词选》,为况周颐早年获读的词选原刻本,也是重刊《蓼园词选》的底本。
[关键词]蓼园词选;谷诒堂词选;黄苏;况周颐
[中图分类号]G256.22[文献标志码]B[文章编号]1005-6041(2017)03-0009-04
《蓼园词选》是得到晚清词学大家况周颐极力推荐的一部词选本。况氏著《词学讲义》,为“初学词者”推荐五种必备参考书,该词选即是其中之一。况周颐年少时偶获该词选,得启蒙,学填词,从此进入词学领域。1920年,已成一代词学名家的况周颐嘱门人将其重刊。词选重刊后,受到当时词学界的关注。至1988年,该词选经人校点后编入《清人选评词集三种》(为程千帆主编《明清文学理论丛书》之一)出版。近年来,学者们着眼于该选本的选词与评词,研究黄苏的词学理论及其影响,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有学者评曰:“黄苏是粤西乾嘉时期的重要词学家,他编选的《蓼园词选》在选词与评词上有自己的特色,并引领了粤西词学不事依傍的风气。”[1]另有学者指出:“从广西学术史的角度来看,《蓼园词选》是广西历史上第一部有较大影响的词学著作。”[2]
笔者从事地方文献工作,对此词选多有留意。一直以来,笔者所知为:况周颐曾于1910年所作的笔记著作《香东漫笔》之“卷第二”中,以及1920年重刊该词选时所作的《蓼园词选序》况周颐《香东漫笔》卷第二,见《国粹学报·庚戌第六年》(宣统二年,1910年)之“丛谈·撰录”册,今可见2012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况周颐集》第1册;况周颐《蓼园词选序》,见1920年惜阴堂刊《蓼园词选》,今可见1988年齐鲁书社出版《清人选评词集三种》。中,分别自叙他12岁时,得读二姐夫黄俊熙的曾祖父蓼园先生所编选的词选,从此开始学填词,该词选成为他学词的“导师”。2016年年初,笔者获王娟女士《况周颐词学文献研究》一书,见书中有“《谷诒堂词选》是况周颐幼年启蒙填词之书”“8岁时得到后开始学习填词”[3]的说法,与之前所见况氏的自叙颇为不同,又从王娟书中知《谷诒堂词选》现藏桂林博物馆,于是前往查阅,将该馆所藏《谷诒堂词选》与桂林图书馆藏1920年重刊的《蓼园词选》仔细比较,有所发现。近日,又获读洪德善先生《〈谷诒堂词选〉与况周颐生平研究献疑》一文,知洪先生对桂林博物馆所藏《谷诒堂词选》进行了相关考证,将该本与《蓼园词选》作了比较,得出了结论并留下了疑问——其文最后称:“况周颐早年学词之蓝本很可能是《谷诒堂词选》,后赵尊岳重刊时始更名《蓼园词选》,并有所删减。至于为何更名为《蓼园词选》,为何对更名之事避而不谈,及况周颐得《谷诒堂词选》始学填词是八岁还是十二岁等诸多疑问,都有待进一步考证。”[4]
笔者的考证结论,与洪先生有所不同,我们认为:况周颐早年学词的启蒙之书就是《谷诒堂词选》,它是重刊《蓼园词选》的底本;重刊时更名,是出于对词选选评者蓼园先生的纪念;况周颐得《谷诒堂词选》始學填词非8岁之时。相关情况考述如下,望就正于方家。
20世纪70年代末,况周颐的后人向桂林博物馆捐赠一批况周颐的遗物况周颐后人向桂林文博部门捐赠之事,见1980年第3期《学术论坛》上《况周颐后裔捐赠文物》一文。,其中有一部词选,版心刻印“谷诒堂词选”,内页有钤“夔笙”(况周颐字夔笙)、“卜娱”(卜娱系况氏妻)朱文印。书后有况周颐女婿陈巨来的题识:“岁乙丑冬日,先外舅况蕙风先生尝谕余曰:他八岁时曾诣其姊丈家中,于书箱中见得此词集,遂乞取归家朝夕诵读,即戏学填词,为老师所嘉许。嗣后即益自渐通,卒成倚声名家,盖全赖斯册有以启发之功云云。蒙以见赐,保存迄今未敢遗失也,因特叙于此,敬以贡献广西文物管理委员会用作掌故文物之珍藏。戊午夏日陈巨来谨识,时年七十有四。”该本为况氏后人捐赠,有况周颐及夫人印章,有捐赠题记载其流传,可说传承有绪,曾是况周颐收藏之物可确信无疑。
据陈巨来作于1978年夏的题识可知:《谷诒堂词选》是况周颐学词的启蒙之书,8岁时在姐夫家中获得,1925年冬交陈巨来保存,又数十年后,由陈氏捐赠广西文博部门。此《谷诒堂词选》,与《蓼园词选》何其相似——同样是词选,同样是况周颐从姐夫家获得,同样是况周颐初学填词的启蒙读物。这些相同点的汇集,似乎可以让人猜想二者的关系了,那就是:二者为同一书,同书异名而已。但却有一个关键的不同,在否定这种猜想:二者获得时间不同,一为8岁,系况周颐口授,由女婿陈巨来记写;一为12岁,系况周颐的自记。二者如是同一书,况周颐获得它的时间,怎会有两种说法?如不是同一书,又怎会有这么多的相同点?好在二书俱在,将它们作一番比较,自然会有所发现。故可将疑问暂时搁置,先比较二书。
1920年惜阴堂刊《蓼园词选》,系赵尊岳以况周颐珍藏的蓼园先生词选原刻本作底本的重刊本。1910年况周颐撰《香东漫笔》时,记他所得蓼园先生的词选原本,其选词“起玄真子《渔歌子》,讫周美成《六丑》,最二百二十四阕”。而惜阴堂刊《蓼园词选》,选词起于玄真子《渔歌子》,止于周美成《六丑》,与《香东漫笔》所记,完全相符,不同的只是其选录的词作只有213阕笔者注:惜阴堂刊《蓼园词选》选录词作213阕,但其目录列212阕,漏列一阕。。此或因原本保存不当,至1920年用作底本时,已有残损缺失,已非224阕完整之卷,或是1920年重刊词选时有所删节,抑或况周颐撰《香东漫笔》时有统计之误。
桂林博物馆藏《谷诒堂词选》,书有残损,且其页码错乱:如书的前十叶,第一叶残损严重,已无版心,故不能确定其页码,其余第二至第十叶,版心刻印的页码分别是十八、九、十、十三、十七、六、十六、十二、十一;再如,该册的最后十叶,版心刻印的页码依次是百○一、百○四、百○三、百○五、百○七、百○六、百十一、百十○、百○八、百○九。可知该本已非原装。此种情况,应是长期保存后,书有残损(具体讲是起始部分残损较严重,后半部分保存基本完好)与散脱,经过了重新装订,在重装时产生错乱。幸运的是,版心标刻的页码尚可识读,可据页码按序排正。于是,笔者按其版心标刻的页码次序,逐叶依次与1920年刊《蓼园词选》对比。endprint
首先对比二书的选词。经对比,可以看出,现存《谷诒堂词选》与1920年刊《蓼园词选》选词相同,所选词作的排列顺序也相同。如《谷诒堂词选》最后10阕词依次是:叶梦得《贺新郎·初夏》(睡起流莺语)、苏东坡《贺新郎·夏景》(乳燕飞华屋)、赵文鼎《贺新郎·夏景》(昼永重帘卷)、刘潜夫《贺新郎·端午》(深院榴花吐)、刘潜夫《贺新郎·端午》(思远楼前路)、宋谦父《贺新郎·七夕》(灵鹊桥初就)、刘改之《贺新郎·游湖》(睡觉啼莺晓)、秦少游《金明池·春游》(琼苑金池)、周美成《大酺·春雨》(对宿烟收)、周美成《六丑·落花》(正单衣试酒),这与1920年刊《蓼园词选》完全一致。非但如此,该本版心标刻的最大页码是“百十一”,当为书的最后一叶(为现存本的倒数第四叶),该叶的最后一阕词是周美成《六丑·落花》(正单衣试酒),与1920年刊《蓼园词选》完全一样,也与况周颐《香东漫笔》记载其所获蓼园先生词选的情况“讫周美成《六丑》”相符。当然,因《谷诒堂词选》起始部分残损,已非完整之卷,其选录词作起于何阕,以及选录词作的阕数,就未得与况周颐《香东漫笔》所记印证了。洪德善先生对桂林博物馆藏《谷诒堂词选》进行了相关考证,但遗憾的是,他未注意到该本经过了重新装订且重装本有页码错乱,故他对比《谷诒堂词选》现存本与《蓼园词选》后,不能得出二书选词相同,并且选词的排列顺序相同的结论,也不能得出《谷诒堂词选》“讫周美成《六丑》”的结论,他说:“《谷诒堂词选》……不是讫于周美成《六丑》是肯定的。但二者内容上有重合。”
其次对比二书的评词。可以看出,在评词的文字上,《谷诒堂词选》与1920年刊《蓼园词选》二本是有不同之处的。以《谷》本现存本最后一叶(版心标“百○九”,其实应是原刻本的倒数第三叶)的一阕,即宋谦父《贺新郎·七夕》(灵鹊桥初就)为例,其评词部分文字,天头眉批为:
亦是翻案法,亦是翻空法。
版框内正文部分文字则为:
沈际飞曰:大盲开眼矣,潜夫《端午》词有嗣响。古诗“双星今夜贪欢乐,那得工夫赐巧思”,正起谦父之论。中年以前日子,万不可轻弃了。人生精力一日减一日,意兴一年减一年。时乎,时乎,不再来!欲挥朝云之涕。
古人云“文征实而难巧,意翻空而易奇”,觀潜夫两作并此作
笔者注:“观潜夫两作并此作”,“此作”当是宋谦父《贺新郎·七夕》(灵鹊桥初就);“潜夫两作”,则应是指选录于“此作”之前的刘克庄(字潜夫)《贺新郎·端午》(深院榴花吐)与《贺新郎·端午》(思远楼前路)二阕。,益信。结数语,有含蓄,妙在“随分”二字。
《草堂诗余续集》载:宋谦父,名自逊,号壶山,宋南昌人。文笔高绝,当代名流皆爱敬之。其词集名《渔樵笛谱》。
将1920年重刊本上该阕的词评与之对照,可见《蓼园词选》没有“亦是翻案法,亦是翻空法”十字,其余文字与《谷诒堂词选》应该说是相同的。全部文字中,只有二字不同:《谷》本“双星今夜贪欢乐”,重刊的《蓼》本作“双星今夜食欢乐”;《谷》本“《草堂诗余续集》载”,重刊的《蓼》本作“《草堂诗余续集》藏”。明显是重刊本在排印时出错——“贪”误印为“食”,“载”误印作“藏”。
经查,《谷诒堂词选》的词评,除见于版框内外,还见于天头眉批,但并不是每阕词都有天头眉批。天头眉批涉及所选词作的技巧、方法、意境等等,或为蓼园先生本人自评,或为择录他人之语,文字长短不一,短者数字,长者数十字。将1920年刊《蓼园词选》的评词文字,与《谷诒堂词选》现存本的评词文字对照,可以看出,《谷诒堂词选》眉批部分的文字,《蓼园词选》没有,除此之外,二书评词部分的文字可以说是相同的(刻印、排印时个别文字的错误除外)。
经以上介绍、考证,可以确定:其一,桂林博物馆藏《谷诒堂词选》,即是况周颐获得的二姐夫的曾祖父蓼园先生选编的词选,它是1920年赵尊岳刊印《蓼园词选》的底本。其二,重刊的《蓼园词选》,选词及选词的排列顺序依照《谷诒堂词选》本,但它的评词只采录了《谷》本版框内部分的文字,而没有采录《谷》本眉批部分的文字,此是二者的区别。其三,今桂林博物馆藏《谷诒堂词选》本,书已有残损,且页码错乱,已非赵尊岳借得用作底本刊印《蓼园词选》时的原貌,更非况周颐最初得到时的原貌。重刊的《蓼园词选》,是否在《谷诒堂词选》的基础上有所删减,因所见《谷诒堂词选》残损,故暂不能定论。
况周颐因偶得蓼园先生选编的词选而进入词学领域,并颇有成就,他曾于《蓼园词选序》及《香东漫笔》中称谢蓼园先生的词选“是余词之导师也”,但对蓼园先生的情况,他知之甚少——他先后三次对蓼园先生的情况进行记载,都十分简单:其《香东漫笔》中记为“余女兄三,某仲适黄,名俊熙,字吁卿。吁卿之曾祖蓼园先生,有词选梓行”;他为重刊的《蓼园词选》作序时,关于词选作者,只有“蓼园先生姓黄氏,吾姊夫吁卿比部之曾大父”一句;其《词学讲义》中记为“蓼园先生姓黄,名佚,临桂人”[5]。可见,他对蓼园先生的了解并不多,只知是二姐夫黄俊熙的曾祖蓼园先生,而不知蓼园先生的名讳。他想搜集蓼园先生的词作,却一直一无所获——1910年的《香东漫笔》中,他写道:“先生选词若是之精,断无不工填词之理,顾所作迄未得见。”因此,笔者认为,1920年,在重刊蓼园先生词选时,况周颐未用原书名——《谷诒堂词选》,而以作者之字号名其书,取名《蓼园词选》,大概是出于他对蓼园先生的纪念。
行文至此,可以回答,也必须回答一个疑问:《谷诒堂词选》与《蓼园词选》既然是同一书,况周颐获得它的时间,怎么可能有8岁与12岁两种?笔者认为,只因其中一种为错记,并且,笔者还认为,8岁为错记。理由如下:
况周颐于1910年在《香东漫笔》中记述他12岁得蓼园先生的“词选”而学作填词,其文曰:“余女兄三,某仲适黄,名俊熙,字吁卿。吁卿之曾祖蓼园先生,有词选梓行……余年十二,女兄于归,诒余是编,如获拱璧。心维口诵,辄仿为之。是余词之导师也。”1920年他为《蓼园词选》作序时,同样明确记其12岁获读蓼园先生的词选后学词,并且在得该词选前“未尝知词”,他还明确记其始学词是壬申年,其文曰:“曩岁壬申,余年十二,先未尝知词,偶往省姊氏,得是书案头,假归雒诵,诧为鸿宝。由是遂学为词,盖余词之导师也。”此外,1915年,好友朱祖谋为他刻成《餐樱词》,他于该词集的自序中言“余自壬申、癸酉间即学填词”[6],据上,况周颐学词始于清同治壬申、癸酉年间(1872—1873)。况周颐的出生年,学界尚有争议,有1859年与1861年二说endprint
可参阅郑炜明《况周颐先生年谱》(200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王娟《况周颐词学文献研究》(2015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书的《况周颐生平考辨》一节,等等。,但即便是出生在1861年,壬申、癸酉始学词时,他也不只8岁,而应有十来岁。再有,12岁之说,系况周颐自记,且曾有不同时期的两次文字记载,应非一时误书,可信度高。而8岁之说,为陈巨来听闻况周颐之言以后,又过了数十年后的记写,很可能误记,并且,当时即很可能误听洪德善先生提出,况周颐于《香东漫笔》与《蓼园词选序》自叙的得书经过,前者是“女兄于归,诒余是编”,后者为“偶往省姊氏,得是书案头”,二者所叙“即有不同”,“情境殊异”,说明况周颐作《香东漫笔》与《蓼园词选序》,追忆获书经历时,“记忆并不十分清晰”。对此,笔者有不同看法。况周颐的两次文字记载,确有不同之处,但是,二者都表述了一个核心意思,那就是“得蓼园先生词选后学填词,该词选是自己学词的导师”,这样看来,“女兄于归”与“偶往省姊氏”应是相互关联的事,“女兄于归,诒余是编”与“偶往省姊氏,得是书案头”则为同一事件(即“得获词选”)的不同表达。况周颐叙述这一事件,不同时期(相隔十年)的自述,于文字表达上有所不同(先前为“二姐归嫁时诒书”,后来为“探望二姐时获书”),应属正常。将况氏的两次叙述进行梳理,可推想当时获书的经过是:况周颐12岁那年的某天,二姐况桂珊归嫁黄俊熙,他送亲到了二姐夫家,偶然得读蓼园先生选评的《词选》,如获至宝,即向二姐提出,欲借书回家据况周颐《香东漫笔》中记,当时还曾请求登临黄氏家祠内存藏有词选印版的偶彭楼,二姐因其年幼而未许。,二姐当时(或第二天“回门”时)将书送给他临桂旧俗,新娘出嫁,由新娘的兄长、弟弟伴送至夫家完婚。新婚翌日,女家派新娘的弟妹或亲属接新郎新娘“回门”。详见1996年《临桂县志》第三十一篇第二节。。应该说,二姐“适人归嫁”之时,又发生了对自己影响极大的事(进入词学领域),当是记忆深刻的,一般不会记错。况周颐的这两次文字记载,与陈巨来据况周颐口授所记的“曾诣其姊丈家中,于书箱中见得此词集,遂乞取归家”也是相吻合的。
以上,即是笔者关于《谷诒堂词选》与《蓼园词选》之关系的考述,其中涉及况周颐获《谷诒堂词选》始学填词的年龄问题。应该说,《蓼园词选》对于研究清代词学理论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特别是,它曾是“临桂词派”(或称“粤西词派”)旗手况周颐的启蒙读物,研究“临桂词派”的发展,探讨渊源,不能不提到這部书。今存《谷诒堂词选》,为研究者提供了与重刊的《蓼园词选》有所区别(即在评词文字上)的、最原始的第一手资料,尤其是,它曾是况周颐获读并珍藏之原本,故更宜珍视。期待学界对其有更多的研究。
[参考文献]
[1]张学军.一部自成格调的词选:浅谈粤西词学家黄苏及其《蓼园词选》[J].作家,2008(10):141.
[2]王德明.《蓼园词选》的选词与评词[J].贺州学院学报,2012(3):23—27.
[3]王 娟.况周颐词学研究文献[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69—70.
[4]洪德善.《谷诒堂词选》与况周颐生平研究献疑[J].词学第三十四辑,2015:411—416.
[5]况周颐.况周颐集·第5册[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11.
[6]况周颐.况周颐集·第3册[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301.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