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岁,人生新开始
2017-09-03朱小海
专栏
四十岁,人生新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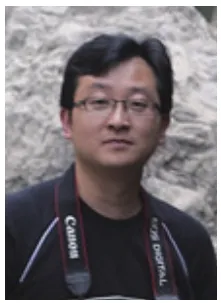
朱小海,伪文艺中年,生于江阴璜塘,常以江因、黄唐为马甲行走江湖。好读书,不求甚解。好电影,不分良莠,自恃定力深厚,欲于光怪陆离风月片悟禅意。
钱玄同先生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非常有趣的一个大人物。早年师从章太炎先生,学习文字学,和周树人、周作人是同门师兄弟。新文化运动期间,原本坚定不移要复古的他却充当急先锋,倡议《新青年》用白话文出版,后来进而甚至提出了简化字计划和拼音注音方案。他还是“鲁迅”的催产妇,鲁迅先生后来在《呐喊》自序中回忆过这段往事,像极了剧本的形式,其中有这么一段,是鲁迅先生所有文字中我的最爱。
S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那时偶尔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
一场表面波澜不惊的对话,其实却是春雷滚滚,由是有了《狂人日记》,有了鲁迅。
我们讲“四大铁”,一起同过窗、一起扛过枪、一起分过赃、一起嫖过娼,鲁迅和钱玄同占了前两个,同是章太炎门下弟子,同是新文化运动斗士,至于后两个,我觉得是不可能有的,虽然同校任教,并无行政职务,何况两位先生私德极好,钱先生自律极严,有人以他妻子身体不好为由劝他纳妾,钱先生严辞拒绝,说:“《新青年》主张一夫一妻,岂有自己打自己嘴巴之理。”
没想到,这两个“老铁”后来也由粉转黑了。学术上的分歧和理念上的差异,就不去说了,单说有趣的吧。1932年,鲁迅先生发表《教授杂咏四首》,第一首说的就是钱玄同:“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何妨肥猪头,抵挡辩证法。”钱玄同生性偏激,年轻时为了表示对封建遗老的憎恶,曾说过,人到四十岁就该死,不死也该枪毙。年轻时过足了嘴瘾,结果自己也活到了四十。
其实四十岁挺好的,随着阅历的增加、经济上的积累,少了些惶恐和焦虑,多了些淡定和从容,周润发当年为洗发水做广告时,用不标准的普通话说:“成功?我才刚上路呢。”
《米尔克》就是讲了一个四十岁上路的故事。哈维•米尔克是纽约城里的一个一事无成的中年男人,直到四十岁生日前夜遇到了年轻俊俏的斯科特,才明白自己喜欢的是男人。米尔克给斯科特喂食自己四十岁的生日蛋糕时说:“40岁了,我还没有完成一件让我骄傲的事呢。”
这对神仙眷侣随即搬到旧金山,在卡斯特罗街区开了一家照相馆,并逐渐成为同性恋人的聚集地。1970年代的美国,人们对待同性恋的态度仍然保守和歧视。米尔克明白,只有“我们”被接受,“我”才能被认可,于是走上了从政之路,剪去长发和胡须,换上西服,屡败屡战,屡战屡败,为同性恋者“不再躲在柜子里”而奔走呼喊。
米尔克在演说中说:“如果暗杀让我倒下了,我希望能有十个,一百个一千个人站起来,如果有子弹射入我的大脑,让它也打破所有柜子的门。我希望这运动能够继续,因为这与个人得失无关,与利己主义无关,与争权夺利无关,而与‘我们’有关,没有希望,‘我们’只有认输。”
米尔克真的被一颗仇恨的子弹射杀了,但希望还在,曾经因为政治离开他的斯科特,接过了他的接力棒,在四十岁时踏上赛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