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心、笨拙、诚实、细心”:读李师江的长篇小说《福寿春》
2017-09-03张婧冉
张婧冉
“耐心、笨拙、诚实、细心”:读李师江的长篇小说《福寿春》
张婧冉
一、转型
李师江是“70后”小说家中引人注目的一位。凭长篇小说《逍遥游》获得2005年度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2007年出版长篇小说《福寿春》。李师江被视为“继王朔之后最具叙事魅力的小说怪才”,并被海外媒体誉为“中国最隐秘的小说天才”。其早年写作年少狂狷,落拓不羁,充满着青春期的活力、躁动和叛逆,而从《福寿春》开始,其写作风格有了很大转变,这也正是他努力进行创作转型探索的成果。
在李师江的众多作品中,《福寿春》独树一帜,表现出和其他作品迥然不同的审美风格:平静、缓慢、细碎。这种独特性也引起了论者的广泛关注。比如张丽军等人认为“李师江诚心诚意讲述一个饱蘸岁月光华的水乡故事,而非用语言漩涡搅动本就躁动不安的思想。”万孝献认为“《福寿春》仿佛是李师江的“悔过书”,他彻底颠覆了自己的创作风格。以前是刀刀见血笔笔张扬,现在是处处收敛至拙至纯。以前是愤青文痞玩世不恭,现在是谦卑平和崇拜大地,前后反差很大。”宋强认为“读过李师江《逍遥游》的人,再读《福寿春》,都会感觉到巨大的不同,会惊诧于作者写作风格转变得太过迅速——从年轻人特有的强烈不满、十足的塞林风格一下子变成了现在的通情达理、平静的愤怒。”作者自己也在小说前的“创作札记”中道出了这种风格转变的意图:“我总结自己的创作,认为以前的笔法刀刀见血句句发力,是硬桥硬马的路数,虽小有力量却整体无势;现在我追求的是太极拳一样的笔法,简中取拙,把浑圆的力量藏在整体感中,缓缓地从文本中传递出去。”
《福寿春》从世道人心的角度,以李福仁一家的生活为线索,详细地描绘了东南地区增坂村人们的生存状态、风俗人情、家长里短,在平淡的叙事中可见出作者有意识的风格转型,他在这部小说中确实在践行他所能想到的写好长篇小说的质素:“耐心、笨拙、诚实、细心”。
二、乡村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乡村描写,既有如沈从文、汪曾祺、孙犁等人的田园牧歌式的描写,在他们笔下,乡村是远离喧嚣和尘世浮华的永恒性的存在,他们如隐士一般地迷恋乡野;又有如鲁迅、路遥等人的批判式的描写,他们对乡村的传统保守、愚昧落后、僵化闭塞提出了批判式的质疑,呼唤变革,向往进步、发展;还有如周立波、柳青、孙犁等集体姿态的描写,描述了乡村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改革发展的过程,歌颂了积极追求进步的革命、变革精神。而李师江的《福寿春》中所描绘的乡村,既有田园牧歌的风格,又有对农村社会的变革隐痛的真实呈现,是牧歌式的田园写作与批判式的反思写作相结合的一次创新性的尝试。
《福寿春》,单是这个名字就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这三个字是中国传统乡村习用的寄寓人们美好希望的语词,蕴含了多少美好的祝愿!在农村,好多父母给儿女起名都会带上这三个字,比如小说中的李福仁、李兆寿、安春、二春、三春、细春等。在描写乡村生活时,小说也表现出田园牧歌式的风格。鹭鸶嫂、常氏等农村妇女的琐碎絮语,对每件“闲事”来龙去脉、细微末节的详细交代,对乡村人情世故和风俗礼节不厌其烦的描述……所有这些,都让人感到时间在这里仿佛静止了,一切似乎都不那么重要了,真正重要的是生活本身。读小说的时候,读者的思维和心境仿佛也随着作者缓慢的诉说沉静下来了。很难想象这样缓慢平实、稳扎稳打的叙事竟是出自一位70后作家之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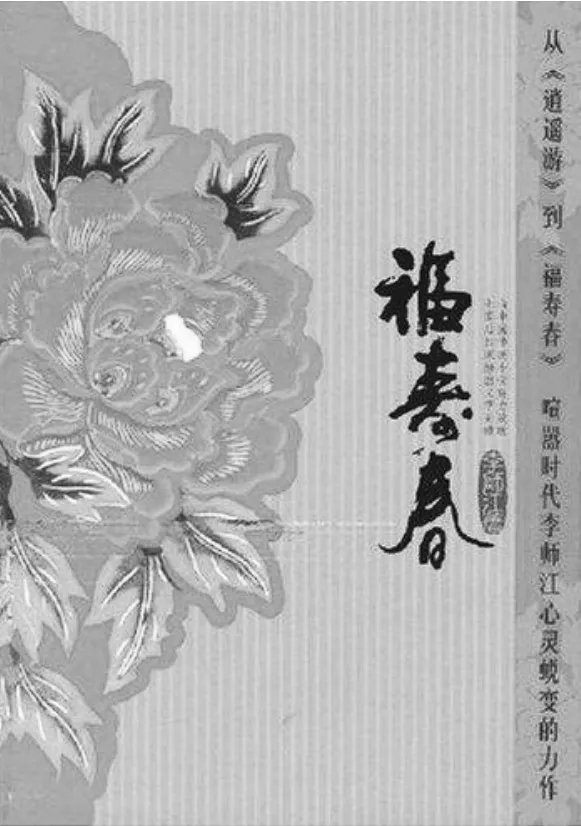
《福寿春》
但与此相对,《福寿春》“虽然写的是家常琐事,但还是曲笔涉及不少社会问题,比如三春辍学的理由是读书没有用,表明当时流行“读书无用论”,李福仁把田地卖掉后的失落和空虚,确实是时下农村的真实现状和生动写照。”增坂村安静的表面下也暗藏着汹涌的变革浪潮。乡村文明在社会发展大潮的冲击下渐趋衰落,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难以为继,陷入困境。在《福寿春》中,这种变化突出表现为父子两代人价值观等各方面的分歧和冲突。以李福仁等为代表的老一辈村民代表着传统的农村生产、生活方式,他们上山种地、下海种蛏,怀念早年吃的红苕米,对传统生产方式的衰落感到恐慌,卖掉田地后会感到茫然、无所适从。这一代纯粹的、传统的老农民终将淡出历史的舞台,而新一代的年轻农民又不满足于农村传统的生产方式,心浮气躁地想干大事、挣大钱,游走在城市边缘地带讨生活。农村的年轻一代屡屡碰壁,体现出在城乡交界处寻找出路的艰难。
三、传统
《福寿春》的整体结构借鉴了中国传统章回体小说的创作手法,以一段预言“子孙满堂,老来孤单,你的命是捡回来的,硬得很”开始叙述,带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宿命论的色彩,以李福仁住进了慈圣寺、潜心参禅向佛收尾。这很容易让人想起《红楼梦》的整体结构安排:也是以和尚的预言开头,以宝玉出家结尾。两部小说在整体上都印证了小说开头时的预言,结尾都令人感伤而又有一种超脱的平静。这恐怕不是巧合,而是《红楼梦》对李师江所产生的重大影响的一个表现。
另外,《福寿春》这个题目也极易令人想起《金瓶梅》。两部小说都是以几个人的名字为题,只不过《福寿春》是以几个男子的名字为题,而《金瓶梅》是取三个女子的名字为题。《金瓶梅》给人的感觉是富贵、高雅的,然而小说的内容却截然相反,描述了封建大家庭内部的奢侈颓靡的生活以及女人之间可怕的嫉妒和明争暗斗,揭示了其朽烂、破灭的过程,暴露了其黑暗腐朽。而《福寿春》这个名字给人的感觉是幸福美满、喜庆祥和,可是小说中人物的命运却并不像他们的名字那般幸福顺遂。乡村生活表面上看起来悠闲自在,无拘无束,但现实生活永远不可能像归隐诗文中所描绘的那样美好,农民们也还是要面对现实的种种问题。李福仁住进了寺庙里,一心拜佛,二春正当壮年却因车祸丧命。几人的悲凉结局和他们的名字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令人感到辛酸。
此外,一些语词取自明清白话,比如“且不提”、“当下”、“不在话下”,还有作者在发出感叹时所用的“噫嘻哀哉”等。这些语词的多次使用体现了作者有意识地对传统的回归,也使小说更具古典美。但与此同时,大量使用古典章回体小说的语词,在小说的现代乡村叙事语境中又会给人以违和感、不适感,使读者感到和小说整体的语境不符,难以完全融入小说的整体语境和氛围当中,有时难免让人觉得牵强、刻意。小说向传统的回归,应该做到从思想上、从内部闪回古典小说的精华和亮点,而不是只在形式上大量穿插古语词汇,把读者强行拉入古典和现代杂糅的矛盾的语境当中。
四、细碎
《福寿春》没有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也没有引人入胜的悬念设置,它所叙述的都是家长里短、柴米油盐的小事,比如种田种蛏、邻里闲谈、发生口角、做寿做会等。整部小说几乎都在絮絮地讲述日常生活中的琐事甚至闲事。作者自己也说:“此为闲事,可有可无。要说正事,却一时也想不起来,你想那农人一年,不外乎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不外乎家长里短,亲戚邻里芝麻大的口角屁事;不外乎柴米油盐,糊口生计。”正是这种细碎的叙事,成就了小说的独特魅力。
乡村是温暖的存在,淳朴的乡村人不管是对自己的家人,还是交往不多的萍水相逢的陌生人,都诚心相待,有一种人情味在。而这也正是区别于都市人的冷漠的一个突出特征。举常氏为例,她在日常的待人接物中说的话总是合情合理,同时又让人觉得温暖。她的举动也总让人觉得得体周到而又妥帖舒服,这就是因为她凡事讲究情理、心中常有他人。此外,李福仁、李兆寿、李兆立的兄弟情也令人印象深刻。小说中详细叙述了这三个患难兄弟结缘的过程:三人当年在一个生产队,性格相投,交情较好。六零年困难时期一起去堂前滩涂抓螃蟹充饥,李福仁、李兆会被民兵发现,审讯时却讲义气,都没有招出李兆寿。而二人被吊起来棍打时,李兆会为他们借了好多棉袄和棉裤穿着。后来李兆立去世得早,留下老伴儿和儿子、儿媳一起住,而儿媳对她很不孝,连饭都不让她吃,她经常要挨饿。熬不下去的时候,她甚至到李兆立坟前去哭诉,希望他能带自己一起走。李福仁和李兆寿就尽己所能接济她,虽然不能很多,却至少让她吃上了几顿饱饭。二人尽力做到多年前对兄弟的一句承诺,这种担当和诚信、这份阴阳相隔情分和义气令人唏嘘动容。作者也忍不住站出来叹道:“噫嘻哀哉!这人间至情只该属于那少数有心的人!”
可以说,《福寿春》是李师江的作品中具有独特的风格和魅力的一部长篇小说,从中我们可以看到“70后”作家李师江的逐渐成熟,同时也能读出他的一种回归的愿望和努力。这种回归可以理解为对乡村原始生存状态、对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方式、对淳朴善良人性的回归,也可以理解为对传统文学形式、艺术手法、叙事方式等的回归。这种回归的尝试可能仍显青涩稚嫩,但这种真诚的态度、切实的努力,本身就很可贵。而李师江作为“70后”作家中勇于尝试、求新求变者,相信未来会带给我们更多惊喜。
(张婧冉,武汉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