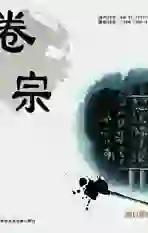法国大革命时期国家认同
2017-09-02陈征
摘 要:国家认同一向是个很难去处理与面对的问题,人与土地的关系,小到自家附近,往上而是村落、市镇、省(旺代省)、大区(罗亚尔区)、国家(法国)。认同的对象,关乎一个人所处的位置,也与历史及生活经验密不可分,还要加上其他可能影响的因素(如宗教)。在旺代,除了是地方意识与中央集权的对抗外,不外乎也是法国大革命时期,法国面临如何去定义“法国人”与各地方如 何去面对“法国”这个词在意义上的转变。
关键词:法国大革命、国家认同、旺代人
1 法国大革命后的国家认同
16世纪初法国人的概念是在法国王权下出生,父母皆为法国人,且永久居住在法国王权之下。1515年稍做改变成为:在法国出生并居住在王权之下,与父母是否为法国人无关。虽然有明确的定义,但是在资格上身为法国人,与是否有国家认同则又是不一樣的情况。因为法国人也是一种相对性的形容,就如同在旺代省,来自封特奈,相对于来自吕松;在普瓦提耶财政区,来自旺代,相对于来自双塞弗尔;来自法国,要相对的是来自法国以外的地区。
如果一个农民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他的村落,他便无法理解法国人的意涵为何,更不会认为法国人一词可以用在他的身上。法国大革命发生后,“国家”这个词出现了不一样的定义。这里面的国家,指的不是政府机关或权力机器,而是受到政府权力所支配的整个社会体系。当在巴黎的执政者忙著区分谁是爱国者时,他们就必须面对到什么是祖国与什么是国家。所以,国家与国家意识或国家认同,是在革命发生后,被政治层面的意识形态所界定的,也是做为区分自己与外敌的依据。对外,靠着延续数年的战争,明显划分法国与欧洲其他各国的差别。对内,靠著掌控整个社会体系的国家机器,建立超乎各地情感之上,对法国的认同。换句话说,国家认同是被建立起来的,是一种想像,建立在不同语言、宗教信仰、生活习惯之上,要求所有的社群都想像自己生活在同样的文化里。[1]
在旧制度末期,王室就已经希望法国是处在一个同一的王权下,但这几乎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法国各地一切都不相同,十分混乱,各地方的组成结构不同,各自有自己的法律行政机关间互不协调,也不一致,使王室束手无策。因为法国社会的状况,并不是各地方紧密依赖于中央的政体。各地方长期各自为政,名义上尊王权,但地方权力也会带给王权很大的威胁。在各地方之间,一般没有称自己为法国人,常用的词是“我们”、“我们的”,来指称自己所认同的地方、文化或生活习惯。因此,要让各地方朝向 一致化前进,是困难的,更不用说会产生一个想像中的法国。
当然,法国大革命发生后,在巴黎的执政者也立刻察觉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因此他们所做的第一步,便是区分何谓法国人与外国人,先把所有他们认为属于法国的,放在法国这个大框架下,找出一个同一性。基本上延续 1515年的法律,也把以往被排除的部分纳入,不论是抗议教派信徒、犹太人或是其他外国人,只要在王权之下守法地生活超过五年,有一定的资产,就可以是法国人。但对法国各地的居民来说,成为法国人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他们生活在这块土地上,接受王权的统治与罗马公教信仰的福音,他们享有的是普世的自然权利。而在巴黎的执政者,却处心积虑要将他们纳入一个想像的共同体中,说是要以国家力量保护他们,实际上却是在塑造自己的意识形态。[2]
当巴黎通过发布征兵法令来试探自己的统治威望时,这个保护国家的大旗,反倒引起了各地的质疑,到底是保护国家,还是保护巴黎的共和。认为是保护国家的地区,被执政当局视为对国家有认同感;而认为是保护巴黎共和者,如旺代及其周边省份,则被视为是不爱国的反叛行为,遭受出兵征讨的命运。这使得国家认同与政治上的意识形态更无法分割,成为一种“沙文主义”式的国家认同,非我即敌。表面上,布列塔尼与旺代等地的叛乱被平定之后,全法国都回归到同一个框架之下,那就是“唯一且不可分割的法兰西共和”,产生同样的国家认同。但是实际上,各地方在巴黎的压力下,却激发出更强烈的地方意识,对抗巴黎利用国家力量达到中央集权的手段。[3]看似在旺代战争后消失的旺代地方意识,便在拿破仑执政后重新浮现。这历史长远的因素,因为法国的历史,就建立在巴黎与其他地区利益冲突的历史上国家认同这个意识形态的建立,被与巴黎的中央集权划上等号,受到各地地方意识的挑战,并非等同各地方欲求独立于法国之外,而是认同的情感,不希望被远在巴黎的执政者所操控,不希望巴黎的一道命令,就要改变他们所习惯的生活方式,所认同的地方文化。不是一句简单的“为了国家”, 其实是为了共和或“国家生死存亡”,就要他们付出自己的生命。
2 旺代人的选择
法国大革命带给法国人的巨大转变,其中之一便是想像中的国家意识由巴黎传播到法国各地。旺代人同样面临到旺代人与法国人认同之间的抉择。旺代人所追求的,基本上还是与土地及生活紧密结合,由钟声文化带出的地方意识,而不是由巴黎的执政者建构的、想像的国家认同。当国民公会以征兵法案要求全法国团结一致面对外侮时,同时也是在测试自己在法国各地的影响力,观察是否自己所推出的国家认同在各地受到广泛欢迎与支持。在命令传达到旺代时,不管拒宣誓派神职人员与保王派的贵族如何在背后推波助澜,旺代人的第一反应,质疑的是为什么要为了巴黎的革命派去打仗。旺代的状况,与巴黎所期待的爱国热诚差距甚远,巴黎希望可以透过爱国心的鼓舞,来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对抗欧洲各国联军的入侵;而旺代则不希望自己成为牺牲品,去帮助远在巴黎的共和政府,以及本身就有问题的革命。旺代人起而反抗中央,表面上看似过去法国各地的农民叛乱,肇因于对社会与宗教的不满,用古老的农民叛乱型式对中央政府诉说他们的诸多抱怨。但是,这也是一个特殊地方意识的展现。社会与宗教因素并非不在 这次的反抗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只是这次的反抗,重新唤起了旺代人地方意识的强烈存在感。虽然在旺代战争后,旺代的地方意识受到强烈的压迫,不过旺代人或是支持旺代、以及在旺代战争中的领袖人物,却在海外开辟了第二战场。[4]
在法国,旺代已经被污名化,地方意识被摧残。而在海外,他们利用出版战争回忆或个人回忆录的方式,让旺代战争持续下去。在拿破仑执政后,旺代人重新拥抱自己的地方意识,更表现出他们心系旺代人的选择虽然他们愿意回到政府的统治之下,但是对于自己本身的社会文化,依旧有着对地方意识的坚持。特别是旺代的农民, 因为战争才刚过去不久,在旺代的恐怖统治又极端残酷,使他们团结起来,紧守著自己的社会文化、历史、宗教与生活经验,保护自己的地方意识,对革命怀有强烈的敌意。他们选择保护自己,还有自己的回忆。对旺代的农民来说,他们也许因为没有受过教育,而无法在历史发言权上争得一席之地,但是他们可以把旺代战争与战后统治中,他们所经历的一切,用回忆流传给子孙。这些经历,代表的是他们拒绝效忠被巴黎所建构出的国家认同,而把自己交给所生活的土地,即旺代的地方认同。
参考文献
[1]马维达尔和劳伦编:《 1787—1860年法国议会档案》第1卷,巴黎1913
[2]N.艾什顿:《1780—1804年法国的宗教和革命》,伦敦麦克米兰出版社.2000
[3]Général Beauvais.Apper?usur laguerre delaVendée. Londres: Imprimeriede Baylis,1798
[4]Martin, Jean-Clément.LaVendéeetla France.Paris: ?ditions duSeuil, 1987
[5]McDonald, Maryon.‘We Are Not French Language,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Brittany. London: Routledge,1989
作者简介
陈征(1990-),男,河南南阳,汉族,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世界史,2015级硕士在读,从事国际关系史史研究。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