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暖与百感交集的旅程(5)
2017-08-11朱伟余华
朱伟+余华
紧接着就是《活着》。《活着》的篇幅还不到12万字,大约是他写得最短的长篇。记得90年代初,我们曾在一起说到长篇小说的容量,余华的观点,长篇的篇幅,15万字内就够了,读着不累。
表面看,《活着》的结构有点笨。由一个类似他自己当年在文化馆下乡采风的身份,引出历经沧桑的老人的讲述。其实,以“我”的视角看老人,凸显了油画色彩斑驳的画面感。小说开头,“我”看到老人的脊背与牛一样黝黑,犁开的田地像“水面上掀起的波浪”,老人唱起粗哑苍老古朴的歌,正是这画面,深深感动了张艺谋。老人以一个个人名吆喝着牛,到小说结尾,你才知道,这些亲人构成了老人一生的辛酸依恋史。最后。这个家只剩下他,福贵,他买下了这头待宰杀的老牛,也称“福贵”,他们还活着。活着是进行时,老人讲述这活着的过程太凄苦了,张艺谋拍成的电影,因此而至今不能上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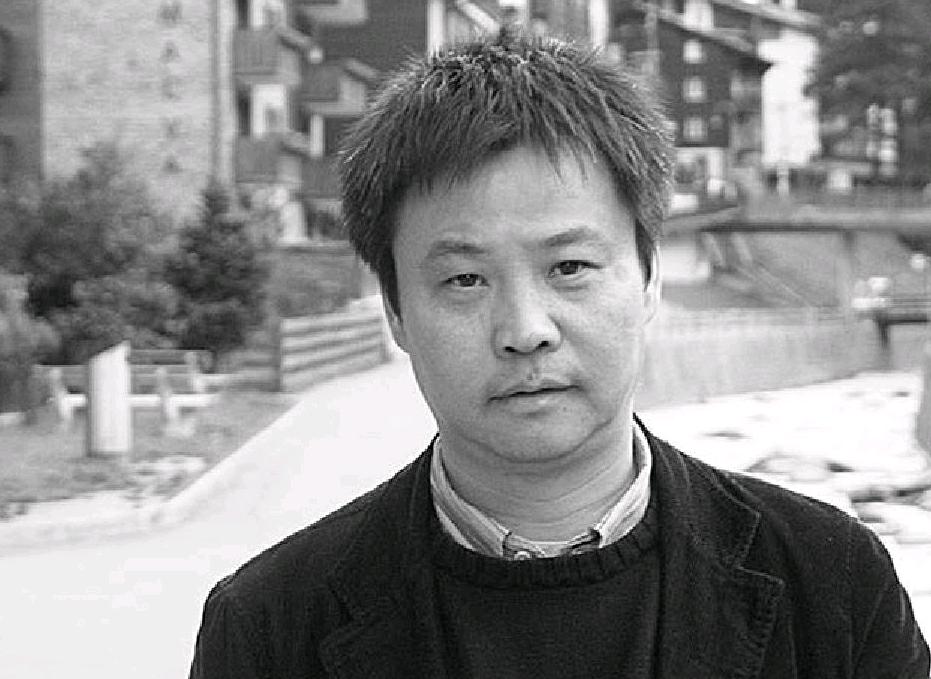
作家余华
我觉得,一个人生,真不可能遭遇不断接踵而来的那么密集的苦难。陪伴他的亲人全死了,最后只剩下他命最硬,余华把这历程极端化了。
老人讲述的解放前部分,是一个富家少爷的吃喝嫖赌败家史。余华写他的富,用了一个别致的说法:“我们走路时鞋子的声响,都像是铜钱碰来撞去的。”少爷迷上了赌,将100多亩地家产都输给了龙二,净身出户,只能成为佃户,从头做起。而进城为他娘请郎中,又被抓了壮丁,亏得能躲过战场上的子弹,成了俘虏后得以回乡。土改时,事情反过来了:亏得他把100多亩地都输了出去,使龙二成了替死鬼。这个故事很典型。我大伯解放前本也有几十亩地产的,母亲在我儿时就老说,亏得你大伯年轻时吃喝嫖赌,把这地都输给了人家。要不,一解放,他的成分就是地主。
解放前这段,有意思是用了戏谑。余华居然形容嫖妓就像水喝多了要去方便一下一样,“说白了就是撒尿”。他的小说里,没有鼓荡情欲的兴趣。他让“我”喜歡上一个胖胖的妓女,“她躺在床上一动一动时,压在上面的我就像睡在船上,在河水里摇呀摇呀”。他让“我”骑她,“骑在她身上像是骑在一匹马上”,荒淫无度。
解放后也有戏谑。人民公社炼钢铁,“福贵”老人的讲述是,到城里买回一个汽油桶。汽油桶怎么炼铁呢?在桶里灌上水煮。1958年炼钢铁是建土高炉,用烧窑的方式。余华大约没见过窑厂,亏他想出来这么个水煮的黑色幽默。水当然是煮不化废铁的,但因夜间守炉睡着了,水烧干,汽油桶爆炸,铁竟就意外炼成了。再一个黑色幽默,是悲伤的——县长的女人生孩子大出血,学校组织孩子们去献血。儿子有庆因为跑得快,排到了第一位,却因不守纪律,被拖了出来。但排队的孩子居然血型一个都对不上,只有他是对的,结果,一抽血,抽不停了,硬是把个儿子抽死了。
余华是通过一个个死,写活。解放前,家败了,“我爹”就从粪坑上掉了下来。他蹲在粪坑上出恭,原来两条腿是像“鸟爪一样有劲”的。娘病了,“我”进城请郎中被抓壮丁,回来娘已经没了,这都死得合理。解放后,三年自然灾害,媳妇家珍得了软骨病,却没死,第一个死的是只有13岁的有庆。然后,聋哑的凤霞好不容易出嫁了,找着一个憨厚老实的二喜,却难产死了。凤霞死了,家珍也死了;家珍死了,二喜夹在水泥板里,也死了。二喜死后,唯一剩下二喜的儿子苦根,竟也因为吃多了煮熟的豆子,撑死了。我总觉得余华的心硬,他能这样接二连三地写非正常死亡,贫困中的命,太脆弱。
这部长篇写得朴素。其中感人的是凤霞送人与有庆喂兔子那段。把凤霞送回去,余华先写风中“凤霞双手捏住我的袖管,一点声音也没有”,“两只小手搁在我脖子上,手很冷,一动不动”。进了城,放下她,要送走了,她“只是睁大了眼睛看我”。写有庆,一天三顿放学前割草喂兔子。成立人民公社,羊充公了,他还是每天三顿地送草,直到羊被宰杀了,他不知所措再去羊棚看,棚里已经空了。再给他买了两头,人没饭吃了,就把羊换成了粮。写得最感人的当然是家珍,她辛劳一世,送走了两个亲生的孩子,陪伴“我”走过最难的日子,最后安安静静地就走了。余华写她的最后是,“胸口的热气像是从我指缝里一点一点漏了出来”。因为这些辛酸的感人,老人陪伴着蹒跚的老牛,在夕照中絮叨一个个亲人的名字,就有了特别苍凉的感觉。这个《活着》,每读一遍,都读得伤心,也就会有趁着在世,要珍惜亲人的觉悟。
余华后来在这部小说单行本出版时写了个前言,他说,他是在听到一首史蒂芬·柯林斯·福斯特(Stephen Collins Foster,1826~1864)所作的《老黑奴》后,被这首歌深深打动,才引起了写这部长篇的冲动。这首歌是福斯特离开家乡去纽约前创作的,当时他父亲与两个兄弟都已去世,两个姐妹出嫁,另一个兄弟也去了克利夫兰,家空了。“老黑奴”是他妻子家的一个老黑奴去世的真实原型。这首歌里唱道——
“快乐童年,如今一去不复返。亲爱的朋友,都已离开家园,离开尘世,去那天上的乐园。我听见他们轻声呼唤着我,我来了,我来了。我已年老背驼,我听见他们轻声呼唤着我……”
余华说,他是从这首歌里听到一种对苦难的承受力,听到一种在承受一切中无怨无悔地活下去的态度。他说,这部小说的写作,其实改变了他对现实的敌对态度,使他意识到,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控诉或揭露,而应该展示高尚。这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人生必要走过艰难、苦痛、欢乐、悲伤,这就是活着。所以他说,他写成了一部“高尚的作品”。
余华与陈虹是写《活着》时结婚的,《活着》的解放前部分,他是请了创作假到北京写的;回到嘉兴,再写完了解放后部分。这部长篇发表在1992年第六期《收获》上,1993年陈虹作为空政文工团的创作员,分到了房子,他也就成了随军家属。这一年我下决心离开了《人民文学》,到三联书店,因为《人民文学》荒废了我整整6年生命中最宝贵的时光。到了三联书店,先是创办《爱乐》杂志,那时三联书店寄居在永定门外一家面包厂里。余华有了新家后,置办了一套音响:美国的音箱,英国的功放,飞利浦CD机,按他自己的说法,“像联合国维和部队”,然后就有了我领他去买CD的故事。那时常去的是陈立在北新桥当掌柜的那家店和小魏在新街口当掌柜的那家店。余华开始买CD是1994年,记得1994年11月我与他聊音乐,有一个对谈叫《重读柴科夫斯基》,发表在《爱乐》第四辑的柴科夫斯基专辑上。那时候他已经买了300张CD了,他说,音乐“像是炽热的阳光和凉爽的月光,或者像暴风雨似的来到我的内心”,很疯狂。(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