屯子里的生灵
2017-07-31李广智
□ 李广智
屯子里的生灵
□ 李广智
一匹马
马的路在自己的蹄下,跑得蹄疼,养马的人找来兽医,给马挂了掌,马蹄声就激荡在路上,马脖子下的铃铛也会轻音缭绕在屯子的上空。
屯子里拴过两挂马车。一挂是二姑父家的,一挂是舅舅家的。他们之前是生产队。生产队是否拴过马车,我不清楚,但肯定是有的。一个生产队虽然只有几十户人家,可也一样要有新媳妇要送,盖房子的石头要拉,地里的收成要运,人干不动的事情,很多都要由马来完成的。当年的生产队饲养院就在屯子的中心地带,独门独院的大院套,养着全屯子的大牲畜,那些牛、马、骡子、驴承担着全屯子的重劳力。耕地、驮粪、拉车,人把这些重活计都推给它们,人当它们的下手,牛拉不动犁了,人在一边帮着拉;骡马拉不动车了,人在后面推,前面拽,和它们一样流汗。汗水滴滴嗒嗒地落在屯子的地上,渗入土里。牲畜和人的汗味被风一卷一卷地送到屯子的每一处角落,也会被送到屯子以外的地方。只是不知道那时,是人把自己当成牲畜,还是牲畜不自己当成了人。
我不清楚,屯子为啥很多年月里只养一匹马。马孤独地站立或行走,往左看是牛,往右看是驴,往前看是驴,往后看是骡子。牛、驴或者骡子,每天看着这一匹马。一个孤独的异类。每天和它们吃着同样的草料,在河边饮着同样的河水。我问过舅舅和二姑父,屯子里养的是一匹母马,母马温驯,好经管,要是养一匹大儿马子,不知道舅舅和二姑父的鞭子是否能降得住一匹发情的公马。也许屯子里的人们谁都心里没个底,就放弃了这个想法。这让屯子一直没能养起几匹马。屯子里的牛生下小牛犊,驴生下小驴驹。马不生马驹,屯子里没有公马,只有发情的大叫驴。大叫驴显出硕大的性器,尽情追逐着母马,努力繁衍着自己的后代。只是这个后代是头杂种,一头骡子。马努力地哺育着自己的子女,心疼地看着一个和自己完全不一样的家伙,不知是何感想,那逐渐长大的小骡子呢。
一匹马肯定孤独的活在屯子里,像某些人的内心。我知道,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一匹马独自在屯子里吃草喝水,独自看月亮升起,独自奔跑。屯子里的驴、骡子、牛、马,每年都有脱缰的时候。一头脱缰的马要是奔跑起来,人追不上,马用不上多长时间就把人远远地拉在后面,然后慢悠悠地在前面走,看见草顺便吃上几口,顺便朝后面看上几眼,等人走近了,再撒开蹄子继续跑,满屯子到处都是喊捉马的人。马,一匹孤独的奔跑者,有时会让捉马的声音引爆数个屯子。我家的院子多年没有院门,甚至没有一只厉害的狗。马,也许更多的时候是一头驴或者骡子,就肆无忌惮地跑进我家院子转上一圈,看见无路可逃,又原路从“院门”返回。我在院子里不止一次地撞见一头骡子或驴迎面跑进院子,然后折返出院子。要是有院门,或者有一只厉害的狗都可以拦住一匹跑缰的驴或骡子。
我在很多年月里,没能遇见一匹脱缰的马。碰见最多的,是放马的人和马一前一后的走在路上。我和人打招呼时,马也边走边愣愣地看上我一眼,大概算是和我打招呼,然后继续走马的路。有时,马在前面走,有时人在前面走。其实,谁也走不到谁的前面去。到了有草的地方,马停下来吃草,人蹲下来割草,一样长的路程。等马吃饱了,人割完草,扛在肩上,仍旧一前一后的走。路上,只听到人和马走路的声音。人走上一小段路,喘息的声音有些沉,可盖不住马的声音,那喘息声也一前一后、一轻一重的响在路上。
一匹马是不是计较自己的孤独,只有马自己心里清楚。屯子里有几头牛,数头骡子,还有几头驴,它们和人努力包揽下屯子里全部的活计,这让喂养的人认为一匹马就够了。马从屯头走到屯尾,可以让刚入世的屯人认识认识一匹马。要是连一匹马都不认识,出了屯子,在路上碰见,那怕是被人笑话。有几年,屯子就在没马的年份里偷偷过了几年,有个叫胡军的屯人从外地特意买来一匹马,在屯子里转了无数圈,仍然无法释怀。最后,买来一部相机,牵着马到处找人合影。足足走了两年,大概附近屯子内外的人都认识马了,他觉得找人和马合影的生意不好做了,原样找人把马牵走了。随后,胡军也走了,再不住在屯子里。
现在,屯子里连养得最多的驴也没剩下几头了。屯子里再没出现一匹马。有时,我努力到达屯子以外更远的屯子,偶尔碰见一匹马,我都会努力辨认着马的全身每个细节,试图寻找一匹马的踪迹,可马最多抬抬头,多看我几眼,这让我觉得它和赶马的人一样,彼此更像个陌生人。
羊儿都上山了
羊儿像白云一样游荡在屯子的山上是很多年前的事了,村子一下了禁牧令,白云一样的羊群就再没飘过屯子。每当白云飘过屯子,我看见屯人看着白云有些呆,我说想羊群了,那个人略带忧伤的点点头。
现在,刘家老二和二表哥投了巨资,把屯子西边两个低矮的山头各自推平一块建起了数排羊舍的养殖场,用铁丝网远远地围了一大圈,顶上屯人十数个院落的面积,又从远处用大汽车买来了新种羊,肯定是想在山上自家的养殖场大干一番事业的。
我到过二表哥家的养殖场几次。一进场门,便听见场内远远的几排羊舍内传出羊儿“咩咩”地叫声,不知道那叫声是羊儿想告诉二表哥关于草料的事儿,还是想走出羊舍透透风、散散步的事儿。我在屯子里生活了那么多年,一种动物的语言都没听懂,羊儿冲我咩再多声都是白浪费感情。我听不懂羊儿的客套话,亦或体己话,为羊办不成一件事。办成一件事,也是二表哥为它们开门透风,填料加水受累,我只有干瞧着的份儿,伸不上手。羊儿和我们一样,有时候也会干些“有病乱投医”的糊涂事。
我家多年前没禁牧时也没养过羊。屯子里好像只有一户杨姓和刘姓的人家养过羊。小时候腿勤,喜欢满屯子的跑风,碰见羊儿的次数肯定不比碰见一条蛇的次数少,我确信碰见三百次以上的蛇。黄的、青的、黑的,很多种颜色,只有羊儿是白的,就算头上带点黑点,也是白的,屯子里没养过黑羊。黑羊太黑,到了晚上更黑,黑成那样,孩子晚上看见了发瘆,胆小的人家不敢养。
屯子的南边有大片的庄稼地,有山,山上有松树和荆条,我可以到山上采蘑菇,割柴,亦或搂柴,灶坑门供不上了,再大的理由都抵不过肚子的理由。没了打柴的理由,随便一个谎言,都会让我在屯子南边转上半日。偏巧那养羊的两户人家都在屯子的南边一角,两家的羊一出院门,就突突拉拉地就近跑上山坡低头吃草,从不越过屯子跑西边的山上转一圈。那样,羊吃草的路就远了,羊的嘴肯定等不了。羊儿不像一头驴,撒个欢就把半个屯子的路跑没了。羊撒几个欢儿也跑不远。或许羊儿嘴急,我们都有嘴急挨烫的时候,羊也一样。羊儿不想在路上嘴儿白白的闲了,一路吃着,自然就近地跑到南边,南边山上就星星点点撒下白。有时,邻村的羊也会翻过山顶,越界到山这边撒几朵白云。那个村子的羊群大,羊群在山顶一朵朵的移动。地里干活累的人,闲眼了就看山上那白,看着看着,泥塑般入了神,忘了手里的活计,定是心里有了个美美的想法,不觉失了态。失了态,也没人究,自己是地的主人,谁看了也管不着,兴许那个人也这般失了态,眼里满是艳羡的。
我在屯子里,遇见多少次羊肯定记不清了。遇见羊,和屯子里遇见一头牛、一个人没啥区别。我和人打声招呼,羊儿肯定也和我互相看了一眼,有几只羊还“咩”地回应了一下,我无法断定羊儿是在自言自语,还是同样和我打着招呼。我回头看羊时,有羊儿也同样停下脚步,回头瞧了我几眼。我和羊儿生活在一块土地上,彼此生活在各自的世界,我们辛辛苦苦打下的粮食,放进锅里煮熟后,就成为了我们的食物,伸手一扬,落在羊的脚下,就成了羊儿或鸡的美餐。我们一生都在试图和院子里的动物拉开距离,可一辈子或者几辈子都生活在一个屋檐下。
我一出门,便看见二表哥家大大的养殖场成排的羊舍暴露在阳光之下,每跑出一只羊,都被我远远的看见。在“山上”,羊儿有了自己的地盘。人和羊远远地看着,再不会走个对过,羊儿往左闪闪身子,让人先走过去;或者,人往右边靠靠,让羊儿先走段路。羊儿驮着满身的膻味儿,羊给人让道儿,人给羊让道儿,都会飘进人的鼻子。要是飘进羊自己的鼻子,和人也没啥大关系,那是羊自己的事,它吸进自己的味道是个啥滋味,人管不着。要是在吃草的地方碰见,散开点点白的羊群里,会冷不丁跳出一只孤单的羊羔追着你,孤单地“咩咩”呼喊着,羊羔啃了几口草芽,想起羊妈妈母乳的味道儿,忍不住,到处追“妈妈”,然后跑开。人看了,忍不住笑出声,定是想起了自己小时候。
半只猫
有几年,老鼠好像相中了我家的粮食,总是想尽办法,剜门盗洞地钻进我家祸害粮食。我们都和母亲商量,家里该养只猫,除除鼠害。母亲说猫是奸臣,养不住,不养。
二姐和我家住在一个屯子,每隔几趟房,走动的就近。二姐就对母亲说:三姨,把我家的猫抱走,你家先养着,等耗子抓净了,再还给我。不算你家养的数。我们觉得这个办法好,都同意了。母亲也觉得这个办法不错。
猫是母亲取回来的,还是二姐送过来的,记不住了。我放学进屋,一只大花猫冲着我“喵喵”地吼叫,我猛地跺跺脚,向猫发出了更厉害的样儿,猫拉开架势,弓着腰,开始想和我叫叫板。我没动,继续跺了几脚,猫大概觉得我这个庞然大物不好对付,又厉害了几声,突然收回身子,转身跑掉。它知道我不好对付,可能也讨不到啥便宜,自讨没趣地去玩了。除了吃饭和睡觉,我好像看不出猫在干啥,猫被抱进屋子,肯定把屋子转了个遍,用眼睛看,鼻子闻,耳朵听,把整个屋子摸透个遍,然后找个闲地儿,把眼睛闭了,也许它想这样休息一会儿,养养神儿,咱足了劲,好全力抓捕屋子里的每一只老鼠。
老鼠不知道猫已经搬进屋子。还和往常一样在屋子里的暗处肆意奔跑。它还和每天一样从老鼠洞里钻出来,闻到粮食的香味,听到人的脚步声、说话声,知道人还和往常一样不会对它有啥威胁,索性迈开正步,也许一溜小跑,直奔装粮食的口袋和柜子,却没有警觉屋子里蹲着一只庞然大物,已经在它出没的路上守候多时,正用耳朵听着,眼睛偷偷瞄着,老鼠一露头,猫的耳朵大概已听得仔细,迅速悄无声息地调整好捕猎的姿势。等到老鼠到达捕猎范围,一个饿虎扑食,已把老鼠按于爪下,老鼠一阵凄惨的哀叫,扑棱扑棱挣扎了几下,就没了声息。过了一会儿,猫舔着嘴唇,伸着懒腰,悠闲地回到我们身边。
猫回到我们身边时,我们刚刚盛好饭,端起饭碗,准备喂饱肚子。猫看见我们,“喵喵”地叫了两声,像是要和我们请功。猫初战告捷,大家高兴,有人在桌上夹了一块好吃的,算是给猫的奖励,猫看了看,又“喵”地一声,好像告诉我们已经酒足饭饱,和夹东西的人表示感谢,然后把脸扭向一边,卧在炕上,不再理识我们。我们相视一笑,有人说这猫啊。
猫在我家有老鼠抓,我家大人、小人为了让猫留下来,也下了些功夫,用好吃的贿赂。没几天,猫就变了节,不往回跑,安心地在我家居住下来。母亲就说,你看这猫,养不住吧。父亲宽慰道,养不住就养不住呗,又不指着养,人还有养不住的呢,有奶便是娘的多了,何况一个哑巴牲口啊?母亲再无话可说。
生产队刚分地时,屯子里的大牲畜不够分,也是按着三户一头牛、两户一头驴,还不够分,用牛槽顶数。抓阄时,爷爷啥牲畜都没抓到,最后只好抬回家一个石头大牛槽,是不是还分着别的啥东西,我不知道。那时我还小,即便跟着大人转上一圈,也屁事不懂。分到的,肯定高兴,没分到的,心里馋。老李家没牛、没驴,种地只好出去借,牛是老刘家和老秦家的。只好先找刘家,再找秦家,两家都同意了,牛牵走。有一家同意,另一家不同意的,同意的人家找不同意的人家商量好了,不同意的出来拿话。你看这事闹的,你二哥不知道事情有变,就把这事给拒了,让我回家好一顿数落,也不看看哪近哪远,他兄弟用牛尽管到院里去牵,别耽误了正事。共养的牛、驴,两家轮流喂。干活时,串换着使,不让牛、驴闲着。
二姐家的猫不一样,猫归二姐家所有,我家需要猫抓老鼠时,让猫住进我家,猫也由我家喂养。即使猫不抓老鼠,也可以住我家,我家不需要了,随时把猫原样送回。猫肯定不管这些,在我家抓没了老鼠,可能觉得住腻了,就返回家住上些日子,偶尔在溜回我家。母亲觉得这猫对我家有功,就好声喂养了。
我们全家都恨老鼠糟蹋了粮食,老鼠从地里就开始和我们抢粮食。我们一户一户地铺展开来,在屯子里选个合适的地方建房子。老鼠如何建的洞穴,老鼠与老鼠间会不会来往,它们是否和我们一样,有些邻居永远都不来往,或者和农村一样把邻居住成一家人般亲,我们都不清楚。我们在地里辛苦的种庄稼,秋天去到地里往回收粮食,却发现有些粮食已被老鼠抢先下手。我们看见地里存在的鼠洞,着急往家收粮食,无暇顾及,只好任由老鼠留在大田、漫地里,逍遥自由。粮食运到场院,运到屋子,老鼠很快也把家安了下来。我们不清楚老鼠咋这么快就跟了过来,安家过日子,繁育后代。我们也认不清那是田里的老鼠,还是新迁进来的一窝老鼠。老鼠是追着粮食放牧一样生活的,还是把家一直安在粮食经过的地方,等着我们把粮食运到嘴边,突然大开洞门,着急储备粮食,然后再重新封闭洞口,在地下安全生活。我们在地上以为老鼠全都消失,到别的地方打洞了,却全然不知老鼠偷偷在我们眼皮底下,把自己隐藏在地下安居乐业继续和我们抢粮食。老鼠肯定没想到我们把它的死敌放进屋子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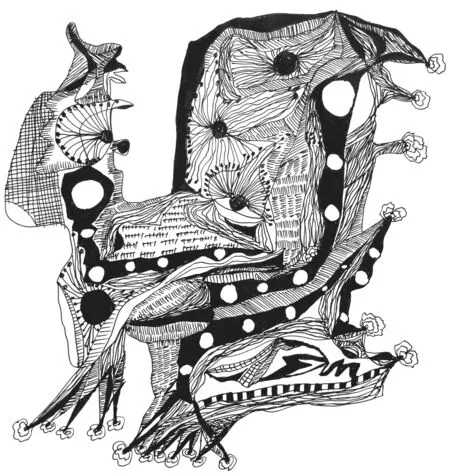
猫一下子打破了老鼠的计划。爬出洞口的老鼠被猫一只只逮住,再吃掉。我再不用担心老鼠在睡觉时,偷偷跑到我的枕边,把我,也许是枕头当成晚餐了。也不用蒙上被,躲避老鼠整夜地啃咬声了。二姐家的猫在消失一段日子后,就会倦卧在我和家人的身边,呼噜呼噜地睡得香。猫在它的生命里,会把这里当作它的家吗?我们时常把居住的地方称作故乡,猫也会这么做吗?
被抱走的那条狗
我出了屯子,乘上客车,打算离开屯子到屯子以外的一个地方。我在屯子里时常做着这样一个梦,一次次地走出屯子。
一个人用纸壳箱装着一条黑色小狗上了车。看得出,他打算从养狗的人家抱走纸箱里的小黑狗,带回家养。
抱狗的人很舒坦地把装狗的纸箱放在我脚边,如释重负地坐正身子,像完成一件重要的活计。我把目光收回到纸箱上,一条小黑狗伸出脑袋,小黑眼睛明亮的,好奇、无助,夹杂着数个表情地看着我。它肯定想用眼神告诉我点啥,是让我放了它,还是原路返回,我没看懂,完全不懂狗的意思。也许,它啥都没想,只是用眼神和我打个招呼,怀着和我同样的心情,想到另一个地方看看。小黑狗是不是在一场眼神的对视里,也看懂了我的无奈。
自从爷爷被狗咬去世后,我很多年没正眼看过一条狗,像现在这样近距离的。我很久都不想接近一条狗。如果狗试图接近我,我通常会捡起一块石头招呼它,我憎恨那条夺走爷爷生命的疯狗,是它让健硕的爷爷离开了我。我把对一条狗的仇恨转嫁给了所有的狗。尽管那条狗早已被人处理,受到应有的惩罚,可我一直不肯放下对狗的仇恨。我们其实一直捡起生活中的一些事情,困住自己,死死不肯放下。多年前,一只啄叨我的大红公鸡,照我的腿上狠狠地拧了一口,当初在皮肤上留下的痕迹,早已退回原样,再找不出伤痕,可在心里的疼痛时常提醒着我。我明明知道大红公鸡早已成为父亲的下酒菜,再不会有一只公鸡敢追我。我们却不肯放下。不知道多年前,我们踢打的一头猪、一条狗、一头牛、一头驴作何感想,它们也会这样记住我们吗?
小黑狗一直试图从纸箱中跑出来。抱狗人一次次地把小黑狗的头按回纸箱,把它抓回纸箱。干脆把纸箱抠个窟窿,把纸箱紧紧地按住,小黑狗好像很不服输地照旧从封口处挤出嘴巴,挤出整个头部,露出明亮的眼睛,努力挣扎着环视每个乘车人,仿佛要记住每个面孔。它是不是想记住每张面孔,准备等到长大了,瞅准机会狠狠地咬上我们一口。我们为了让一头驴多跑上几圈,把一块黑布蒙在驴眼睛上,让驴没有尽头的围着一盘磨或者一盘碾子走个不停。也许闲慢,又在驴身上踢上一脚,打过一鞭子。我们没注意,以后的日子里,那头驴在角落里,用眼神狠狠地瞪我们,它们不能像狗一样咬上谁一口,踢谁一脚也不容易。人在驴这样的大动物跟前,总是小心翼翼。驴很少有越轨的机会,可狗不一样,狗在我们眼皮底下,稍不留心,狗就可以达成愿望。
小黑狗倔强的钻出纸箱,然后被抓住摁进纸箱。抱狗人一直不想让狗钻出来,每次都让小黑狗钻出纸箱的计划泡汤。小黑狗甚至敌不过人的一条手臂,它力气太小了,把头刚刚从纸箱缝隙钻出来,使劲地转动一下,用眼睛看看四周,都是我们这些乘车的人。它肯定再次感到自己的孤单,它都不肯哼一声。我家之前也养过好几条狗,对狗还算了解。小黑狗大概以为车上的人多,也没有大狗在身边,即使它向我们弄出些声音,也讨不到便宜。索性装聋作哑,不和人计较。
车走到半路时,抱狗人把小黑狗带下车。小黑狗努力挣扎着,再次露出脑袋,用一种无助的眼神看着我们这些乘车人。我们为了生活背井离乡时,也是这般眼神吗?我们抬抬腿,就上了一辆车,离开家乡,或者返回家乡,小黑狗肯定不能和我们一样,它抬抬腿,也跑不上多少里路。我突然想起,小黑狗努力地挣扎着露出眼睛,是不是想透过车窗,记住来时的路,它也想有一天返回自己的家乡,我们却狠心断了一条狗回家的念想。
小黑狗被抱到哪里我不清楚,可我肯定,小黑狗也许再也回不到他的家乡。我努力地向车窗外看着,我是不是也想记住窗外的风景,我确信我一定会返回家乡。
老马家的鸡
老马家住在屯子的西北一条沟里,我们习惯上称作老马家沟里。自然,老马家的鸡也生活在老马家沟里,和屯中的鸡少有往来。
少有往来的意思不是没有往来。老马家住在山根沟沿,地势颇高。老马家的鸡一出院门,便看见大半个屯子,要不是沟的另一面地势也不低,都能看见全屯子。这样的地势,让通往老马家的道路没修宽,进不得大车,进得大车也没用,老马家沟里除了几户人家的几块农田,别无他物,这让不愿劳累的屯人少有涉足。
平日里,老马家的鸡出得院门,迈开两条细长的鸡腿,往坡下看看,有几只鸡在平坦的漫地觅食,撒欢游戏的眼热,也想凑下热闹,没往下迈几步,鸡肯定和人一样感觉腿有些闯,继续往前跑,每一腿下去,腿都像迈进深坑,触得骨头疼,不敢继续往下跑,收了身子往回走。下面的鸡多半也看见了,诚心欢迎个新伴儿,飞腿想往上迎,没跑几步,看对方往回走,也失了兴,不做理会。老马家的鸡再看见坡下屯子里的鸡,用翅膀拍拍还有些疼的细腿,只好相互望上一眼,各行其是。偶有老马家的鸡和屯子里的鸡不嫌累,终于跑到一起,还没在一起磨合好,尽兴做一件鸡的事,便匆匆分手。
一年秋天的某一天,我领着女儿到老马家沟里去采菇娘儿。经过老马家门前,几只鸡闲散在他家院外树下,刨食、打盹,亦或奔跑在树间做鸡的事。看见我们走近了,齐齐的伸长脖子,瞪大了眼睛,有两只甚至还发出短促的鸡叫,好像是给同伴发出的警报,有人侵犯了它们的领地。也许是告诉我们,这是它们的地盘,看见我们好像没啥威胁,才收回脖子,继续忙鸡的事。
我也收回目光,指着鸡问四岁的女儿:“看,那是啥?”
只在卡片和电视上见过鸡的女儿说:“鸡啊。爸爸!这个我认识,可奶奶家为啥没有啊?”
女儿把问题又踢给了我。我告诉女儿:“奶奶家之前也有很多鸡的,只是都病死了,所以没有了。”
我以为女儿肯定会和以往一样继续问我鸡为啥病死了啊。女儿看了看我,又看了看鸡,似有所悟地“哦”了一声,算是表达我回答问题的一个表态。
其实,几年前,或者说更早的年份里,屯子每一户人家都养着一群鸡,等鸡老了,再换一茬,一直往下养,不会停顿下来。后来,有两年,一场又一场的瘟疫总是围着鸡转。村子里也下来人动员不让散养鸡,鸡就逐渐在屯子里消失了踪迹。
我不清楚老马家是如何让几只鸡能够生存下来的。我问过母亲,母亲说屯子里的鸡都没了。然后我到屯子的四处转了两圈,鸡真的少了踪迹。之前,鸡在屯子里到处闲逛,它们迈着鸡步,房前屋后,到处印满脚印,仿佛满屯子都是它们经营的土地。我家的一茬鸡甚至不知何时,不爱住在自己的鸡窝里,每晚悄悄飞蹦上井边的一棵矮桃树树枝上。鸡不想过我们为它们安排好的生活,自己做主选择了在桃树上,谁也猜不出为啥。那些鸡,起先是一只,后来是两只,再后来,鸡窝里半数的鸡都加入到桃树上。黑夜里,黑压压的压满了桃树枝,有时咯的一声,不知闲挤了,还是在夜里看见啥东西,让它们发出那样的声音。兴许是先前的一只鸡,自己待在树上没意思,找了窝里的一只鸡,讲好晚上你和我去树上睡,我白天和你玩,还给你捉几条虫子吃,后面的鸡觉得合适,便答应了,一直争取到再没一只鸡肯答应这个条件才作罢。鸡窝里的鸡为此分成了两派,留在鸡窝里的鸡看见鸡窝腾得又宽又大,再不想让出去的鸡返回鸡窝,用话激出去的鸡,出去的鸡只好不论刮风下雨地窝在树上。
老马家的鸡是不是也住在树上,我没在老马家住过,黑天时看不见鸡是不是钻进鸡窝里,还是也和我家的鸡一样站在树上过夜。白天里,所有的鸡跑出老马家的院子,在坡上看满屯子再跑不出几只鸡影,不知老马家的鸡会想些啥。现在,地里种下再多的种子,我也不担心鸡会跑进地里刨食了,甚至连菜园子的墙头帽儿也不用扎了。我家院内的菜园子好几年没扎圪针了,小侄儿不走菜园门,像小鸡一样一下从墙头帽儿直接蹦进菜园子。其实,抹墙头帽儿是件累人的活计,扎墙头帽儿是件扎人的活计,这些都因为院子里没有了鸡,省下了。
老马家肯定和屯子里没有养鸡的人家不一样。因为几只鸡,他们还会抹墙、扎圪针,凭空往地里多跑数个来回,多喊上无数嗓子的力气,这些是鸡带给老马家的活计。鸡会下无数只红皮、白皮鸡蛋报答老马家。老马家可以和很多年前的奶奶一样,从鸡窝里拿起一只刚下的,还温热着的鸡蛋,顺手一磕,从露眼儿出吸溜吸溜吸干蛋清和蛋黄。全屯子没有鸡的人家只好咽着唾沫,想一想鸡的好处了。
偶尔,我会听见老马家的鸡传来若隐若现的打鸣声,那是屯子祖辈听惯了声音。现在,它让老马家独享了。一屯子会不会有几个失眠的人。
李广智,1974年生。辽宁省作协第七届签约作家、葫芦岛市文联签约作家,有散文被《散文选刊》《读者•乡土人文版》《中华活页文选》等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