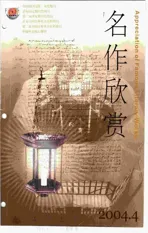“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巾”
——读周国平《人性的哲学探讨》
2017-07-13北京启之
北京 启之
“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巾”——读周国平《人性的哲学探讨》
北京 启之
周国平以散文闻世,“男看王小波,女读周国平”是20世纪90年代大学里的一道风景。王小波的小说跨越古今,奇思异构,叛逆在骨。周国平的散文情浓意永,文美理深,哲思入心。我问清华的研究生,为什么周国平的散文打动人心?这些“80后”的学生居然很少有人知道,周国平吃的是哲学饭,更没有人知道,他曾经对人性有专门的研究。我建议他们读一读周国平的硕士论文,刚刚问世的《人性的哲学探讨》,学生们大叫其苦——太哲学太艰深了,周老师太奇葩了,还能写出这种书!
学生的抱怨,反衬出周先生的高明——幸亏他今天才推出这本书,要是20世纪90年代出了,恐怕“女读周国平”就会变成“人畏周国平”。
这本书确实缺乏可读性,个中原因,一在时代,二在内容。此书写于1981年,那时候,整个中国刚刚从“文必假大空”的语境中挣扎出来,即使跑在前面的周国平也难免要带些旧时代的痕迹。对此他深感惭愧。他给这本书开列的三大缺点之一就是“文风干涩。有太多的引经据典,太多的逻辑推理,因此在现在的我看来,仍是有太多的废话”。
对此,他做了如下的解释:“也许可以把这些缺点看作那个时代刻下的痕迹。改革开放之初,由于长期的文化禁锢,一方面,西方古典哲学著作的译本还相当少,更不用说现当代的了。一个显著的例子是,我当时对尼采的了解仅限于读到某些书本中摘译或引用的片断。另一方面,在国内理论界——当时就是这么称呼的,这是一个恰当的名称,那时候的确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占据着主流地位。我虽然有意要从这种理解中突围,为此不得不大量引证原著来为我的观点辩护,但实际上也就受着当时那种话语模式的支配,即设定一个绝对真理,把它当作不容置疑的终审法官。”
翻翻20世纪80年代初的《新华文摘》,你就会知道,周国平不是在为自己辩解,而是在倾诉苦衷。从他个人的痛苦中,我们可以窥见,文化封闭和思想僵化给学术研究带来的创深巨痛。那些讥讽周国平“奇葩”的“80后”不会想到,在写这本书时,作者首先要当“搓澡工”,把那些被弄得面目全非的基本概念扔进学科的硫酸池里,洗去它们身上的锈迹霉斑。然后,他还必须拿出“清洁工”的手段,用水龙头、铁扫帚清除淤积在思想界多年的污泥浊水,而这种清淤除垢的工作,又只能靠引经据典来支撑,用主流允许的学术语言来阐释。天下是否有什么学术超人、文章高手能在这种困境中,把“哲学中的人性概念”“人性观的基本类型”“人的活动和人性”“人的生物性和社会性”,以及人性理论方法论等内容写出可读性,而文风活泼,不说“太多的废话”,我深表怀疑。
周国平关于人性的研究,让我想起了好多共和国的往事。
1963年,南京师范附小教师斯霞提出“母爱教育”,认为“儿童不但需要老师的爱,还需要母爱” 。教师应该“像一个辛勤的园丁”“给我们的幼苗带来温暖的阳光和甘甜的雨露” 。斯霞的这一教育思想很快得到了同仁和家长的拥戴,呼应的文字飞向各种媒体。然而《人民日报》的赞美之声未歇,《人民教育》的批判之声蜂起:斯霞的“母爱教育”就是资产阶级的“爱的教育”,它抹杀了教育的阶级性,把教育为无产阶级服务变成了为资产阶级服务。“对学生应该实施马列主义的爱憎教育,而不是人道主义的母爱教育。”不要引导孩子陷在“人性爱的污泥之中” 。让孩子们为“小白兔的病痛而流出同情的眼泪”,就会软化他们对剥削阶级的斗争。一时间,斯霞成了“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宣传者。极“左”战士以笔为枪,将“母爱教育”打倒在地,又踏上一万只脚。
这是一个信号弹,随之而来的是对电影的讨伐。苏联电影《第四十一个》《雁南飞》《士兵之歌》……宣扬“人性论”被打入冷宫,国产影片《林家铺子》《北国江南》《舞台姐妹》《早春二月》……宣传人道、人情片成了毒草。文学即人学,文艺作品离不开关于人性的描写。绝大部分文艺作品都面临着灭顶之灾。
这股风刮进了课堂,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师生们遇到了一个难题:如果一人落水,救还是不救?同学们分成两派,一派是“施救派”,一派是“调查派”。调查什么呢?调查落水者的阶级出身。“施救派”发问,等调查出了结果,那落水者不就淹死了吗?“调查派”反问:如果你救起的是地主,是反革命,你不是帮助了阶级敌人了吗?“施救派”败下阵来。
在“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语境中,这股风肯定会吹到北京大学的课堂里。正在哲学系上本科的周国平会做何感想?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可以确信的是,凡是有理性的、有常识的人都会反感于这种极端,怀疑于这种极“左”。而正是这种反感和怀疑,奠定了20世纪80年代哲学界清理人性论的思想基础。
“文革”来了,江青点名枪毙了几十部毒草影片,人性人情人道成了最大的罪名——《五更寒》“充满了人性论”;《革命家庭》“充满了人情味”;《柳堡的故事》“谈情说爱,低级趣味”……
人性、人道、人情是与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连在一起的。无数的人为它丧失了人性,无数的人成了牛鬼蛇神。如果你问那些穿着旧军装,腰扎武装带的少男少女为什么打人?他们会理直气壮地告诉你,他们打的是阶级敌人——敌人不是人。
这种谬论,首先来自中国的理论界。
三十四年后,周国平在这本书的前言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在中国当时的理论界,只要谈到人性,人们就必定搬出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论断,据此把人性归结为社会性,又搬出毛泽东关于阶级社会里一切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的论断,据此进而把社会性归结为阶级性。一种普遍的论调是说,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性是唯一具体的人性,除去阶级性就只剩下了抽象的人性,甚至只剩下了动物性。当真有人质问:如果抽掉了性爱、母爱的阶级属性,人与动物在这些事情上还有什么本质区别?这等于是说,在做爱或哺乳时,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便是怀着阶级感情做这些事的。如此可笑的论点,却是出自当时的理论权威之笔下。”
虽然周国平笔下留情,对这位理论权威的理论点到为止。但是其“唯阶级性”之荒谬可笑,足以令人演绎出这样的推理——若男女双方都满怀着无产阶级的感情去做爱,性趣会因其感情之高洁而得到提升;若有一方感情的纯度有所缺欠,那么其性趣则会下降以至消弥。值得一提的是,在那荒诞的岁月里,这一荒谬的理论竟然不乏实践者。
饶瑞农先生给我们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李师傅本来是厂里数一数二的技术骨干,只因他在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三省时当过几天日语翻译,“文革”一来,就成了“历史反革命”。入狱过堂,审问判刑,自不必说。好在他靠拢政府,积极改造,熬到了刑满。当时的政策是刑满之后留厂就业,李师傅留下来,施展他的钳工手艺。不久,他在当地农村找了个贫下中农的对象。按规定,留厂就业人员每周有假日一天。因此,这李师傅每逢周末必喜滋滋地回家。不幸的是,“批林批孔”之际,这李师傅到了该回家的时候,突然从以前的喜形于色变成了长吁短叹。原来他老婆要离婚。为什么呢?好事者一打听,才知道端底——李师傅每次回家,必先向女方汇报学毛著之心得,批林批孔之体会。而其妻对这番汇报不胜其烦,忍无可忍,提出离婚。满怀无产阶级感情的李师傅大为震怒,理直气壮地找厂里,要求领导出面调解。没想到厂领导在这事上,毫无兴无灭资的觉悟。李师傅碰了一鼻子灰,只好忍痛离了。(饶瑞农:《走出恐惧——“九一三”事件40年祭》,载《记忆》第75期)
其实,在那位理论权威看来,既然人类社会只有阶级性,没有共同的人性,那么包括饮食男女在内的人之欲望,就都应该归属于不同的阶级。而李师傅早就应该与那位没有正确的“做爱观”的女人分道扬镳。李师傅请领导调解,是无产阶级立场不坚定的表现。
周国平以人性作为论文的题目,显然是有感而发,他要纠正广泛的误解,还人性的本来面目。为此,他在书中着重阐述了三个论点。“第一,人性的完整性。人性是在人的活动中形成的人所特有且共有的生物属性、心智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综合体。第二,人的社会性的丰富内涵。从横向看,同时代的社会关系不但有阶级,而且有民族、国家、职业、家庭,等等,它们都有阶级所不能取代的特殊内涵,在人身上形成相应的社会规定性……从纵向看,还存在着历史继承的社会关系,即个人同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文化的接触和对它们的接受。第三,自由活动是人的本质。人的活动区别于动物的生命活动的本质特征是自由,即以活动本身也就是能力的运用和发展本身为目的和最高享受。在此意义上,可以把自由活动规定为人的真正本质,它是人的价值和使命之所在,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目标。最大限度地保证一切个人自由发展其能力的社会,才是合乎人的本性的社会。”
在此书的第六章中,周国平对否定抽象人性的歪理邪说,给予了更直截了当的驳斥。他指出,人们生活在一个共同的社会关系系统之中,尽管这个系统分裂成了彼此对立的阶级,但是,“人们所从事的各种形式的活动之间仍然存在着结构上的统一性,尽管活动领域不同,人都是活动的主体,在活动中通过一定的手段改造对象。因此,任何个人只要以一定的方式从事活动,他也就因为活动结构的统一而获得了人的共同本质”。也就是说,在阶级爱憎之上,还有着人类共同的感情。斯霞的“母爱教育”与所谓资产阶级“爱的教育”一样,放之四海而皆准。
那些指斥斯霞把孩子“陷在人性爱的污泥之中”的革命“左派”,无知于自己就生活在人类社会的统一性之中,而自以为只有把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放在无菌室里,才能保持其纯洁性。他们忘记了,他们吸吮的母奶就产于无菌室外,而父母对他们的爱抚就出自“人性爱的污泥”之中。
那些主张先调查溺水者的出身成分,再决定是否施救的激进青年,那些鼓吹“亲不亲,阶级分”的革命小将,当其父母沦为“黑帮”“走资派”“三反分子”的时候,有几个不是扑上去保爹保娘呢?人性在他们身上的胜利,证明了书中阐述的一个朴素的真理:“人的一般本质也就是广义的共同人性。它们是普遍的,即为一切社会类型包括一切阶级类型的人所具有。它们是稳定的,即为一切历史时代的人所具有。”“人们在爱情、友谊这样的私人感情关系中表现出的个性差异是最为突出的,其中也包括一定的阶级差异。但是,把阶级感情看作阶级社会里人的无所不包的感情形态,否认爱情、友谊区别于阶级感情的特殊性和其中包含的纯粹人类感情的因素,显然是荒谬的。”
可以说,这本书不但挖掉了那些歪理邪说的老根,廓清了笼罩中国几十年的理论迷雾,也奠定了周国平的“三观”,为他的散文创作奠定了方向和审美。
前些年,《文化苦旅》火的时候,读书界有“南有余秋雨,北有周国平”的说法。余秋雨站在历史的荒墟之上,以文化反思为职志,游走于现实的庙堂。周国平驻足于哲学的殿堂之中,以灵魂人心为皈依,浪迹于精神的家园。那些沉迷于其散文的人们,可曾知道,自称厌恶政治、甘守孤寂的周先生,骨子里无可救药地坚守着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巾”。
作 者:
启之,本名吴迪,学者,现供职于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编 辑:
张玲玲 sdzll080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