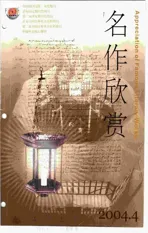凌叔华的闺阁叙事与“五四”反思(下)
2017-07-13福建常彬河北王慧
福建 常彬 河北 王慧
凌叔华的闺阁叙事与“五四”反思(下)
福建 常彬 河北 王慧
三
凌叔华笔下的旧式女性,不管是闺中少女,出阁少妇,还是年老高贵的“命妇”,既被封建文化“完美”地塑造,又被封建文化完全地抛弃,犹如“绣枕”命运。凌叔华以其女性经验的直觉和内省,勾勒了一系列旧式女人死寂闺阁中或麻木,或痛苦,或绝望的生存图景。
《女儿身世太凄凉》中的少妇婉兰,也许可以视为已经出嫁的大小姐、芳影、阿英姐妹(《绣枕》《吃茶》《茶会以后》)。出嫁前的她,婉约精致古典得犹如《红楼梦》里的病美人林黛玉,“湘帘半卷,时时吹出些药味,夹杂些香炉烟,徐徐地出来”,只见她“身穿凝杏黄衫子”,半卧在贵妃床上,“长眉细目,另有多病佳人的风致”;也早就知道未来的夫婿是个眠花宿柳的纨绔子弟,可是迫于礼教的压力,不敢退婚,被母亲开导为“女儿终归是人家的人,这次得罪他们,以后你就难做人了”。封建礼教规训女人要贤德端庄、不淫不妒、柔弱顺从、孝敬公婆、事夫如天等。新婚的婉兰却左右为难,轻薄的丈夫要在人前与她亲昵,若是顺从丈夫,既不符合端庄贞静不以色诱夫的妇训,又会遭致婆婆对她“狐狸精”“不要脸的女人”的詈骂。为了在夫家忍辱偷生,婉兰讨好婆婆,取悦丈夫:丈夫觊觎丫头美色,她就劝他收丫头为妾,丈夫不领情,说她贪图“贤德之名”(不淫不妒),婆婆也讽刺她“假惺惺”。丈夫要纳妓为妾,她不敢请求婆婆应允,丈夫骂她“吃醋不贤”。丈夫对她“冷一阵,热一阵的,没有一些真情义,过些日子,玩够看够,也和银香(他家丫头,引者注)一般”。可以说,封建礼教把婉兰打造成极合男权要求的毫无自我、逆来顺受的“夫权”和“婆权”的奴隶,尽管如此,为人媳妇(婆之媳、夫之妇)的她,仍然无所适从地两难于礼教赋予夫权和婆权的悖论性要求中,既被旧文化的价值体系所打造又被它所非议。
如果说《女儿身世太凄凉》是“绣枕”故事的“少妇篇”,那么《古韵》则可视为“中年篇”了。虽然这部长篇自传体的家族小说并不创作于“五四”及20世纪20年代,但其题材表现上仍然描写封建大家族女人的“绣枕”命运,其艺术风格也和上述作品颇为相似,属于凌叔华的“绣枕”系列,故将其纳入一并讨论。
《古韵》描写清末民初一个妻妾成群的官宦大家族女人争宠失宠的辛酸故事。它包含了许多小故事,每个故事之间既独立又关联。《一件喜事》以一个六岁小女孩“我”的视角反映妻妾制度下的妇女命运:在京城做直隶布政使的爸爸要娶“六妈”(第六房姨太太),是家里的“一件喜事”,小孩子们快乐得像过年一样,穿新衣、听大戏、吃大菜、玩游戏,还要向爸爸和几位妈妈道喜讨赏,此时的爸爸比平时和蔼了许多,几位妈妈们也“喜气洋洋”地里外张罗着迎娶新人。可“我”不明白“像苹果花一样美丽,鲜艳得令人嫉羡”的五妈为什么私下里要哭,而且“哭了一夜,饭都没吃”;不明白为什么在这样喜庆的日子里她要提到死,说“我真想一死了之。人只有死了,才会忘记一切”呢?为什么没有儿子的妈妈总是被有儿子的妈妈欺负?可三妈不是有儿子么,为什么仍然怕爸爸不喜欢她?三妈和新娶的六妈经常吵架,互相骂很难听的话,三妈骂六妈:“一天到晚缠着老爷,不让他到别的房里去”,六妈回敬三妈:“你个醋坛子,酸得发臭了,也不害臊。老爷愿到我这儿来,我能把他推出去?我倒想知道哪个老巫婆反锁了房门,留野男人跟她睡觉?”于是两个妈妈厮打成一团,只见“三妈和六妈又黑又长的头发,披散在脸和脖子上,遮住了眼睛,怪吓人的。粉和胭脂就着眼泪,把脸上弄得红一块,白一块,黑一块的,还有好多指甲抓过的印子”。多妻制下女人的生存之战,在不见天日的高墙大院里硝烟了上千年,兀自耗尽了毕生心力,至多挣得“奴隶的总管”(恩格斯),这就是男权社会女人命运的写照。
《有福气的人》是凌叔华闺阁叙事的“老年篇”。比起《古韵》中那几位命运多舛争风吃醋的姨太太,章老太太的福气是无可比拟的:她明媒正娶,娘家极为阔气,夫家也是官宦世家,“从年轻到老年她没有忧过财米”,也“没有为衣服首饰不如人红过一回眼”;年轻时出门参加喜庆活动,是正经八百的尊贵“命妇”,得穿“团鹤大褂,绣花朝裙,并带上朝珠”的“命妇”礼服;如今快七十了,“皮肤还是非常细腻”,几乎看不出皱纹。总之,章老太太的福气多得远不止这些,最难得的是她夫妇双全,四个儿子都已娶亲,早就有了一大群孙子,如今孙媳妇又要给她添重孙子;三个女儿也已出嫁,外孙多得老太太也记不清楚。反正老太太没有不如意、不顺心的事。尤其是儿子媳妇都很孝顺,都争着想法子讨她欢喜,“恨不得将老太太顶在头上走”。
做婆婆做祖母也许不是什么了不得的福气。最令人羡慕的还是她自己妆奁私储的富足,以及她的儿子媳妇及孙媳都孝顺她吧。天上方浮出乌云,大家都争着替老太太取衣服添上。二少奶奶同四少奶奶特别预备好吃的东西,来给老太太尝。老太太吃过后,若有些饱胀的毛病发作,她们就整天责备自己好逞能。大少奶奶和三少奶的嘴不大巧,也常常别出心裁使老太太欢喜。
老太太不仅福气好,还贤德过人“明大义”。章老太爷在京城做官时讨了两房小妾,她不仅没为此事与丈夫吵嘴生气,还大度地说:“大家人没有两三个伺妾是不成体统的,争风吃醋是小家子气的人才做得出来。”
就这样一个洪福齐天的老太太,在一次偶然的“听墙”中,得知子媳们的孝顺乖巧,原来是为了觊觎她丰厚的嫁奁私储。老太太的“好福气”一下子变得空落落的,变得无依无着。在旧价值体系(也是章老太太认定的“福气”的标准)中,她是团鹤朝裙、朝珠、命妇、贤德、财富、子孙等代表女人身份和价值的载体,是作为“绣枕”的闺阁小姐们梦寐以求的理想归宿。我们难以知道她是否为丈夫的不断讨妾痛苦伤心流泪过,也无法知道她在“摆平”了姨太太们的纷争中,是如何将自己抚平的,也许这些都是她内心无法言说的隐秘。我们只是看到她一次次以大度之心认可丈夫的“花心”,一次次以屈辱隐忍换来丈夫公婆的赞许,以不折不扣的礼教“贤德”规范打磨自己。也许这个“打磨”相当痛苦而漫长,犹如“炼狱”一般,但似乎看不到痛苦,也找不出血迹,甚至不用“刽子手”(礼教)亲自用刑,而是内化为自我的屠戮和沉埋。尽管如此,朝珠、命妇、朝裙、财富、贤德、子孙等,仍是旧价值体系认证章老太太福气和尊贵的意识形态力量。凭着这份价值认可,活在其中的章老太太当然很满意,很有福气。可历史的烟尘已经远离了昔日的荣光,朝珠、命妇、贤德、子孙……曾让章老太太无限风光的旧式女人的终极理想,已不再具有意识形态价值。如今裸露在儿孙面前的老太太,除了还有一份丰厚的妆奁私储值得让子媳儿孙们有惦记的价值外,其实已经一无所有,旧价值体系的坍塌让昔日的“命妇”成为裸露在历史中的弱者——个体——女人。
凌叔华的这些深宅大院的女性故事,存在着内在的关联性,显示了大家族女性生活的幽闭空间和“绣枕”命运。她们被封建文化“打造”得无可挑剔,不管是做女儿,做太太,还是做老太太,在有限的空间里,走过了女人一生的童年、青年、中年、老年的不同时光。无论她们的人生阶段有着怎样的不同,她们都在不知不觉中用一生演示并完成着生命被扼杀的过程,这是一种从欲望到情感到意志到思想的全面扼杀,而且这种扼杀不是明显地令人震惊的伤害事件,而是在日复一日的日常生活中,在死寂闺阁中悄然发生、自然进行的,无论是“他杀”还是“自戕”,都找不到任何暴虐的痕迹,这是礼教“软刀子”的功夫和女性自觉内化的结果。
和同时代女作家创造的女性形象相比,凌叔华小说中的女人要世俗得多,然而对照庐隐的自我沉迷,冰心的虚幻之爱,沅君的叛逆激情,凌叔华的女性世界又要切实得多。新文学初期盛行过的“问题小说”,冰心、庐隐皆以此驰名,而凌叔华未尝不是同行人,只是她的“问题”不是放眼时代风云讲述主流话语,不是振臂高呼的女性解放,摔门而出的“娜拉”身影,而是专注于不被纳入时代问题的旧式闺阁一隅。作为一个老去的时代,这个时代注定是死亡,但作为需要拯救的个体,闺阁中“大小姐”们难言的悲戚,绝望的处境,也是妇女解放不应被忽视、需要关注的问题。而凌叔华的这一视角,也是“五四”及20世纪20年代人们无暇顾及,或者根本忽略的女性生活的另一潜层。凌叔华无意使小说成为政治批判、社会批判的武器,而是着眼于文化批判、道德批判的人性建设,没有撕心裂肺的痛苦呐喊,也没有辗转反侧的绝望呻吟,只是“使习见的事,习见的人,无时无地不发生的纠纷,凝静的观察,显示人物‘心灵的悲剧’,或‘心灵的战争’。叔华的作品,在女作家中别走出了一条新路。作品中没有眼泪,也没有血,也没有失业或饥饿,这些表面的人生,作者因生活不同,与之远离了,作者在自己所生活的一个平静世界里,看到的悲剧,是人生琐碎的纠葛,是平凡现象中的动静,这悲剧不叫喊,不呻吟,却只是沉默”。从一个被意识形态所忽略的女性生活的幽闭层面揭示了妇女问题的复杂性,妇女解放的艰巨性和长期性,这就是凌叔华别异于“五四”言说的独特发现。
①《女儿身世太凄凉》是凌叔华的发轫之作,原载《晨报副刊》1924年1月13日。
②凌叔华:《女儿身世太凄凉》,见傅光明编:《凌叔华文萃》,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129—135页。
③凌叔华《古韵》又名《古歌集》,英文名“Ancient Melodies”,写于抗战期间,是用英文写成的,1953年在英国伦敦出版。《古歌集》的出版很受英国读者欢迎,认为是“一部令人陶醉的作品”,《泰晤士》报“文学专刊”特别撰文介绍,并成为英国当年的畅销书,后被译成法、俄、瑞典等多国文字出版,为凌叔华赢得了国际声誉。《古歌集》由傅光明译成中文,取名《古韵》,由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年在国内首次出版发行。《古韵》写作的起因和过程与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有一段不解之缘。凌叔华1938年开始与伍尔夫通信,直到1941年伍尔夫去世止。在伍尔夫的建议与鼓励下,凌叔华用英文写自传,每写好一篇就寄给伍尔夫一篇。伍尔夫很欣赏她的这些作品,致函称“我非常喜欢你写的东西,它们很可爱,很有魅力”。“二战”结束后,凌叔华来到伦敦,在英国桂冠女诗人萨克威尔·威斯特的帮助下,在伍尔夫的旧居中找到了自己的手稿,并于1953年由英国伦敦荷盖斯出版社(Hogarth Press)出版。
④⑤⑥⑦凌叔华:《古韵》,见傅光明编:《凌叔华文萃》,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26页,第29页,第45页,第44页。
⑧凌叔华:《有福气的人》,原载《现代评论第一周年纪念增刊》(1925年12月)。
⑨凌叔华:《有福气的人》,见傅光明编:《凌叔华文萃》,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206、207页。
(10)沈从文:《论中国现代创作小说》,见《文艺月刊》二卷4号至5、6号合刊,1931年4月30日至6月30日。
作 者:
常彬,中国华侨大学文学院教授。王慧,河北大学文学院讲师。编 辑:
张勇耀 mzxszyy@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