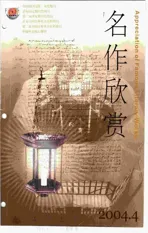散文·行走
——山西女人(上)
2017-07-13山西吴言
山西 吴言
散文·行走——山西女人(上)
山西 吴言
行走,是作家同脚下土地发生关联的方式,每位作家都该有属于自己的作家地理。由于山西特殊的地理位置,行走在山西女作家的创作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葛水平、蒋韵等都是热爱行走的作家,她们亲近土地、深入民间,离开了女性的狭隘地带,从而呈现出一种开阔和深厚。
山西女作家 行走 民间
若是一个作家了悟了行走的意义,我想他已经寻找到了写作的门径。
行走,是作家同脚下的土地发生关联的方式。每位作家都该有属于自己的作家地理。一东一西,有两位作家的行走呈现出了地域特色。一位是东部的张炜,他曾立意要遍访胶东半岛的三千多个自然村落。那时他就有了这样的认识:“书斋生活给予我滋养,但也消磨我的灵性。”一个作家只有走近土地,才能寻找到创作的根脉。另一个是西部的阿来,他一直在川藏交界的川西高原游走,那里成为他审视藏汉文化的立足点,成就了他作品的藏域特色。他的作品基本上都是行走的结果。如果有幸去过川西,就知道上帝多么眷顾那个地方,那里的景色是人间至境。能在那样的土地上行走是幸运的。
就地理环境而言,山西受到东面太行山脉,西面吕梁山脉的夹逼,中部狭长地带由东北倾向西南是一连串的盆地。黄河沿着吕梁山脉贯穿南北,形成晋陕两省的省界。从晋西北过黄河可通向广袤的塞外,于是产生了走西口的传统。太行山是一座非常有孕育能力的山脉,中华文明形成之初的农耕文明诞生于太行山中,上古神话历史阶段的神话故事大都发生在太行山脉。这些地方都留下了山西女作家的足印。行走在山西女作家的创作中也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葛水平是个热爱行走的人,她说:“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向前走。”行走已然成为她的一种姿态。她还说:“行走告诉了我,什么是速朽,什么是永恒,什么是肤浅,什么是本质,让我在时间流逝中获得一种生命的原始激情。”行走也涵养了她的气质,山川河流、雨露精华恩泽了她。她也有这样的决心:“我必将怀揣着从这个社会中消失的一切美好行走,一年年走下去,走进我生命长逝的深处。”
所以,行走很早就开始成为葛水平作品的题目,比如《我走我在》《心灵的行走》《走过时间》《在精神的领地行走》《向前走》。散文集《河水带走两岸》和散文《大地是河的长旅》是河流的行走,河流见证着时代的变迁,是河流带着她在两岸和大地上行走。
葛水平在行走中获得写作素材。她的长篇小说《裸地》的开篇,就是她行走乡间时遇到的第一个移民到太行山的山东人,篇名“裸地”竟然也是出自此人之口。那些深藏在太行山褶皱中的故事,在她行走时迎面而来。行走使她亲近土地,深入民间。行走使水平的散文脱离开女性散文的狭窄领地,呈现出一种开阔和深厚。
《大地是河的长旅》是沿着浊漳河的行走。浊漳河古时称为“天脊之水”,因为太行山脉的缘故,晋东南的上党地区古有“天脊”之称。从立体地形图上看,上党盆地独立于南北方向贯通山西中部的一连串盆地,在太行山脉及其支脉的包围下,呈封闭的窝状。此前,一直以为晋东南是革命老区,想当然地以为它是闭塞贫穷的,其实不然。这里孕育过早于晋商的潞商,商业曾经非常发达。《大地是河的长旅》写到了上党地区的神农遗迹和炎帝文化,让我又认识了上党盆地的另一层意义。那里因为太行山的屏蔽和地势高度,在远古的洪水泽国时期得以孕育最初的农耕文明,那里是神农氏炎帝最初的发祥地,农耕民俗文化积淀深厚。
散文集《河水带走两岸》是沿着山西第二大河流、水平的母亲河沁河的行走。河流在断流、干涸、死亡,村庄在衰落、背离、消失。“羊群代替了河水成为河道里的流淌物。”沁河源头水逐年减少,注入黄河处不见浪花。附着于河流的某些历史、生活方式及审美价值正在消逝。祖祖辈辈的故乡山神凹断了人脉。河流和村庄走向了衰亡的命运,一个被河流和乡土养育的女人,为母亲河见证和呐喊。
《河水带走两岸》中写了很多沁河流域的风物和民俗,见证着沁河两岸曾有的富庶繁华。《高于大地的庙脊》这一篇写琉璃,琉璃自古是代表权威的重器,常产生于富裕之地。民俗专家、作家冯骥才说最大气的琉璃在晋东南,由此可见昔日繁华。写这样的散文,水平会选取历史的角度,写出琉璃的兴衰缘由。要旁征博引很多史料典籍,比如《战国策》《魏书》《隋书》等,还要引用诗词戏曲,显示出她深厚的史学和国学功底。此外,还从民俗角度写了民间的手艺人,以及琉璃的各种门类、技法。水平的收藏嗜好在此派上了用场,她对古物是有亲身感受的,再夹杂以行走见闻和收藏轶事,整篇文章呈现出繁复和厚重,当然有时也会失于堆叠。这样的散文应该归于文化散文,水平在以自己的方式,为这一文体注入活力。
水平说自己是生活在城市的乡下女人,在失乡前,每年夏季都要穿过沁河,走回故乡。故乡的人和事是她创作的源泉。《河水带走两岸》也收集了她写乡亲、乡情的散文,我跟很多人一样,都是更喜欢这部分散文。《我们家的乡下男人》写有着山野之风的养父,《痴情的小厌物和她的爷》写一生孤寡的小爷,都写了他们的死,死得朴素如黄土,却有着撼动人心的力量。
水平还有一种行走,是她早年在剧团时走村串乡的演艺经历,这一部分她写得少,最近才结集出版了专门写戏剧的散文集《幕后的私语》。但我想她行走的意识和习惯,一定同那段演艺有很大关系。她丰富的民间写作题材,一定有很多来自那个时期的行走。
水平的散文有种生长性。比如关于“二胡”这个题材,在《今生今世》这本散文集中,是短小精干的散文《脱尽生命年节的二胡》。在《河水带走两岸》中变更为《旖旎的弦乐铺满大地》,补充了五爹的细节,乐器由原来的二胡扩展为上党“八音会”,补充了八音会的历史、曲目、类别等。到最新的散文集《幕后的私语》,题目没变,又增加了父亲的细节。对题材不断进行挖掘,一篇小散文逐渐拓展成一篇丰满的大散文,如同小树长成大树。同时散文集也呈现出了这种生长,《河水带走两岸》比最初的《今生今世》更为厚重。
水平的散文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小说化。她散文中的很多笔法是小说化的,很多题材在她笔下以散文和小说两种形式出现过,如《当政治延伸到日常生活中》写的是“土改”,是同赵树理有关的一个故事。水平还原了当时的场景,细节铺陈和情节转折也很自然到位,将赵树理部分隐去,就独立成为一篇小说《第三朵浪花》。于是,在水平这里就能清晰地感受到散文和小说的区别,一般地,散文是以作者的视角观察外物,小说则要切入人物自身心理,让情节自己去发展。水平在散文中常做这种切换,这让她的散文多了一份生动,也形成了她散文写作的特色。作为散文时,我们会被那份真实所感染;作为小说时,会有更完整和更强的文学表现力。
作家总是在找寻属于自己的词语、句子、语气、语调等,读水平的散文,也能体会出这一过程。最初,水平的语言还没有形成现在这样的特色,有点像普通话,很多人都在操持这样的语言。后来逐渐加入了方言。像很多相对封闭独立的地域一样,因少受外来语侵扰,晋东南一带有着自成一体的方言,这种方言很强烈,有自己独特的、传神的表达。水平散文和小说中的对话常常直接引用,能感受到这种方言的精彩。水平慢慢找到了自己的语气、语调,形成了自己的语言特色。
水平的语言很烈也很艳,“烈”是因为情感饱满浓烈,字句背后满含着情感能量。这点像太行山孕育出来的性格。“艳”更多的是受戏剧艺术的影响,像戏曲舞台上的浓墨重彩。水平是学戏曲出身,她的语言无疑受戏曲影响很深,她传承了戏曲语言的精准凝练、铿锵生动。水平不是学院派,那些规规矩矩的主谓宾定状补对她形不成约束,她直接跟词语遭遇,随心所欲安置着词语。比如说爱情和职业,“经历了才好向大地弥撒”,“弥撒”在这里的用法,我想不是笔误之类,她是取了字面和音色部分,更像一个动词,而不是宗教仪式的名词本意。水平最初写诗,所以语言非常跳跃,再加方言、古语的糅杂,有时不很顺畅,耐理解。水平的文字是从大地泥土里长出来的野生植物,蓬蓬勃勃。不过读她近期的文字,感觉越来越顺畅,那些生鲜的因子在减少。
蒋韵最新的散文集《活着就有眷恋》,令人惊喜地也写了很多行走。有20世纪80年代的“走西口”,有21世纪的“走台口”,除此之外,蒋韵的行走更辽阔,延伸到异域,美国、法国等。
蒋韵的行走更多的是一种主动的探寻,她用行走走近这片客居的土地。如她说,是向脚下的大地致敬。蒋韵这种行走的意识启蒙得很早,在20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的热潮中,她和李锐就开始“走西口”。蒋韵说:“行走中的体验和困惑,多次出现在我的作品中,那短短的一段行程,在我生命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迹。”即便已经过去了三十年的时间,蒋韵还是将这场行走刻画进了作品里,成就了她近期广受赞誉的小说《行走的年代》。
从蒋韵这里,我才知道“走台口”是什么,这个期待原本是放在水平那里的。“走台口”就是剧团辗转各地演出,也就是下乡,因为如今地方戏曲的市场多半都在农村。2000年的时候,蒋韵跟着实验晋剧院二团“走台口”。蒋韵写道:“曾经很迷恋那种漂泊和流浪的生活,参加一个‘草台班’做一个流浪艺人是我的梦想之一。”看来这样的行走是每个文艺青年的梦想!还记得我年少时那种对上戏校同学艳羡的心情。水平是学戏曲出身,应该有“走台口”的亲身经历,但也许缺少一种审美距离,水平写得少。她可能不知道自己实现了很多人的梦想。当写到“走台口”时,蒋韵又呈现出了另一面,有些粗犷,甚至豪放。这是在她的小说里感受不到的,就像从书斋走向了土地。
异域的行走中,2002年参加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工作坊,对于蒋韵的创作来说是重要的。远隔太平洋,她回望了自己的中国经验,也开始更加珍惜民间经验。此后,她的作品更多地出现了民歌、民俗,少了前期浓郁的书卷气。连她自己都说,回来后她的创作发生了潜移默化的转变。她毅然抛弃了一些东西,拾起了另一些东西,走出迷惘,重获自由。随之写出了《想象一个歌手》这样有着浓郁民俗气息的小说,写出了她的获奖作品和代表作品《心爱的树》。
蒋韵的散文更多的是一种随笔,作为小说家,看得出她没有在散文上花费更多的心思。所以也会从她的散文中明显地感觉出一种放松。于是在她的散文里就有一些小说中没有的东西。在蒋韵的小说里,感觉到她在竭力地挽留着一种流逝的美。蒋韵的小说常写死亡,但很少写丑陋和阴暗。在她的散文里,却也常出现“险恶”“凶险”之类的字眼,当然是说人事的,而不是自然。蒋韵一直在追寻一种很纯粹的精神生活,但生活没有让她驻足在象牙塔里。她一直在拨开芜杂,发现着这块并不诗意的土地上,并不是很多的美和传奇。
蒋韵散文的遣词用句,并不像小说里那样斟酌、用力。但是读她写爱荷华的那篇,感动还是涌到了心里,就像她的小说一样。能让一个已经不容易感动的中年人感动,这里面一定有特别的东西。于是想,写景状物、讲故事并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写感情。这不同于“抒情”,那要借助很多外在的形容词,也不同于那种琐碎的心理描写。基本上是在一些作家写了二十多年后,才能在他的作品里感受到这种直指人心的能力。就是说作家的每字每句都和自己的生命经验融到了一起,字句中饱含着生命能量。这需要一个人诚实无欺,忠于自己,对文字一直心存敬意,文字的锤炼过程和感情的萃取过程紧密结合,经过漫长的写作实践和生命体验,才能达到的境地。优秀的作家很多,才华各异,各有所长,但是我在心中默默数了数,能达到这个境地的作家加起来是个位数。这样的作家能用自己的文字,抵达人类情感最细微幽深的地方,并且能够对感情进行重新塑造。我确信,蒋韵拥有了这样的能力。
水平有篇散文《我走过时间,我走过山河》,非常好地道出了行走的意义,“只有行走才能寻找岁月透露出的希望”。只有脚踏大地,才能感受到力量源源不断地注入身体。这篇文章还把行走的意义同生命的价值联系在一起——“生命的价值仅仅在于,是否向真、向善、向美,即使目的地并未走到,但她朝向这个目的行走,她行走得认真,她摒弃了种种诱惑,走得执着。”
作 者:
吴言,本名李毓玲,山西省作协首届签约评论家。编 辑:
张玲玲 sdzll080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