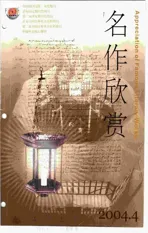《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获奖前后
2017-07-13北京阎纲
北京 阎纲
《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获奖前后
北京 阎纲
一
张一弓的中篇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发表在1980年第1期《收获》杂志,当时引起了读者的强烈震动。这部中篇小说,人们有充足的理由称它为“暴露文学”的名作之一;可是,它的歌颂却因“暴露”的真切准确而显得更为动人。我们面前被缚着的这个人,是国家的罪犯(犯人李铜钟!),又是人民的英雄(庄稼人用脑袋撞着床帮为他恸哭!),“犯人”和“英雄”,难道只隔了一张纸吗?疑义产生了,主要是两条:一,为“犯人”讴歌,于安定团结有碍;二,“动公仓”“抢皇粮”,有助长不安定因素之嫌。张一弓惴惴不安。他的这部小说,被编者从来稿中发现,并以十足的勇气发表出来,交付读者鉴别和批评,而批评界最初的反应却出乎意外的冷淡。
小说的故事是“大跃进”时的李家寨,为国家交粮几百万斤,“反瞒产”又反走了十万斤。当超额完成粮食征购任务的奖状挂上墙壁的时候,社员每天只能吃到粮食“二大两”。到后来,当公社书记大喊“反右倾可以反出粮食,反出吃的,灵得很”时,村里的榆树皮已经被剥光了,四百九十多口人已经完全断粮了。当“带头书记”做梦还在吹牛“两年进入共产主义”时,李家寨不得不宰牛了。老黄牛圆鼓鼓的眼睛滴着豆大的泪珠,好像对主人说:“我还要犁地,杀了我,够你们吃几顿呢?”正是为了安定团结,李铜钟没有带领饥民们暴动,没有对党发过一句牢骚,甚至没有逃荒,而是顾全大局,凄然地说:“党不知道咱忍饥挨饿!”饥民们心想:“毛主席不叫咱冻着……就不会叫咱饿着……兴是年前风老大,电话线刮断了……上头跟底下断了线……等两天,再等两天……等电话线接上……”四百多口人已经断粮七天,“告急信”如石沉大海,音讯渺茫;“反右倾”连萝卜汤都要反掉了,还在反,千钧一发,万般无奈,一个党支部书记“动”了“公仓”,借出活命之粮。李铜钟“他感到必须睡一个好觉,才能有足够的精力,让那条假腿把他带到县公安局‘投案自首’”。在法庭上,他“蓦地伸出那双铐在一起的大手,呼唤着:‘田政委,救救农民吧!’‘政委,快去……卧龙坡车站……快,快……’像是完成了一件神圣的使命,李铜钟恬静地入睡了”。他事前事后都向上级做了报告,虽然他成了法律的“犯人”,可是,他同时成了道义的英雄。当道义同法律产生矛盾的时候,理解法律,应该顾及道义。作者张一弓紧紧地抓住法律与道义对立统一的关系,把读者置于悲剧性壮烈的陶冶之中。所以,李铜钟一戴上手铐,英雄的形象就完成了。
《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传递出一个重要的信号,即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文学在控诉“文革”和极“左”的同时,已经将笔墨上溯到“十七年”的“左”祸,历史在这里沉思:“文革”与极“左”,事出有因。
二
1981年全国第一届中篇小说评奖开始,主办单位是《文艺报》。初评小组一致推举《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但是当时的气氛比较紧张。王任重批评《文艺报》是“右派骨干掌权”,应该进行人员调整。紧接着,召开“文艺部门党员领导骨干会议”,会上,林默涵就《文艺报》发表沙叶新的旨在针对“剧本创作座谈会”的《扯“淡”》等错误倾向,亮明了他与周扬、陈荒煤和冯牧的四点分歧。《文艺报》的领导以及他们的支持者对于“人性”“人道主义”“揭露阴暗面”的作品十分敏感,生怕被人抓住上纲上线,所以,对于《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评奖一事举棋不定。正是这个时候,作者张一弓所在的河南省纷纷提出反对意见,有的意见以加盖公章的单位证明信的方式转送到上级有关单位。反对这部中篇入选的意见主要是“暴露黑暗面”,其次是有着三十年新闻记者生涯的作者本人在“文革”中曾经进入《河南日报》革委会,是“三种人”。但是初评小组全体中青年评论家坚持授奖不动摇。《文艺报》为此专门派人前往郑州、登封等地进行调查,结果证明:一、作品暗指的“信阳事件”确有其事,事实比作品所写更严重;二、张一弓“文革”中进入《河南日报》社领导班子是事实,但属人民内部矛盾,更不是“三种人”,可以发表作品,至于能不能给奖,其说不一。事已至此,评选委员会不得不向评委会主任巴金实情禀报。巴老不但同意该作得奖,而且力主列为一等奖中打头的一个(一等奖共设五名)。后来由于各种考虑,将谌容的《人到中年》排在一等奖的第一位,《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排列第四。
事实证明,《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并没有因得奖而妨碍国家的安定团结,张一弓并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张一弓此后不断写出好作品,《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将此后的“反思文学”推向深入,作为“反思文学”的代表作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册。后来,我当着张一弓的面向他表达我近年愈渐强烈的心愿:“驱动改革开放的仍然是李铜钟式的人物,文学仍然需要李铜钟式的硬汉子,今天文学的历史价值、悲壮意味和阳刚之气不能无视李铜钟式的忠烈之士。”后来,我又应邀为他主办的《热风》一周年题词:“张天翼说现代文学在续写阿Q,事实证明新时期文学又在续写阿Q,可能还要写——李铜钟。”
当然,张一弓口将言而嗫嚅,将责任仅仅追到乡一级,而老实巴交的众社员们,都相信毛主席会来救他们,只不过“电话线刮断了”,电话打不通,毛主席在北京不知道。张一弓本人心里明白,暴露真相已经够冒险了,至于责任,止于“乡级”,再以上他不敢写。
而小说暗指的“信阳事件”,真相比张一弓写的严重得多。张一弓能够率先以小说的形式触及这个历史的疮疤,是我对《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特别看重的原因。2016年1月9日,张一弓在郑州与世长辞,享年八十一岁。历史不应当忘记他。
作 者:
阎纲,现代小说家。 出版有《文坛徜徉录》《文学八年》《阎纲短评集》《神·鬼·人》《余在古园》等。编 辑:
斛建军 mzxshjj@126.com